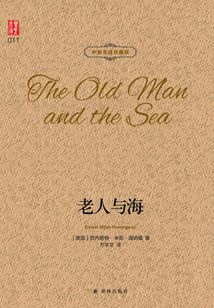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老人獨自一人駕著小船在灣流[1]中捕魚,已經有八十四天了,卻連一條魚也沒有捕到。頭四十天里,倒是有一個男孩陪著他。可四十天之后,男孩的父母見沒有捕到魚,就告訴男孩老人絕對是極“salao[2]”,意思是老人倒霉到了極點。男孩遵父母之命上了另一條漁船,頭一個星期便捕到了三條大魚。男孩見老人每天都空船而歸,心里很不好受,總是走過去幫忙,幫他拿那盤繞在一起的魚線,或者手鉤和魚叉,以及繞在桅桿上的船帆。船帆上用面粉袋打了些補丁,卷在桅桿上,就像一面象征著永遠失敗的旗幟。
老人面容消瘦而憔悴,脖頸上布滿了深深的皺紋。他的面頰上有些褐斑,那是太陽在熱帶海面上反射的光線所引起的良性皮膚癌變現象。那褐斑從他臉的兩側一直蔓延下去。由于常用繩索拉大魚,他的雙手留下了很深的疤痕。但這些疤痕沒有一處是新的,全都是昔日留下的,像無魚的沙漠里的蝕巖那般古老。除了眼睛,他渾身上下都顯露出老態——他那雙眼睛跟海水的顏色一樣,閃動著歡快和不服輸的光芒。
“圣地亞哥,”他們倆從小船停泊的地方攀上岸時,男孩對老人說道,“我又能陪你出海了。我們家掙到了一些錢。”
老人教會了這男孩捕魚,男孩愛他。
“不,”老人說,“你上的是一條好運漁船,就跟他們去吧。”
“可你別忘了,有一回你一連八十七天都沒捕到一條魚,但在接下來的三個星期里,我們卻每天都能捕到大魚。”
“我記著呢。”老人說,“我清楚你并不是因為缺乏信心才離開我的。”
“是爸爸叫我離開的。我是孩子,必須聽他的。”
“我明白,”老人說,“這是很正常的。”
“是他缺乏信心。”
“不錯。”老人說,“可咱倆有信心,是不是?”
“是的。”男孩說,“我請你到露臺酒吧去喝杯啤酒,然后再一起把漁具送回家吧。”
“好啊。”老人說,“捕魚人一道喝酒解悶嘛。”
兩個人來到露臺酒吧坐下。有好幾個漁夫拿老人開玩笑,老人卻不氣不惱。另外幾個年紀大些的漁夫望著老人,為他感到難過。不過他們并沒有把這種心情表露出來,而是禮貌地聊著,談論海流,談論他們把魚線下得有多深,還談論持續的好天氣,以及他們的所見所聞。此時,滿載的漁船紛紛返回。漁夫們把捕到的馬林魚一條條剖開,整條橫放在兩塊木板上,每塊木板的一端由兩個人抬著,深一腳淺一腳地送到收魚站,在那里等冷藏車來把魚運往哈瓦那的市場。捕到鯊魚的人則把它們送到海灣另一側的鯊魚加工廠去,吊在滑輪上,除去肝臟,割掉魚鰭,剝去魚皮,把魚肉切成一條一條的,以備腌制。
刮東風的時候,一股腥氣就會隔著海灣從鯊魚加工廠飄過來;但今天只飄來一絲淡淡的腥氣,因為風轉向了北方,后來逐漸平息了。露臺酒吧環境宜人,陽光明媚。
“圣地亞哥。”男孩開口說道。
“哦。”老人應了一聲。他手端酒杯,正在回憶好多年前的事兒。
“我去捕一些沙丁魚給你明天用吧?”
“不用了。你打棒球去吧。我還劃得動船,羅杰里奧會給我撒網的。”
“我很想去。即使不能陪你捕魚了,我也很想為你做點事兒。”
“你請我喝杯啤酒就夠了。”老人說,“你已經長大了。”
“你頭一次帶我出海,我有多大?”
“五歲。當時我把一條活蹦亂跳的大魚拖上船,它差一點把船撞得粉碎,你也差一點送了命。還記得嗎?”
“我記得魚尾巴噼里啪啦地胡亂拍打,船上的坐板都給打斷了,還有你用棍子打魚的聲音。我記得你一把將我推向了船頭,那兒放著濕漉漉的魚線卷。我感到整條船都在顫動,聽到你啪啪地用棍子一個勁兒地打魚,那聲音像砍樹一樣,我渾身上下都是甜絲絲的血腥味兒。”
“你是真的記得那件事,還是我跟你說的?”
“自打咱們頭一回一起出海,什么事兒我都記得清清楚楚。”
老人用那雙被灼曬且充滿自信的眼睛慈愛地望著他。
“如果你是我的兒子,我就帶你出海再賭一把。”他說,“可你是你爸爸和你媽媽的孩子,而且你現在跟的又是一條交好運的漁船。”
“我去弄沙丁魚來好嗎?我還知道從哪兒可以搞到四份魚餌。”
“今天我還剩下了一些魚餌。我把它們放在箱子里用鹽漬著呢。”
“讓我給你弄四份新鮮的來吧。”
“那就弄一份吧。”老人說。他的希望和信心從沒消失過,不過現在它們又重新煥發,就像心頭刮起了一陣清風一樣。
“還是兩份吧。”男孩說。
“好,就兩份吧。”老人同意了,“你不是偷來的吧?”
“我倒是想去偷,”男孩說,“不過這些是買來的。”
“謝謝你了。”老人說。他為人過于單純,并不去細想何時自己竟然這樣謙卑了。但是老人心里清楚自己變得謙卑了,知道這并不丟臉,無損真正的尊嚴。
“看這海流,明天一定會是個好日子。”老人說。
“你打算上哪兒捕魚?”男孩問道。
“往遠處走,等轉了風向再回頭。我想天亮前就出發。”
“我想辦法讓我的船主也往遠處走。”男孩說,“這樣的話,如果你釣到了真正大個頭的魚,我們可以趕去幫你的忙。”
“他怕是不會愿意到很遠的地方去。”
“不錯,”男孩說,“不過我會看見一些他看不見的東西,比如一只正在覓食的鳥兒。我會說前方有條鲯鰍[3],哄他駕船去追趕。”
“他的視力那么差嗎?”
“幾乎和瞎子差不多了。”
“這可怪了,”老人說,“他又從沒捕過海龜。只有捕那東西才傷眼睛呀。”
“你在莫斯基托海岸外倒是捕了好多年海龜,可你的視力還不照樣挺棒的。”
“我是個不同尋常的老頭子。”
“可你現在還有力氣對付一條真正大個頭的魚嗎?”
“我想還可以吧。捕魚講究的是技巧。”
“咱們把東西拿回家吧。”男孩說,“把東西送回去,我就可以拿上漁網,去弄沙丁魚了。”
他們從船上拿起捕魚的用具。老人把桅桿扛上肩頭,男孩拿的是魚線木箱,箱子里裝的是盤起來的編得很結實的棕色魚線、手鉤和帶桿子的魚叉。盛魚餌的箱子被放在小船的船尾的艙蓋下面。船尾的艙蓋下還放著一根棍子——如果捕到大魚,將它們拖到船邊,就用這根棍子制服它們。盡管不會有人來偷老人的東西,不過他覺得還是把桅桿和那些沉甸甸的魚線帶回家去的好,因為露水會腐蝕這些東西。盡管老人深信當地不會有人來偷他的東西,但他認為,把一只手鉤和一根魚叉留在船上實在是不必要的誘惑。
他們順著大路一起走到老人的小窩棚,從敞開的門走進去。老人把纏繞著船帆的桅桿靠在墻上,男孩將木箱和其他用具擱在桅桿旁邊。桅桿之長差不多相當于窩棚內一個單間的長度。窩棚是用大棕櫚樹上的那種被人戲稱為“海鳥糞”的堅韌的苞殼搭成的,窩棚里面有一張床、一張桌子、一把椅子,在泥地上還有一處用木炭燒飯的地方。把纖維質特別結實的“海鳥糞”一層一層展平再疊蓋在一起筑成棕褐色的墻壁,墻上掛著一幅彩色的耶穌圣心像[4]和一幅科布雷[5]圣母像。這些都是他妻子的遺物。墻上曾經還掛著他妻子的一張著色照,但他把它取下來了,因為他看到照片就覺得自己太孤單了。如今,那張照片放在屋角處的擱板上,掖在他的一件干凈襯衫下面。
“你吃什么飯呀?”男孩問。
“有鍋魚肉黃米飯。要吃點嗎?”
“不了,我回家去吃。要我給你生火嗎?”
“不用了,過一會兒我自己生吧。或者干脆就吃冷飯算了。”
“我把漁網拿去好嗎?”
“當然可以。”
其實窩棚里并沒有什么漁網,男孩還記得他們是什么時候把漁網賣掉的。然而他們每天要扯一通這種臆想出來的事情。也沒有什么魚肉黃米飯,這一點男孩心里也很清楚。
“85是個吉利的數字。”老人說,“你想不想看到我捕到一條去除了內臟后,凈重一千多磅的魚?”
“我拿漁網去弄些沙丁魚。你坐在門口曬太陽好嗎?”
“好吧。我有昨天的報紙,我來看看棒球賽的消息。”
男孩不知道“昨天的報紙”是否也是老人的想象,但是老人真的從床下取出了報紙。
“這是佩里科在‘bodega[6]’給我的。”他解釋說。
“我弄到沙丁魚就回來。我會把你的魚跟我的一起用冰鎮著,明早可以分著用。等我回來后,你可以給我講棒球比賽的情況。”
“揚基隊不會輸。”
“可我怕克利夫蘭印第安人隊會贏。”
“相信揚基隊吧,孩子。別忘了那位了不起的迪馬喬[7]。”
“我怕底特律老虎隊會贏,也怕克利夫蘭印第安人隊贏。”
“你可小心點,要不然連辛辛那提紅人隊和芝加哥白襪隊,你都要怕啦。”
“你仔細看報,等我回來了給我講。”
“你覺得我們去買張尾數為85的彩票怎么樣?明天就是第八十五天了。”
“可以啊。”男孩說,“不過,你上次的紀錄不是八十七天嗎,尾數買87怎么樣?”
“這種事情不會再有第二次了。你能弄到一張尾數為85的彩票嗎?”
“我可以去訂一張。”
“訂一張吧。要花2.5美元。向誰去借這筆錢呢?”
“這個容易。我總能借到2.5美元的。”
“我想我大概也借得到。不過我盡量不去借錢。第一步是向人借錢,下一步可就要向人討飯嘍。”
“身上穿得暖和點,老爺子。”男孩說,“別忘了,這可是九月了。”
“正是捕撈大魚的月份。”老人說,“在五月里,人人都能當個好漁夫。”
“我要去撈沙丁魚了。”男孩說。
男孩回來時,老人坐在椅子上睡著了,太陽已經落山了。男孩從床上拿來一條舊軍毯,蓋在椅背上,蓋住了老人的雙肩。老人的肩膀讓人挺不可思議的。雖然老人的年齡很大了,但他的肩膀依然非常強健,脖子也依然結實壯碩。而且當老人睡著了,腦袋向前耷拉著的時候,他脖子上的皺紋也不大明顯了。他的襯衫上不知打了多少次補丁,看上去像他的船帆一樣,那些補丁被陽光曬得褪成了許多深淺不同的顏色。老人的臉就顯得非常蒼老了,眼睛閉上時,臉上便一點生氣也沒有。報紙攤在他膝蓋上,在晚風中,靠他一條胳膊壓著才沒被吹走。他腳上沒穿鞋,打著赤腳。
男孩沒驚動他,悄悄走了。等他回來時,老人仍酣睡未醒。
“醒一醒,老爺子。”男孩一邊說,一邊把一只手搭在老人的膝蓋上。老人睜開眼睛,一時間仿佛從很遠的地方回來一般,隨即他笑了一下。
“搞到點什么?”他問。
“晚飯。”男孩說,“咱們吃飯吧。”
“我不太餓。”
“來吧,吃點吧。你可不能只打魚不吃飯呀。”
“我就是這么做的。”老人說著,站起身來,拿起報紙,把它折好,然后便動手把毯子折起來。
“還是把毯子披在身上吧。”男孩說,“只要我活著,就決不讓你餓著肚子去打魚了。”
“那么,祝你長壽,多保重自己。”老人說,“晚飯吃什么?”
“黑豆米飯,油炸香蕉,還有些燉菜。”
這些飯菜是男孩用雙層金屬飯盒從露臺酒吧拿來的。他口袋里有兩副刀叉和湯匙,每一副都用餐巾紙包著。
“這是誰給你的?”
“是馬丁。那個酒吧老板。”
“我得去謝謝他。”
“我已經謝過啦。”男孩說,“你用不著再去謝他了。”
“捕到大魚,我得把魚肚子上的肉送給他。”老人說,“他這樣照顧咱們,可不止一次了吧?”
“我想是這樣吧。”
“那除了魚肚子上的肉以外,我還得送一些別的給他。他對咱們太關心了。”
“他還送了兩瓶啤酒。”
“我喜歡罐裝的啤酒。”
“我知道。不過這是瓶裝的,阿圖埃伊牌啤酒。喝完我還得把空瓶子送回去。”
“你真是太好了。”老人說,“我們可以吃飯了嗎?”
“我一直在等著你呢。”男孩輕聲說,“不等你準備好,我是不愿打開飯盒的。”
“我準備好啦。”老人說,“我只需稍微洗一把就可以了。”
“你上哪兒去洗呢?”男孩心想。“村里有水的地方要沿著這條路再走兩條街才到。真該帶些水過來,還有肥皂和干凈的毛巾。我為什么這樣粗心大意呢?我該再給他弄件襯衫和一件夾克衫來讓他過冬,還要有一雙什么鞋子,并且再給他弄條毯子來。”
“這燉菜棒極了。”老人說。
“給我講講棒球賽吧。”男孩請求他說。
“正如我所說的,在美國聯盟[8]中,揚基隊出盡了風頭。”老人喜形于色地說。
“他們今天可是輸了的。”男孩告訴他。
“那算不上什么,關鍵是偉大的迪馬喬又重展雄風了。”
“球隊里其他人也很棒。”
“自然嘍。不過他的確不同凡響。在另一個聯盟[9]中,拿布魯克林隊和費城隊來說,我站在布魯克林隊一方。不過,我可沒有忘記迪克·西斯勒[10]和他在老公園[11]里打出的那些漂亮球。”
“那可是打得頂頂漂亮的球。他是我見過的擊球擊得最遠的球員。”
“你還記得他過去常來露臺酒吧嗎?我想帶他一起出海捕魚,但是卻不敢開口。我讓你去說,而你也不敢。”
“我記得。那可是大大的失策呀。他本來有可能跟咱們一起出海的。有那樣的經歷,一輩子都回味無窮啊。”
“我真希望能和了不起的迪馬喬一起去打魚。”老人說,“大家都說他父親就是個漁夫。也許他當初也像咱們一樣窮,能夠理解咱們。”
“了不起的西斯勒的父親可沒過過窮日子,他父親像我這么大時,就在大聯賽里打球了。”
“我像你這么大時,就在一條開往非洲的橫帆船上當水手了,在傍晚時分我還見過獅子在海灘上游蕩。”
“我知道。你跟我說起過。”
“現在聊非洲還是聊棒球賽?”
“我看還是聊棒球賽吧。”男孩說,“給我講講那個了不起的約翰·J.麥格勞[12]的事兒吧。”說話時,他把J 念成了“赫塔[13]”。
“過去的那些日子,他有時候也到露臺酒吧來。可是他只要一喝酒,就撒野,滿口粗話,難以相處。他的心思全都在賽馬和棒球上。至少,他衣袋里老揣著參賽馬的名單,常聽他在電話里提到一些馬的名字。”
“他是個了不起的經理。”男孩說,“我爸爸認為他是最了不起的了。”
“那是因為他來這兒的次數最多。”老人說,“如果杜羅徹[14]還是每年來這兒,你爸爸就會認為他是最了不起的經理了。”
“說真的,誰是最了不起的經理,盧克[15]還是邁克·岡薩雷斯[16]?”
“我覺得他們不分上下。”
“要說最了不起的捕魚人,那就是你了。”
“不。我知道有不少人比我強。”
“Qué va[17],”男孩說,“好漁夫倒是有很多,還有些是很了不起的。但頂好的只有你一個。”
“謝謝你。你的夸獎叫我高興。但愿不要碰上一條大得叫我對付不了的魚,免得證明你夸錯了人。”
“如果你還像你說的那么強壯,就不會有你對付不了的魚。”
“我也許不像我自以為的那樣強壯了,”老人說,“可是捕魚的訣竅我倒是懂得不少,而且我也有決心。”
“你該上床睡覺了,明天早上你才會精神飽滿。我把這些東西送回露臺酒吧。”
“那么祝你晚安。明天早晨我去叫醒你。”
“你是我的鬧鐘啊。”男孩說。
“而我的鬧鐘是我的歲數。”老人說,“為什么老人醒得特別早?難道是要讓白天長些嗎?”
“這我不清楚。”男孩說,“我只知道年輕人睡得死,會睡過頭。”
“叫人起床這一點我記得住,”老人說,“到時候一定會去叫醒你的。”
“我不想讓船主去叫我,顯得好像我不如他似的。”
“我懂。”
“祝你睡個好覺,老爺子。”
男孩走了。他們剛才吃飯的時候,桌子上沒點燈,此時老人就脫了長褲,摸黑上了床。他把那張報紙塞在長褲里,將褲子卷起來當枕頭。還有幾張舊報紙鋪在彈簧床墊上,他將毛毯往身上一裹,躺在報紙上就睡了。
沒過多久他就睡熟了,夢見小時候見到過的非洲,夢見長長的金色海灘和白色海灘,那海灘白得刺人眼睛,還夢見高聳的海岬和褐色的大山。他如今每天夜里都住在海岸邊,在夢中,他聽見激浪拍岸的怒嘯聲,看見當地人駕船在海浪中穿行。睡夢里,他聞到甲板上柏油和麻絮的氣味,還聞到陸地上的晨風夾裹著的非洲氣息。
通常一聞到陸地上刮來的風的氣息,他就會醒來,穿上衣裳去叫醒那男孩。然而今夜陸地上的風的氣息來得太早,他在夢中也知道時間尚早,就繼續做他的夢。他夢見群島的白色山峰從海面上升起,隨后夢見了加那利群島形形色色的港灣和錨地。
在他的夢里,不再有風暴、女人、大事件、大魚、搏斗和角力,也不再有他妻子的影像。如今他只夢見一些他去過的地方和海灘上的獅子。那些獅子在暮色中像小貓一般嬉戲著,他愛它們,如同愛那個男孩一樣。男孩從沒在他的夢境里出現過。此時一覺醒來,老人從敞開的門看了看外邊的月亮,攤開長褲穿上。他在窩棚外撒了泡尿,然后順著大路走去叫醒男孩。清晨的寒氣使他瑟瑟發抖,但他知道身子抖一抖就暖和了,而且馬上也就該劃船了。
男孩住的房子的屋門虛掩著。他推開門,赤著腳悄悄走了進去。男孩在外間的一張帆布床上熟睡,老人借著外面漸漸要消逝的月亮投進來的光線,把男孩看得很清楚。他輕輕握住男孩的一只腳,直到男孩被弄醒了,轉過臉來瞧了瞧他。老人點點頭,男孩從床邊椅子上拿起長褲,坐在床上把褲子穿上。老人走出門去,男孩跟在他后面,一副沒睡醒的樣子。老人伸出胳膊摟住男孩的肩膀說:“對不起。”
“別這么說,”男孩說,“男子漢就應該這樣做。”
他們順著大路朝老人的窩棚走去,一路上看見黑暗中有些打著赤腳的漢子在走動,扛著各自船上的桅桿。
到了老人的窩棚,男孩拿起放在籃子里的魚線卷兒,還有魚叉和手鉤,老人把繞著船帆的桅桿扛在肩上。
“想喝咖啡嗎?”男孩問。
“咱們把東西放到船上,然后去喝一杯吧。”
他們在一家清早為漁夫提供早餐的地方,喝了用煉乳罐盛的咖啡。
“你睡得怎么樣,老爺子?”男孩問。雖然要徹底擺脫睡意仍很難,但他的意識已經清醒了。
“睡得很好,馬諾林。”老人說,“我今天信心十足。”
“我也一樣。”男孩說,“現在我該去拿你和我用的沙丁魚,還有給你的新鮮魚餌。我的那個船主,東西都是他自己拿的。他從來不要別人幫他拿。”
“咱倆之間就不一樣了。”老人說,“你五歲時我就讓你幫忙拿東西了。”
“我知道。”男孩說,“我馬上就回來。你再喝杯咖啡吧。在這兒是可以賒賬的。”
他說完走了,光著腳沿著珊瑚石的小路向貯存魚餌的冷藏庫走去。
老人慢慢地喝著咖啡。這是他一整天的飲食,他知道應該把它喝了。好久以來,吃飯使他感到厭煩,因此他從來不帶午飯上船。老人在小船的船頭那兒放了一瓶水,一整天只需要喝那個就夠了。
男孩拿著沙丁魚和兩份包在報紙里的魚餌回來了。隨后,二人順著小路走向小船,腳下踩著的是夾雜著鵝卵石的沙地。他們抬起小船,讓它滑入水中。
“祝你好運,老爺子。”
“也祝你好運。”老人說。他把船槳的繩圈套在槳栓上,身子向前傾,借著槳葉在水中的推力,在黑暗中將船徐徐劃出港去。海灘別處也有其他船只要出海,老人只聽得見嘩啦嘩啦船槳入水和劃動的聲音,卻無法看見,因為此刻月亮已落到山后面去了。
偶爾某條船上傳來說話聲,但大多數船都寂靜無聲,只有嘩啦嘩啦的劃槳聲。眾漁船一出港口就分散開來,每一條都駛向指望著能找到魚的那片海面。老人心里有數,知道自己這次要駛向遠方,于是把陸地的氣息拋在身后,向散發著清晨純凈氣息的海洋深處劃去。劃過一片水域時,他看見水中閃現的磷光——那是馬尾藻發出的,漁夫們管這片水域叫“大井”,因為這里的水深突然達到七百英尋[18]。此處,海流沖擊在海底深處的峭壁上,激起了漩渦,因此形形色色的魚都聚集于此。在水底最深處的巖洞里,有大量的海蝦和做魚餌用的小魚,有時還會有一群一群的魷魚,它們在夜間浮到靠近海面的地方,所有在附近游弋的魚都拿它們當美餐。
在黑暗中,老人可以感覺到早晨正姍姍而至。他劃著劃著,聽見飛魚出水時噌噌的震顫聲,還有它們在黑暗中凌空飛起時挺直的胸鰭發出的咝咝聲。他非常喜愛飛魚,把它們當作他在海洋上的主要朋友。他替鳥兒感到難過,尤其是那些柔弱的黑色小燕鷗,因為它們始終在飛翔,在覓食,卻幾乎總是覓不到。他心想:“除了那些海盜鳥和強壯的猛禽,其他的鳥兒都比人類過得艱難。既然海洋環境這樣殘酷,為什么像海燕那樣的鳥兒卻生得那么纖弱和瘦小?海洋仁慈而又十分美麗。然而她會一下子變得殘酷無情,而且說變臉就變臉。那些在空中飛翔的鳥兒沖入水中覓食,鳴叫聲細小而悲哀。它們生得太柔弱,不適合這樣的海洋環境。”
每想到海洋,他老是稱她“la mar[19]”——這是漁夫們對海洋抱有好感時用西班牙語對她的稱呼。有時候,那些喜歡海洋的人也會說她的壞話,不過話語中總是把海洋當作女性。有些比較年輕的漁夫捕魚時用浮標當魚線的浮子,在把鯊魚肝賣了大價錢后買了汽艇,他們把海洋叫“el mar[20]”,將海洋視為男性。他們談論起海洋時,把海洋當作一個競爭者或是一個去處,甚至當作一個敵人。可老人總是把海洋當作女性,無論她愿意或者不愿意施恩于人;如果海洋做出離譜或者邪惡的事情,老人會覺得那是因為她身不由己。他心想,月亮能對海洋產生影響,就像月亮能影響一個女人一樣。
他平穩地劃著槳,這對他來說并不吃力,因為他把劃船的速度掌握得很好。除了海流偶爾攪起幾個漩渦,海面平平展展的。他把三分之一的活兒都讓海流替他干了。此時天開始放亮,他發現自己已經把船劃得很遠了,超出了之前的預期。
“我在‘大井’這兒曾經捕過一個星期的魚,卻一無所獲。”他心想,“今天我要換個地方,到有鰹魚群和長鰭金槍魚群的水域去,說不定那兒有大魚呢。”
天色大亮之前,他放出了一個個魚餌,讓船隨著海流漂移。第一個魚餌下沉到四十英尋的深處,第二個去了七十五英尋的深處,第三個和第四個在藍色海水中分別沉到了一百英尋和一百二十五英尋的深處。每個魚餌都是用小魚制成的——魚頭朝下,魚鉤的鉤尖藏在魚腹里,系好,縫牢;凡是魚鉤突出的部分(鉤彎以及鉤尖),都有新鮮的沙丁魚裹在外邊做偽裝。每條沙丁魚都用釣鉤穿過雙眼,幾條魚穿在突出的鋼鉤上就形成了半環形。釣鉤上沒有一處不叫大魚覺得又香又美味的。
男孩給了他兩條新鮮的小金槍魚,或者叫作長鰭金槍魚,這兩條魚像鉛錘般掛在那兩根入水最深的魚線上。在另外兩根魚線上,他分別掛上了一條大大的青鲹和一條黃色金銀魚——這兩條魚已被當魚餌使用過,但依然完好,再加上一些鮮美的沙丁魚為輔,更增加了它們的香味和吸引力。每根魚線都像一支大鉛筆那般粗,一端纏在一根青皮釣竿上,只要有魚一拉或一碰魚餌,釣竿就下垂。每根魚線有兩個四十英尋長的魚線卷,它們可以牢牢地系在其他備用的魚線卷上,這樣一來,如果用得著的話,一條魚可以拉出長達三百多英尋的魚線。
此時,老人一邊緊盯著那三根支在小船一側的釣竿,觀察著動靜,一邊輕輕搖著槳,讓魚線上下垂直,在水中保持適當的深度。天空亮堂堂的,太陽像是隨時會噴薄而出。
太陽從海上升起來了,光線淡淡的。老人可以看見海上還有一些別的漁船,船身低低地浮在水上,在靠近海岸的那片水域,隨著海流排開。太陽變得更亮了,耀眼的陽光射在水面上。接著,太陽完全升了起來,平坦的海面把陽光反射到他眼睛里,刺得眼睛火辣辣地疼,因此他劃船時不敢朝太陽看。他低頭看海水,注視著那幾根直直垂入黑黢黢的深水里的魚線。他的魚線垂得比任何一個漁夫的魚線都要直。這樣,在黑黢黢的水里,每個深度都有一個魚餌守候在他所期待的地方,等著在附近游動的魚來上鉤。而別的漁夫讓魚線隨波逐流,有時候魚線垂入六十英尋的深處,他們卻以為已經到了一百英尋的深度了。
老人心想:“我能精確地保持魚線的位置。只是我不再像以前那樣幸運了。不過,誰說得準呢?也許今天好運會降臨呢。每一天都是一個新的日子。走運當然好。不過我寧愿精確些。這樣,運氣來的時候,就從容了。”
太陽升起有兩個小時了。他瞭望東方時,不再感到那么刺眼了。現在他的視野里只有三條船,低低的,遠遠的,在靠近海岸那邊。
“我這一輩子,初升的太陽老是刺痛我的雙眼,”他心想,“可我的眼睛還是好好的。傍晚時,我可以直視太陽,那時眼前沒有發黑的感覺。按說,傍晚時的陽光更強一些,但叫我眼睛痛的卻是早晨的陽光。”
就在這時,他看見一只軍艦鳥舒展長長的黑翅膀在前方的天空中盤旋。它嗖地俯沖下來,斜著身子,雙翅朝后縮,隨后又凌空盤旋。
“它找到什么了。”老人大聲說道,“它不只是在搜尋。”
他劃得又慢又穩,前往那只鳥盤旋的那片水域。他不疾不徐地劃著船,讓魚線保持上下垂直的狀態。由于他想利用軍艦鳥引路,船速加快了些,不過他稍微靠海流近了些,以便依然保持正確的捕魚方式。
軍艦鳥在空中飛得高了些,又開始盤旋起來,雙翅一動也不動,隨即嗖地猛沖下來。老人看見有飛魚從海水中躍出,接著拼命地掠過海面。
“有鲯鰍,”老人叫出了聲,“有大鲯鰍。”
他把雙槳放在船上,從船頭下面拿出一根細魚線,魚線上系著一段金屬接鉤繩和一個中號釣鉤。他把一條沙丁魚魚餌掛在上面,然后將魚線從船舷那兒放下水去,把一端緊緊地系在船尾的一只環首螺栓上。隨后,他在另一根魚線上也安了魚餌,又把它卷起來放在船頭的陰影里。他又一邊開始搖槳劃船,一邊注視著那只此刻正低低地貼著水面覓食的長翅膀的黑鳥。
他看著看著,那只鳥又朝下俯沖。為了這一動作,它特地把翅膀朝后掠,然后猛烈地扇動一陣翅膀,追蹤著飛魚,卻無果而終。老人可以看見水中的大鲯鰍也在追逐逃跑的魚,它們所過之處浪花四濺。鲯鰍在凌空躍起的飛魚身下破水而行,等飛魚落入水中時,它們就潛入水中全速追趕。這群鲯鰍的數量真多啊,他想。它們散得很開,飛魚無路可逃。那只鳥卻希望渺茫。飛魚對它來說個頭太大了,而且又飛得太快。
他看著飛魚一再地從海里躍出,那只鳥的追逐卻毫無效果。“這群大魚從我眼前溜掉了。”他心想,“它們游得太快,游得太遠了。不過,說不定我能逮住一條掉隊的,說不定我期盼的大魚就在它們周圍轉悠呢。我的大魚肯定就在跟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