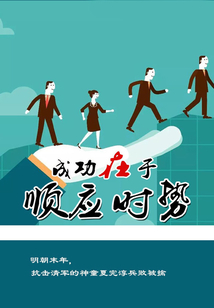
成功在于順應(yīng)時(shí)勢(shì)
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第1章 管仲巧諫齊桓公
【原文】桓公觀于廄,問廄吏曰:廄何事最難?廄吏未對(duì)。管仲對(duì)曰:夷吾嘗為圉人矣,傅馬棧最難。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傅,直木無所施矣。先傅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亦無所施矣!
(《管子·小問第五十一篇》)
【譯文大意】齊桓公察看馬圈,問管理馬圈的官吏說:“在馬圈干什么事情最難?”管馬圈的官吏一時(shí)回答不上,管仲回答說:“我曾經(jīng)當(dāng)過養(yǎng)馬人,我了解里邊的情況,把各種竹木合在一起編成馬圈欄是最難的。如果先用彎曲的材料,那么彎曲的又要彎曲的才能搭配,直到用彎曲的材料把馬圈欄編完,這樣,直的材料就沒有地方可用了。反之,如果先用直的材料,那么直的又要用直的去搭配,直到用直的材料把馬圈欄編完,這樣,彎曲的材料也就沒有地方可以用得上了。”
【闡釋】管仲借著齊桓公視察馬圈的機(jī)會(huì),巧妙地對(duì)齊桓公進(jìn)行了規(guī)勸。他以“傅馬棧最難”的比喻道出了選用人才最難的真情。編排各種不同的竹木為柵欄,必須把彎曲的同彎曲的,直的同直的排列在一起。而選用人才也這樣。同時(shí),這則故事也說明,進(jìn)行諫議既要有膽量,又要講究方式方法。這樣,才能達(dá)到諫議的目的。
楚莊王納諫
【原文】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愚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于秦晉,喪地?cái)?shù)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蹊蹺為盜于境內(nèi)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
(《韓非子·喻老》)
【譯文大意】楚頃襄王想攻打越國,杜子進(jìn)諫說:“大王想攻打越國,為什么呢?”楚頃襄王回答說:“因?yàn)樵絿y兵弱。”杜子說:“我為攻打越國而擔(dān)憂。智慧就象人的眼睛一樣,能看見百步以外的東西而不能看見自己的眼睫毛。大王的軍隊(duì)自從被秦、晉打敗以后,喪失了數(shù)百里的土地,這是兵弱;楚國境內(nèi)蹊蹺造反而官吏不能禁止,這是政亂。大王您的兵弱政亂一點(diǎn)不在越國之下,而想去攻打越國,這樣的智慧就象眼睛看不到睫毛一樣。”楚頃襄王停止了攻打越國的行動(dòng)。所以,了解事物的難處,不在于看清別人而在于看清自己。這就叫“能看清楚自己才算得上聰明”。
【闡釋】納諫從善,虛心聽取別人的意見,隨時(shí)改正錯(cuò)誤,無論是治國還是為人處世都是極為重要的智慧。
唐太宗納諫
【原文】上厲精求治,數(shù)引魏徵人臥內(nèi),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上遣使點(diǎn)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軀干壯大者,亦可并點(diǎn)。”上從之。敕出,魏徵固執(zhí)以為不可,不肯署敕,至于數(shù)四。上怒,召而讓之曰:“中男壯大者,乃奸民詐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執(zhí)至此!”對(duì)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眾多。陛下取其壯健,以道御之,足以無敵于天下,何必多取細(xì)弱以增虛數(shù)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無欺詐。’今即位未幾,失信者數(shù)矣!”上愕然曰:“朕何為失信?”對(duì)曰:“陛下初即位,下詔云:‘逋負(fù)官物,悉令蠲免。’有司以為負(fù)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征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為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關(guān)中免二年租調(diào),關(guān)外給復(fù)一年。’既而繼有敕云:‘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為始。’散還之后,方復(fù)更征。百姓固已不能無怪。今既征得物,復(fù)點(diǎn)為兵,何謂以來年為始乎!又陛下所與共治天下者在于守宰,居常簡閱,咸以委之;至于點(diǎn)兵,獨(dú)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為治乎!”上悅曰:曩者朕以卿固執(zhí),疑卿不達(dá)政事,今卿論國家大體,誠盡其精要。夫號(hào)令不信,則民不知所從,天下何由而治乎!朕過深矣!乃不點(diǎn)中男,賜徵金饔一。
(《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個(gè)二唐紀(jì)八)
【譯文大意】唐太宗勵(lì)精圖治,多次讓魏徵進(jìn)入臥室內(nèi),詢問政治得失。魏徵知無不言,太宗均高興采納。太宗派人征兵,封德彝上奏道:“中男雖不到十八歲,其身體強(qiáng)壯的,也可一起征召。”太宗同意。敕令傳出,魏徵堅(jiān)持已見不肯簽署,如此往返四次。太宗大怒,將他召進(jìn)宮里責(zé)備道:“中男中身體強(qiáng)壯的,都是那些奸滑虛報(bào)年齡以逃避兵役的人,征召他們有什么害處,而你卻如此固執(zhí)!”魏徵答道:“軍隊(duì)在于以道義加以統(tǒng)率,而不在人數(shù)眾多。陛下征召身體壯健的成丁,用道義加以統(tǒng)率,便足以無敵于天下,又何必多征召年幼之人來充虛數(shù)呢?況且陛下每次都說:‘朕以誠義、信任治理天下,以使百姓沒有欺詐行為。’現(xiàn)在陛下即位沒多久,卻已經(jīng)多次失信了!”太宗驚愕地問道:“朕怎么失信了?”魏征答道:“陛下剛即位時(shí),就下詔說:‘百姓拖欠官府的財(cái)物,一律免除。’有關(guān)部門認(rèn)為拖欠秦王府的財(cái)物,不屬于官家財(cái)物,仍舊征收。陛下由秦王即位天子,府庫的財(cái)物不是官家之物又是什么呢?陛下又說:‘關(guān)中地區(qū)免收二年的租調(diào),關(guān)外地區(qū)免除徭役一年。’不久又有敕令說:‘已納稅和已服徭役的,從下一年開始。’等到歸還已納稅物后,又重新開始征調(diào),這樣百姓不能投有怪罪之意。現(xiàn)在是既征收租調(diào),又征召為兵,怎么能說從下一年開始呢?況且與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都是這些地方官員,日常事務(wù)都委托他們辦理;至征召兵丁時(shí),都懷疑他們有詐,這難道是以誠信為治國之道嗎?”太宗高興地說:“從前朕認(rèn)為你比較固執(zhí),懷疑你不通達(dá)政務(wù),現(xiàn)在看到你議論國家大事,都切中要害;朝廷政令不信實(shí),則百姓不知所從,國家如何能得到治理呢?朕的過失很深吶!”于是,不征召中男,并賜給魏徵一個(gè)金饔。
【闡釋】《尚書》說:“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說的是能禮賢下士的人可以統(tǒng)治天下,認(rèn)為別人都不如自己的人一定會(huì)滅亡;隋煬帝恃才驕橫,不聽諫言,終至滅亡。唐太宗則認(rèn)識(shí)到“未能受諫,安能諫人”,故有“貞觀之治”流名后世。
北齊孝昭帝納諫
【原文】庫狄顯安侍坐,帝曰:“顯安,我姑之子;今序家人之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下多妄言。”帝曰:“何故?”對(duì)曰:“陛下昔見文帝以馬鞭撻人,常以為非;今自行之,非妄言邪?”帝握其手謝之。又使直言,對(duì)曰:“陛下太細(xì),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日久,將整之以至無為耳。”又問王唏,唏曰:“顯安言是也。”顯安,干之子也。群臣進(jìn)言,帝皆從容受納。
(《資治通鑒》卷一百六十八陳紀(jì)二)
【譯文大意】庫狄顯安有一次侍坐,孝昭帝說:庫狄顯安是我姑姑的兒子,今天咱們以家人的禮節(jié)相待,免去君臣之間的敬畏之禮,你可以說說我的不足。庫狄顯安說:陛下老胡亂地說話。孝昭帝問:為什么呢?庫狄顯安答道:陛下以前看見文帝用馬鞭子打人,認(rèn)為做得不對(duì)。現(xiàn)在陛下自己卻這樣做,難道不是說假話嗎?孝昭帝握住他的手表示感謝。又讓他進(jìn)一步直言。庫狄顯安說:陛下太瑣細(xì),身為天子,卻更象一個(gè)小吏。孝昭帝說:我深知道這一點(diǎn)。然而國家沒有法制很久了,我將整頓它,以使國家達(dá)到無為而治。孝昭帝又問王唏,王唏說:庫狄顯安說得對(duì)。庫狄顯安是庫狄干之子。朝中群臣所提建議,孝昭帝都從容接受采納。
【闡釋】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鄒忌諷齊王納諫
【原文】鄒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映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fù)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客曰:“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yuǎn)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于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nèi),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卜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譏于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卜,群臣進(jìn)諫,門庭若市。數(shù)月之后,時(shí)時(shí)而間進(jìn)。期年之后,雖欲言,天可進(jìn)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于齊。此所謂戰(zhàn)勝于朝廷。
(《戰(zhàn)國策·齊策一》)
【譯文大意】齊國的鄒忌身長八尺有余,容貌也很英俊。有一天早晨穿著好衣冠對(duì)著鏡子問他的妻子:“我和城北的徐公比起來誰美?”妻子說:“你美麗得多,徐公哪里能夠比得上你呢。”城北的徐公,是齊國的美男子,鄒忌不相信自己比徐公漂亮;便又去問他的妾:“我和城北的徐公比起來誰美?”妾說:“徐公哪里能夠比得上你呢!”上午,有位客人來訪,鄒忌和他坐下談話,問客人道:“我和徐公哪一個(gè)美?”客人回答說:“徐公不如您美。”第二天徐公來訪,鄒忌仔細(xì)地看著徐公,覺得自己比不上他。再對(duì)著鏡子照照,更覺得不如徐公美了。夜里躺在床上一想,不覺恍然大悟:“妻子說我美,是因?yàn)槠珢畚野。绘f我美,是因?yàn)槲窇治野。豢腿苏f我美,那是想有求于我啊。”
于是他就去朝見齊威王,說:“臣知道自己實(shí)在不及徐公美,可是因?yàn)槌嫉钠拮悠珢畚遥嫉逆窇治遥嫉目腿讼胗星笥谖遥远颊f臣比徐公美。如今齊國方圓一千多里,城一百二十座,宮中的妃子和大王左右的人,哪一個(gè)不偏愛大王;朝廷上的眾臣,哪一個(gè)不畏懼大王;國內(nèi)的百姓,哪一個(gè)不想有求于大王。這樣看來,大王受的蒙蔽實(shí)在到了極點(diǎn)了。”齊威王說:“不錯(cuò)。”于是就下了一道命令:“官吏百姓如有能當(dāng)面指責(zé)我過錯(cuò)的,給頭等賞;上書規(guī)勸我的,給中等賞;能在公共場所批評(píng)我,被我聽見了的,給下等賞。”這道命令剛發(fā)下時(shí),群臣紛紛進(jìn)諫,門庭熱鬧得象市場一樣。幾個(gè)月之后,進(jìn)諫的就斷斷續(xù)續(xù)的了,一年以后,雖然想說,可是卻沒什么話可說了。那時(shí)燕、趙、韓、魏等國聽說了這件事,都來朝見齊威王,與齊國交好。這是安坐在朝廷上打了勝仗啊!
【闡釋】鄒忌能在一片贊揚(yáng)聲中保持清醒頭腦,可謂有自知之明。更值得稱道的是,齊威王能接受忠言,居安思危,獎(jiǎng)勵(lì)批評(píng)自己過失的人,這樣的民主作風(fēng)更是難能可貴。
鼓勵(lì)直言
【原文】納言之政,謂之諫諍,所以采眾下之謀也。故君有諍臣,父有諍子,當(dāng)其不義則諍之,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惡不可順,美不可逆;順惡逆美,其國必危。夫人君拒諫,則忠臣不進(jìn)其謀,而邪臣專行其政,此為國之害也。故有道之國,危言危行;無道之國,危行言遜。上無所聞,下無所說。故孔子不恥下賤,故行成名著,后世以為圣。是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矣。
(《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
【譯文大意】采納建議和接受意見的方法稱為直言相勸。它是廣泛征集意見的重要途徑。所以君主有敢于提意見的臣子,父親有敢于提意見的兒子。一旦發(fā)現(xiàn)他們有不符合道義的言行便馬上進(jìn)行規(guī)勸。幫助發(fā)揚(yáng)正確的地方,糾正錯(cuò)誤的地方。錯(cuò)誤的不能任其發(fā)展,正確的不能受到指謫。助長錯(cuò)誤扼止正確,國家一定很危險(xiǎn)。如果君主拒不接受規(guī)勸,那么忠臣就不能獻(xiàn)出他們的謀略,奸佞之臣就會(huì)專橫于朝政,這是國家的禍患。因此道德風(fēng)尚好的國家,人們行為直率言論大膽;道德風(fēng)尚不好的國家,人們言行不一,貌恭詞遜。朝廷很難了解到下層的真實(shí)情況,下層百姓不敢向朝廷講真話。孔子不以做低賤的工作為恥辱,所以行為有修養(yǎng),名聲很響亮,后來的人把他尊為圣人。因此房屋漏雨雖然滴落在地上,但卻要堵塞上面;上面不堵塞,下面就無法居住。
【闡釋】能否聽到不同的意見和采納不同的意見都十分重要。國家要有敢于直言和勇于接受的良好風(fēng)氣,否則國家政權(quán)就不會(huì)鞏固。
狄人杰諫武則天立儲(chǔ)
【原文】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狄仁杰從容言于太后曰:“姑侄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后,配食太廟,若立侄,則未聞侄為天子,而拊姑于廟者也。”太后乃寤。
(《智囊·語智部》)
【譯文大意】武則天兩個(gè)侄子武承嗣、武三思,一心鉆營想當(dāng)太子。狄仁杰從容地對(duì)武則天說:“姑侄和母子哪一個(gè)更親呢?陛下如果立自己的兒子,那么千秋萬代后也會(huì)被供奉在太廟之中;如果立侄子,我還沒有聽說侄子作天子,會(huì)把姑媽供奉在宗廟里的。”武則天于是幡然醒悟。
京房談古論今
【原文】是時(shí),中令石顯顓權(quán),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上曰:“君不明而所任用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shí)亂而君危知之。”房曰:“如是,任賢必治,任不肖者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于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jì)二百四十二:年災(zāi)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zāi)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卜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愈于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后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幃幄,之中,進(jìn)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后上亦不能退顯也。
(《資治通鑒》卷二十九元帝建昭二年)
【譯文大意】漢元帝時(shí),宦官石顯獨(dú)攬朝綱,他的好友五鹿充宗任尚書令,二人聯(lián)合執(zhí)政,權(quán)傾內(nèi)外,無所不為。
一日,元帝在閑暇時(shí)召見京房,京房問元帝:“為什么在周幽王、周厲王時(shí)國家出現(xiàn)危機(jī)?他們?nèi)斡昧撕稳耍俊痹壅f:“君王無道,任用奸佞之臣。”京房又問:“是作君王的明知其奸佞而仍用他們,還是因其賢能才任用的呢?”元帝說道:“當(dāng)然是覺得他們賢能才用的。”京房說:“可為什么現(xiàn)在說他們不是賢能呢?”元帝說:“那時(shí)天下大亂,君王身處險(xiǎn)境。”京房說:“既如此,任用賢能國必有治,任用奸佞國必大亂,這都是必然的。為什么幽王、厲王不能覺悟起用賢能,而一味任用奸佞以致陷于困境呢?”元帝回答說:“亂世之君,以為自己所用都是賢能的,若能覺悟出自己的錯(cuò)誤,天下怎么還會(huì)有亡國之君呢?”京房道:“齊桓公、秦二世也曾經(jīng)知道幽王厲王之事,并譏笑過他們。可齊桓公仍用豎刁,秦二世仍用趙高,以致朝政混亂,盜賊群起。為什么他們沒能以幽王、厲王為戒,覺悟到自己用人不當(dāng)?”元帝說:“只有治國有法的君王,才能根據(jù)過去預(yù)測將來。”
京房脫下官帽,叩頭道:“《春秋》一書記載二百四十二年間的天災(zāi),用以警示后代的君王。自陛下登極以來,日食月食,星辰逆轉(zhuǎn),山崩泉涌,大地震動(dòng),天落隕石;夏降霜,冬響雷,春花凋謝,秋葉茂盛,即使霜降也不能肅殺害蟲。水災(zāi)、旱災(zāi)、蝗災(zāi)、饑荒、瘟疫流行。盜賊難以制伏,受刑之人滿市。《春秋》所記天災(zāi)人禍,應(yīng)有盡有。陛下以為現(xiàn)在是亂世還是治世?”元帝說:“已經(jīng)亂到極點(diǎn)。”京房又道:“陛下現(xiàn)在任用的是什么人?”元帝說:“現(xiàn)在舶災(zāi)難和為政之道,幸而較前代為過,我以為責(zé)任不能全歸于他們。”京房說道:“前代的君王也和陛下的想法一樣,恐怕后代人再看現(xiàn)在,也如同現(xiàn)在看前代一樣。”
元帝想了一會(huì)問道:“現(xiàn)在擾亂朝政的人是誰?”京房回答:“陛下自己應(yīng)該明白。”元帝說:“我不明白,不然,哪里還會(huì)再用這種人呢?”京房說道:“陛下最信任的,與他共商國事,并握有用人權(quán)柄的便是。”京房所指即為石顯。元帝也很清楚,他對(duì)京房言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京房告退。這之后,漢元帝依然任用石顯如故。
【闡釋】京房所言,主要是奉勸漢元帝,不要任用石顯等奸佞之人,卻沒有直接說出。而是以幽王、厲王為例,引出前代君王任用奸佞,導(dǎo)致國家混亂,天災(zāi)肆虐。進(jìn)而指出治世亂世,全在于君王是否任用賢能。最后才直言漢元帝所用奸佞之臣。層層剖析,文辭縝密,具有很強(qiáng)的邏輯性。
裴度上表斥奸臣
【原文】翰林學(xué)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jié),求為宰相,由是有寵于上,每事咨訪焉。稹無怨于裴度,但以度先達(dá)重望,恐其復(fù)有功大用,妨己進(jìn)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奸蠹之狀,以為:“逆豎構(gòu)亂,震驚山東,奸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zhèn),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為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后。河朔逆賊,只亂山東;禁闈奸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無以驅(qū)除。今文武百僚,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忿,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獎(jiǎng)用方深,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為國計(jì),且為身謀。臣自兵興來,所陳章疏,事皆要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奸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與佞倬亦無仇嫌,正以臣前請(qǐng)乘傳詣闕,面陳軍事,奸臣最所畏憚,恐臣發(fā)其過,百計(jì)止臣。臣又請(qǐng)與諸軍齊進(jìn),隨便攻討,奸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礙,逗留日時(shí);進(jìn)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fù),悉不顧矣。為臣事君,一至于此!若朝中奸臣盡去,則沙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好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陛下倘未信臣言,乞出臣表,使百官集議,彼不受責(zé),臣當(dāng)伏辜。”表之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癸未,以弘簡為弓箭庫使,稹為工部侍郎。稹雖解翰林,恩遇如故。
(《資治通鑒》卷二百四個(gè)二穆宗長慶元年)
【譯文大意】翰林學(xué)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互相勾結(jié),求做宰相,因而受到唐穆宗的寵信,每有大事就向他詢問。元稹與裴度無嫌怨,只是因?yàn)榕岫仍谒笆苤赜茫衣曂芨撸屡岫仍倭⒋蠊Γ恋K自己進(jìn)升,所以,凡是裴度上奏的軍事謀劃,他都與魏弘簡從中阻撓,使之不得實(shí)施。于是,裴度上表,指責(zé)元稹和宦官朋比為黨,奸邪害國的罪狀,認(rèn)為:“王庭湊、朱克融逆臣豎子叛亂,震驚山東,奸臣朋比為黨,禍害國家。陛下如果想掃平幽州、鎮(zhèn)州的叛軍,首先應(yīng)當(dāng)肅清朝廷奸黨。為什么呢?因?yàn)闉?zāi)禍有大小,考慮事情有先后。河朔逆賊只能禍亂山東,宮中的奸臣卻禍亂天下。所以河朔的叛賊危害小,而宮中的奸臣危害大。危害小的,我與各將領(lǐng)就能翦滅,危害大的,如果不是陛下覺悟,則斷無法驅(qū)除。現(xiàn)在滿朝文武,京城和地方官吏,凡是有良心的人,對(duì)奸臣所為無不憤慨,凡能言語之人也無不嗟嘆。只是由于陛下正重用他們,才不敢指責(zé),恐怕奸臣未除而禍及己身,并不為國家考慮,而是擔(dān)心牽連自己。自從朝廷興兵討伐幽州、成德以來,我所陳奏的用兵方略,都事關(guān)緊要,但朝廷的詔書,卻指令不一。我受陛下委任,責(zé)任不輕,但遭奸臣從中阻撓的事情,也實(shí)在不少。我一向與奸臣無仇怨,只是由于前不久請(qǐng)求乘驛馬到京城,當(dāng)面向陛下陳述用兵方略,奸臣最懼怕的,是我向陛下揭露他們的罪過,所以百般阻撓我進(jìn)京。我又曾上奏朝廷,請(qǐng)準(zhǔn)許我率兵與諸軍一同進(jìn)攻,隨機(jī)應(yīng)變,討伐叛賊。但奸臣怕我成功,以各種理由橫加阻撓,致使我軍停滯不前,無淪進(jìn)退,都受到他們的牽制,所奏方略,也都被他們從中阻塞。他們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讓我出兵不利,不能成功,于國家安危,山東征討勝負(fù),全然不顧。作為臣下侍奉皇上,竟然如此!如果朝中奸臣全部鏟除,那么,沙朔叛亂會(huì)不討自平;但若朝中奸臣仍舊存在,那么,討平叛亂,對(duì)于國家也無益處。陛下如果不相信我的話,請(qǐng)把我的奏章公布于眾,讓百官議論,如果奸臣不遭到群臣的譴責(zé),我愿受到應(yīng)有的懲罰。”裴度多次上奏斥責(zé)元稹等人,穆宗雖然很不高興,但考慮到裴度是朝廷重臣,不得不作出讓步。癸未,貶魏弘簡為庫箭使,元稹為工部侍郎。元稹雖被解除翰林學(xué)士的職務(wù),但穆宗對(duì)他的寵信依然如故。
【闡釋】元稹為了個(gè)人私欲,置國家安危于不顧,百般阻撓裴度用兵方略的實(shí)施。因此,裴度上表,痛陳清除朝廷奸臣的必要,鮮明地提出,奸臣不除,叛亂難平,國家更無安寧之日。然而?身為最高統(tǒng)治者的穆宗皇帝,卻無洞察之明,對(duì)奸臣非但不除,反而寵信如故,可見,上無明君,下必奸臣當(dāng)除,反而寵信如故,可見,上無明君,下必奸臣當(dāng)?shù)馈?
史起自薦引漳水
【原文】魏襄王與群臣飲酒,酣,王為群臣祝,令群臣皆得志。史起興而對(duì)曰:“群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得志則不可。”王曰:“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對(duì)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dú)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門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與不忠,不可效也。”魏王無以應(yīng)之。明日,召史起而問焉,曰:“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duì)曰:“可。”王曰:“子何不為寡人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也。”王曰:“子誠能為寡人為之,寡人盡聽子矣。”史起敬諾,言之于王曰:“臣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雖死藉,愿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諾。”使之為鄴令。史起因往為之,鄴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鄴有圣令,時(shí)為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之稻粟。”使民之可與不可,則無所用智矣。魏襄王可謂能決善矣。
(《論語疏證·泰伯篇》)
【譯文大意】魏國君襄王與群臣飲酒,飲到正高興的時(shí)候,為群臣祝愿,希望他們都能得到滿意的期望和要求。大夫史起興沖沖地對(duì)曰:“群臣中有賢德者,也有不賢德者,賢德者得志猶可,不賢德者得逞則不可。”襄王說:“都像西門豹這樣的臣子如何也。”史起回答說:“魏國行田制度為百畝,而鄴偏偏為二百畝,是田地不好嗎;漳河之水就在鄴縣的旁邊,西門豹卻不知道用來灌溉鄴下之田,是其笨拙無能也;他知道的事情而不報(bào)告,是不忠也,既愚又不忠,不可仿效也。”史起的一番話,問得襄王無言答對(duì)。次日,襄王召見史起而問曰:“漳水真的可以灌鄴下之田嗎?”史起回答說:“能。”襄王說:“先生為何不為我去辦此事呢?”史起說:“我恐怕大王沒有這樣的決心。”襄王說:“先生若真能為我為之,我盡聽先生吩咐矣。”史起對(duì)襄王表示敬重,答應(yīng)了襄王的要求,并告訴襄王說:“我可以去完成此項(xiàng)任務(wù),但開工后,勞民費(fèi)財(cái),得不到近利,朝野必定怨恨于臣。大者致死,小者抄家。臣雖然喪命抄家,大王也不要改變主意,應(yīng)改派他人繼續(xù)進(jìn)行下去。”襄王曰:“我答應(yīng)了。”
于是便以史起為鄴下令。史起赴任,著手辦理引漳水濟(jì)鄴下的工程。果不出所料,不久便民怨大張,想抄史起的家,史起不敢出來而躲了起來。于是襄王便又委派別人去替代史起,繼續(xù)把引水工程進(jìn)行下去。
經(jīng)過艱苦努力,終于竣工通水,民大得其利,百姓交相稱頌而歌之:“鄴有賢明的縣令,首推史起公,引來漳河水,灌溉鄴下田,最終結(jié)束了自古以來不生谷物的咸鹵地,長出了稻黍谷粱。”
治國需兼聽
【原文】國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亂者,君間也。君之所以明也,兼聽也;其所以間者,偏信也。故人君通必兼聽,則圣日廣矣;庸說偏信,則愚日甚矣。
(王符《潛夫論·明間》)
【譯文大意】國家之所以能治理好,是因?yàn)閲t明智慧,通情達(dá)理;國家之所以治理不好,甚至發(fā)生動(dòng)亂,是因?yàn)閲栌箤V疲廾翢o知。而國君之所以聰明智慧,并且通情達(dá)理,是因?yàn)樗軌蚵犎「鞣矫娴囊庖姡粐曰栌褂廾粒且驗(yàn)樗麆傘棺杂茫犉哦斐傻摹R虼耍瑖胪ㄟ_(dá),就必須聽取各個(gè)方面的意見,這樣他的智慧就一天比一天多,道德也隨之日益高尚;國君如果在聽取意見時(shí),采取偏聽偏信的態(tài)度,甚至采納一些很不高明的建議,那么,他就一天比一天昏庸,一天比一天愚昧。
【闡釋】一個(gè)國家的當(dāng)權(quán)者要想把國家治理好,這同他在對(duì)待下屬進(jìn)言問題上的道德修養(yǎng)關(guān)系密切。國君能治理好國家,必然真?zhèn)涿髦恰⑼ㄇ檫_(dá)理、廣開言路的品質(zhì);反之,則只能是剛愎自用,愚昧無知。賢明君主之所以賢達(dá)在于他能“兼聽”左右建議;昏君之所以亡國就在于他偏聽偏信。所以,兼聽則明,則治;偏聽則暗則亡。領(lǐng)導(dǎo)者應(yīng)該不斷加強(qiáng)自身的道德修養(yǎng),這是我們從中得出的結(jié)論。
明君不輕賤拒言
【原文】是故明君蒞眾,務(wù)下言以昭外敬,納卑賤以誘賢也,其無距言,未必言者之盡可用也,乃懼距無用而讓有用也。其無慢賤,未必其人盡賢也,乃懼慢不肖而絕賢望也。是故,圣王表小以厲大,賞卑以招賢,然后良工集于朝,下情達(dá)于君也。故上無遺失之策,官無亂法之臣,此君民之所利,而奸佞之所患也。
(王符《潛夫論·明間》)
【譯文大意】所以,賢明的國君治理天下,務(wù)必要聽取下層的意見,以昭示對(duì)朝廷之外臣民的尊重;務(wù)必要任用地位低下的人以吸引在野賢人的到來。國君之所以不拒絕別人的意見,也并不是因?yàn)閯e人的意見都對(duì),都可以采納,而是害怕拒絕了無用的意見而排斥了有用的意見。賢明的國君之所以不輕視地位低下的人,也不是說地位低下的都是賢才,而是害怕輕視那些不好的人而使賢才感到絕望。所以,賢明的君主表彰小的激勵(lì)大的、賞賜地位低的招引才華出眾的。這樣,人才就能集中到朝廷,下層的情況也能傳達(dá)到君王耳朵里。國君沒有失誤的政策,國家沒有不守法的官吏。這種情形,國君和百姓都感到很有利,而奸佞之徒則感到害怕、憂慮。
【闡釋】這里深入論述了如何兼聽的策略問題。一是不要鄙視地位低下的人,要敢于打破等級(jí)觀念,大膽任用在野的有能之士。但又并不是濫用,因?yàn)槟康氖瞧鹫邔?dǎo)向作用,好讓那些懷才之士不對(duì)政府失望,并且主動(dòng)積極地為政府效勞。二是不要拒絕下級(jí)的意見。這并不是講,不做分析研究,來者不拒,一概采用;而是通過采納正確的提議來使言路通暢,保證為政者處在有效的輿論監(jiān)督環(huán)境中,使他有機(jī)會(huì)去糾正自己尚未發(fā)覺的錯(cuò)誤,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損失。如何鑒別來自下級(jí)進(jìn)言的正確與否,還要虛心地聽取周圍人(包括下屬)的意見,集眾人之智慧以明斷。
為政之道務(wù)于多聞
【原文】為政之道,務(wù)于多聞,是以聽察采納眾下之言,謀及庶士,則萬物當(dāng)其目,眾音佐其耳。
(諸葛亮《便宜十六策·視聽》)
【譯文大意】治理國家的道理,務(wù)必要多多聽取各方面的情況。因此要認(rèn)真聽取、分析和采納下級(jí)的建議,謀劃決策甚至要考慮到普通士兵的意見。這樣,就能把任何事情都看得清清楚楚,各種各樣的意見也能起參考作用。
【闡釋】諸葛亮倡導(dǎo)從政者必須“聽察采納眾下之言”,才能客觀地分析問題,找出解決問題的正確辦法;并且,只有充分聽取下級(jí)的意見,才能調(diào)動(dòng)各個(gè)方面的積極性。這很有見地。
為政要善知其過
【原文】夫修諸己而化諸人,出乎邇而見乎遠(yuǎn)者,言行之謂也。故人主之患,莫甚于不知其過;而所美,莫美于好聞其功。
(《晉書·潘岳傳·附潘尼傳》)
【譯文大意】用自己的道德修養(yǎng)水平作標(biāo)準(zhǔn)去感化別人,并由近及遠(yuǎn)地傳播,是靠語言和行動(dòng)的。所以,一國之主最大的禍害,沒有比看不清自己的過失更大的了;而最大的優(yōu)點(diǎn),也沒有比樂于聽取別人批評(píng)更好的品質(zhì)了。
【闡釋】潘尼認(rèn)為,為政為官者,自己必須有高尚的道德修養(yǎng)。每個(gè)人都有自己看不見的缺點(diǎn),而旁觀者清;所以,聽取別人對(duì)自己缺點(diǎn)的指正正是一個(gè)為政者的最大美德;反之,則是其最大的過失。
荀子論進(jìn)諫
【原文】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懼也,大臣父兄,有能進(jìn)言于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jìn)言于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之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與疆君矯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之所尊厚也,而暗主惑君以為己賊也。故明君之所賞,暗君之所罰也。暗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也。伊尹、箕子可謂諫矣,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于趙可謂尊矣,信陵君之于魏,可謂拂矣。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
(《荀子·臣道篇》)
【譯文大意】君主如果有了錯(cuò)誤的主意,做錯(cuò)了什么事,害怕這些錯(cuò)誤將會(huì)危及國家敗壞社稷,作為君主的大臣、父親、兄弟不能不管。有人能向君主進(jìn)獻(xiàn)忠言,勸他糾正,君主如果采納,就算完事,如果不采納,就毅然離去,這叫作諫;有人向君進(jìn)獻(xiàn)忠言,勸他糾正,君主如果采納就算完事,如果不采納,就當(dāng)君面死去,這叫作爭;有人能齊心協(xié)力,帶領(lǐng)群臣百官一起強(qiáng)行使君主糾正錯(cuò)誤,君主即使感到不高興,也不得不接受,于是解除了國家的災(zāi)難,解除了國家的災(zāi)難,最后使君主受到尊重,國家從此安定下來,這就叫作輔;有人能不聽從君主的命令,并竊取君主的重器,做了君主不同意做的事情,但卻使國家轉(zhuǎn)危為安,洗刷了君主的恥辱,給國家?guī)砹藰O大的好處,這就叫作弼。所以,敢于諫、爭、輔、弼的人是國家的棟梁,君主的寶貝。對(duì)于這種人,賢明的君主尊重厚待他們,而昏庸的君主則把他們看成是賊害自己的人。因此,賢明的君主所要賞賜的人正是昏庸的君主所殺害的人。昏庸的君主所要賞賜的人,正是賢明的君主所要?dú)⒑Φ娜恕R烈⒒涌梢苑Q得上是諫臣,比干、伍子胥可以稱得上是爭臣,平原君可以稱得上是趙國的輔臣,信陵君可以稱得上是魏國的弼臣。所以,傳書上說:“服從道義不服從君主”,就是這個(gè)意思。
【闡釋】荀子深刻地論述了進(jìn)言的四種方式或策略,并對(duì)這四種人高度贊揚(yáng),稱之為社稷之臣,是國家的財(cái)寶。君主對(duì)這四種人應(yīng)該尊重、信賴、厚待。更為可貴的是,他還提出了“從道不從君”的論點(diǎn)。也就是說,對(duì)上級(jí)進(jìn)獻(xiàn)忠言時(shí),應(yīng)該實(shí)事求是,從真理出發(fā),堅(jiān)持原則,而不是為了討上司的歡喜而溜須拍馬。這種為追求真理而不惜得罪上司(甚至?xí)忻饴殹㈩^的危險(xiǎn)),以國家利益為重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
讒言似蜜危害無窮
【原文】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曰甲。余欲君之棄其正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為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shì)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如賜死君前。妾以賜死,若復(fù)幸于左右,愿君必察之,無為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為棄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為后,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裹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強(qiáng)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于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詐棄,而子以之死。從是觀之,父之愛子也猶可以毀而害也。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群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賢圣之戮死哉!此商君所以車裂于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于楚者也。
(《韓非子·奸劫拭臣等十四》)
【譯文大意】楚莊王弟弟,春申君有個(gè)愛妾,名叫“余”,春申君的正妻有個(gè)兒子叫做“甲”。余想讓春申君拋棄正妻,于是自個(gè)兒把身體弄傷給春申君看,哭著說:“我能夠當(dāng)您的妾就感到很榮幸了,雖然,能到夫人那里侍奉就不能侍奉您了,到您這兒來侍奉就不能去夫人那里了。我自己本來不好,沒有侍奉兩個(gè)主人的能力,而侍奉兩個(gè)人又是很困難的。與其死在夫人那里,不如您賜我死在您面前。我因您恩賜而死,而再有人得到你的寵愛,您務(wù)必要察明清楚,不要讓人笑話。”春申君因聽信了余的讒言,拋棄了自己的正妻。余又想把正妻的長子甲殺死,讓自己的親生子繼承王位,于是,自己撕爛了貼身的內(nèi)衣跑去讓春申君看,并且哭著說:“我得到您的寵愛已經(jīng)很長時(shí)間了,甲不是不知道,但是他要用強(qiáng)力調(diào)戲我,我進(jìn)行反抗,他卻撕爛了我的衣服。這個(gè)孩子的不孝道,沒有比這更厲害的了。”春申君很氣憤,于是殺了甲。正妻因?yàn)閻坻钠墼p而被拋棄,兒子也因?yàn)殒喽馈S纱丝磥恚赣H如此摯愛的兒子,還是未能逃脫因詆毀而被加害。而君王和大臣相處,沒有父親和兒子之間那種親密的感情。而且群臣中傷詆毀的壞話廣又不是出自妾余一人之口,那么賢圣的人被殺死又有什么奇怪的呢?這就是商鞅被秦國車裂,吳起被肢解于楚國的原因。
【闡釋】春申君因聽信讒言而殺子棄妻,充分說明了聽信讒言的危害性。讒言是諫言的變種。它往往出自被寵愛者之口,寵愛者和被寵愛者之間因?yàn)槟撤N利害關(guān)系,加上讒言披著諫言的外衣,有甜蜜柔順的誘惑性,因此欺騙性是很隱蔽的。一上當(dāng)受騙者往往在付出慘重代價(jià)后后悔不已。為此,在對(duì)待自己親近溺愛的人言一事上,要冷靜分析,深入調(diào)查,不能以好惡親疏來決定是非曲直,否則憑一時(shí)沖動(dòng),將會(huì)醞成千古之恨。作領(lǐng)導(dǎo)工作的人,不能不以此為鑒,現(xiàn)在有很多鉆營之徒往往借助領(lǐng)導(dǎo)的親近寵愛者來實(shí)現(xiàn)個(gè)人野心,對(duì)此,不能不提防。
魯哀公中計(jì)拒諫
【原文】仲尼為政于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梨且謂景公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榮其意?哀公新樂之,必怠于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于魯。”景公曰:“善。”乃令梨且以女樂二八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于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
(《韓非子·內(nèi)儲(chǔ)說下第三十一》)
【譯文大意】孔子在魯國從政,政績顯著,魯國路不拾遺,夜不閉戶。齊景公對(duì)此深感不安。梨且對(duì)齊景公說:“君工您不用愁,去掉孔子,就象是吹走一根羽毛那樣容易。您為什么不用高官厚祿來迎接他呢?我們可以送給魯哀公一批能歌善舞的年輕女子,使他產(chǎn)生驕橫虛榮的情緒。哀公得到這樣一批女子后,必然貪戀新歡而懶得處理政事;而仲尼又一定要進(jìn)行諫爭,結(jié)果必定為魯君拒絕。”景公說:很好。于是命令梨且把十六個(gè)能歌善舞的年輕女子送給魯哀公。哀公很高興,并以此為樂,結(jié)果懶得處理政事。孔子進(jìn)諫,哀公也不聽。于是孔子便離開魯國而到楚國去了。
【闡釋】孔子在魯國為政,頗有政績。但后來卻因哀公拒諫而出走,這對(duì)魯國是一個(gè)損失。哀公為什么拒絕了孔子的進(jìn)言呢?道理很簡單,他中了景公的計(jì)。景公利用哀公喜歡聲色的特點(diǎn),投其所好,結(jié)果哀公就荒廢朝政,疏遠(yuǎn)諍臣,更聽不進(jìn)諫言,孔子對(duì)哀公就很失望,不得不走之。這個(gè)故事提醒人們不要被糖衣炮彈所擊中,你所喜愛的東西往往會(huì)斷送你的前途。其危害性與讒言相比較,有過之而無不及;特別是它的形式很具有隱蔽性、欺騙性;其效果卻和普通讒言一樣使人的感官得到滿足,并誘發(fā)你沉溺其中。自愿走進(jìn)獵人的陷井。這是一種何等淺薄的悲劇,但它的發(fā)生頻率卻很高。難道對(duì)這種物質(zhì)化的美麗“讒言”就無法對(duì)付嗎?冷靜的理智是唯一的選擇。
齊景公痛哭失晏嬰
【原文】晏子死,景公操玉加于晏子尸上而哭之,涕沾襟。章子諫曰:“非禮也。”公曰:“安用禮乎?昔者吾與夫子游于公阜之上,一日而三不聽寡人,今其孰能然乎?吾失夫子則亡,何禮之有?”免而哭,哀盡而去。
(《晏子春秋·外篇不合經(jīng)術(shù)者》)
【譯文大意】晏子死了,景公拿了一塊玉石放在他尸體上,哭了起來,淚水都把衣服沾濕了。章子進(jìn)諫說:“這樣做不合乎禮節(jié)。”景公說:“哪里還能講什么禮節(jié)?過去我曾和晏子一起游歷公阜,一天竟有三次不聽我的話,現(xiàn)在誰還能這樣做呢?我失去了這樣敢于直言相諫的重臣,我自己也難以生存下去了,此時(shí)我還有什么禮節(jié)可講呢!”言畢,免冠大哭,直到哭盡悲哀才離去。
【闡釋】景公痛哭失晏,這個(gè)故事相當(dāng)感人;卻也同樣發(fā)人深省。景公乃一國之君,竟然不顧君臣之禮,而在他人面前哭訴其哀。何也?晏子在世之時(shí),經(jīng)常善言進(jìn)諫,有時(shí)甚至一日三次;而景公雖然當(dāng)時(shí)有些不悅,但還是采納了他的建議,并深受其益。故在晏子死時(shí),倍感是一個(gè)重大損失,于己于國都不利,甚至發(fā)出“吾失夫子則亡”的感人之言。說明景公的確是位愛賢、任賢、信賢的明智君王;而晏子也的確是位忠心耿耿,為國為民而不吝進(jìn)言的諍臣。這種默契配合,進(jìn)而建立了一種深厚的感情,對(duì)工作大有裨益。景公和晏子所具有的美德令后人仰慕。
忠言逆耳利于行
【原文】夫良藥苦于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人而已己疾也;忠言拂于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韓非子·外儲(chǔ)說左第三十二》)
【譯文大意】良藥吃了很苦,但是聰明的人經(jīng)勸告后還是喝下,因?yàn)橹懒妓庍M(jìn)到肚子以后可以醫(yī)治好自己的疾病;忠言聽到耳朵里是不順心的,但是賢明的君主還是要認(rèn)真地去聽取,因?yàn)橹乐已钥梢詫?dǎo)致事業(yè)的成功。
【闡釋】韓非子用形象的比喻說法闡述了忠言的巨大作用。忠言好比良藥,其味很苦,但卻能醫(yī)治疾病;諱病而忌醫(yī)治,勢(shì)必導(dǎo)致自我滅亡。這個(gè)道理很簡單,正如古語云:“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但是,要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執(zhí)行起來卻不容易。我們應(yīng)有意識(shí)地增強(qiáng)自己接受帶刺的忠言的能力。
革車千乘不值一言
【原文】趙簡子圍衛(wèi)之郛郭,犀循犀櫓立于矢石之所不及。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吾之士數(shù)弊也。”行人燭過免胄而對(duì)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弊者。昔者我先君獻(xiàn)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zhàn)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xiàn)公沒,惠公即位,淫衍暴亂,身有玉女,秦人恣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受之,圍衛(wèi)取鄴,城濮之戰(zhàn),五敗荊人,取尊名于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弊也!”簡子乃去循櫓,立矢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zhàn)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之一言也。”
(《韓非子·難二第三十七》)
【譯文大意】趙簡子率軍包圍了衛(wèi)國都城的外圍,他自己身旁有堅(jiān)固的盾櫓防衛(wèi),并且站立在弓箭石頭攻擊不到的地方。他擂鼓讓士兵攻城,可是沒有人奮起沖鋒。筒子很生氣,扔掉鼓棒抱怨說:“士兵太疲勞了!”戰(zhàn)士燭過摘去頭盔而回答說:“我聽說過,只有君王自己投有把人用好,士兵是沒有什么毛病的。過去,我們的先君獻(xiàn)公吞并了十七個(gè)國家,使三十八個(gè)國家對(duì)之臣服,十二次戰(zhàn)勝別國,這也是使用人的結(jié)果呀!獻(xiàn)公死了之后,惠公即位,荒淫暴亂,沉溺女色,國勢(shì)衰危,秦國隨意對(duì)我們侵略,直到奪取絳地十七里,這也是使用人的結(jié)果呀!惠公死后,文公即位,包圍衛(wèi)國,攻下鄴城,城濮一戰(zhàn),五敗楚國軍隊(duì),取得天下尊名,這同樣是使用人的結(jié)果呀!所以,只是君王沒有把人用好,而士兵沒有不能用的!”筒子聽完之后,深受啟發(fā),馬上去掉護(hù)衛(wèi)自己身體的盾、櫓,站在敵人的弓箭和石頭都能射到的地方,再次把戰(zhàn)鼓擂響,士兵果然趁著鼓聲奮起,士氣大振,大獲全勝。簡子感慨地說:“與其我得到革車千輛,不如聽到戰(zhàn)士燭過的一句話有價(jià)值!”
【闡釋】趙簡子兵臨衛(wèi)國都城之下,擂鼓號(hào)召士兵沖鋒,可士兵們卻沒有響應(yīng)。為什么呢?燭過進(jìn)諫分析廠,趙國歷史上三位君王由于用人不同,獲得了三種不同的治國效果。簡子悟到:原來是自己躲在掩護(hù)所里,沒有身先士卒,以實(shí)際行動(dòng)去鼓舞戰(zhàn)士。于是,立即撤去護(hù)衛(wèi)自己的盾和櫓,站在前沿陣地,再次擂鼓進(jìn)軍,士兵奮起,大獲全勝。簡子能采納一位士兵的忠言,并立即改正錯(cuò)誤,這種精神很可貴。
不以貴賤論是非
【原文】使言之而是,雖在褐夫芻蕘,猶不可棄也;使言之而非也,雖在卿相人君,揄策于廟堂之上,未必可用。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
(《淮南子·主術(shù)訓(xùn)》)
【譯文大意】假如說的話是正確的,即使出于平民,甚至是那些割草打柴的人,也不能不采納;假如說的話是錯(cuò)誤的,即使是出于卿相大臣,甚至是國君自己的口,在朝廷之上出謀劃策,也未必采用。正確和錯(cuò)誤之所在,不能憑借說話人身份的貴賤和地位的高低來確定。
【闡釋】只要言之有理,言之正確,就應(yīng)該虛心接受,而不論進(jìn)言者身份的高低貴賤;只要言而無據(jù),捕風(fēng)捉影,甚至是讒言誹謗,不管進(jìn)言者地位如何之高,也不能采納。故曰:“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貴賤尊卑論。”
國君齋戒受諫
【原文】天子齋戒受諫。司會(huì)以歲之成,質(zhì)于天子。冢宰齋戒受質(zhì),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zhì)于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齋戒受質(zhì),百官各以其成,質(zhì)于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zhì)于天子。百官齋戒受質(zhì),然后休老勞農(nóng)。成歲事,制國用。
(《禮記·王制》)
【譯文大意】天子沐浴齋戒,潔身凈心以接受群臣進(jìn)諫。司會(huì)把本年的簿記本子呈奉給天子,以便讓他對(duì)本年度的工作進(jìn)行評(píng)估,此時(shí)群臣總管冢宰也要沐浴齋戒,整潔身心,接受評(píng)估。大樂正、大司寇、司市官也要把本年度簿記本子呈上,隨從大冢宰一起接受天子的評(píng)量。同樣,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也要沐浴齋戒,整潔身心,接受評(píng)估。百官都把本年度的簿記本呈給三官,接受三官的評(píng)量。然后,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再把百官本年度的簿記本呈送給天子以接受天子的評(píng)量。百官齋戒沐浴,接受量評(píng),然后使年老者休息,慰勞農(nóng)民。完成了年終的工作,以制定下一年的國用。
【闡釋】天子百官于年終沐浴齋戒,對(duì)本年度的工作進(jìn)行全面的總結(jié)評(píng)估,說明年終總結(jié)是件十分嚴(yán)肅的工作,要高度重視。總結(jié)評(píng)估,一方面要對(duì)過去一年工作中的成績進(jìn)行肯定;另一方面要實(shí)事求是地找出差錯(cuò),分析原因,以便糾正;同時(shí)還要對(duì)下一度工作提出設(shè)想。上級(jí)對(duì)待總結(jié)評(píng)估,一要重視,二要認(rèn)真評(píng)估。發(fā)現(xiàn)不適之處,馬上加以改正;看到建設(shè)性提議,要迅速采納。根據(jù)實(shí)際情況,進(jìn)行適當(dāng)?shù)莫?jiǎng)懲。
頌而勿諂,諫而勿驕
【原文】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勿諂,諫而勿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
(《禮記·少儀》)
【譯文大意】當(dāng)天子的臣下,國君有過錯(cuò)可以進(jìn)諫但不能誹謗,多次進(jìn)言而不被采納,可以離開,但不能記恨;國君有功德可以歌頌但不能討好;一旦接受了自己的諫言也不能因此而驕傲自滿。國君若惰怠工作,就應(yīng)該振奮精神去幫助,政事廢馳,就應(yīng)該加以掃除更新。這樣的人才能稱得上社稷之臣。
【闡釋】下級(jí)對(duì)領(lǐng)導(dǎo)進(jìn)諫應(yīng)該有正確的態(tài)度和方式。領(lǐng)導(dǎo)有過錯(cuò),應(yīng)該敢于指出來,但要注意分寸;切忌借題發(fā)揮,發(fā)泄私憤,成為詆毀誹謗,這既不道德又違法。反之,領(lǐng)導(dǎo)有功績,應(yīng)實(shí)事求是地肯定,切忌阿諛奉承。如果進(jìn)言受阻,不能灰心喪氣,更不能懷恨在心,伺機(jī)報(bào)復(fù)或消極抵抗;在這種情況下,一走了之也不對(duì),要等待時(shí)機(jī),或采取迂回的辦法,輔之以必要的策略,力求使上級(jí)誠心接受。在進(jìn)言被接受并運(yùn)用于具體實(shí)踐,取得明顯成效的情況,切不可以功臣自居,驕傲自滿起來;這樣又會(huì)導(dǎo)致惰怠工作甚至瀆職行為。這種細(xì)致的剖析進(jìn)諫者的心態(tài),進(jìn)而提出進(jìn)諫者應(yīng)具有的適當(dāng)?shù)牟呗裕呛苡袃r(jià)值的。今天,如何處理好上下級(jí)關(guān)系,上下級(jí)應(yīng)該怎樣對(duì)待彼此的批評(píng)與被批評(píng),我們可以從中得到許多啟發(fā)。
晏子力勸阻葬狗
【原文】景公走狗死,公令外共之棺,內(nèi)給之祭。晏子聞之,諫,公曰:“亦細(xì)物也。特以與左右為笑耳。”晏子曰:“君過矣,夫厚葬斂,不以反民,棄貨財(cái)而笑左右,傲細(xì)民之憂,而崇左右之笑,則國已無望矣。且夫孤老凍餒而死,狗有祭;鰥寡不恤而死,狗有棺。行辟若此,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聚于百姓,而權(quán)輕于諸侯。而乃以為細(xì)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治狗。
(《晏于春社·內(nèi)篇諫下》)
【譯文大意】齊景公心愛的狗死了,他命令外邊準(zhǔn)備好棺材,宮里供給祭品以祭祀一番。晏子聽說這件事后,就向景公進(jìn)諫。景公回答說:“這是件小事,只不過給左右的人開開玩笑而已。”晏子說:“君王您錯(cuò)了,向百姓征收這么多的錢財(cái),又不用它救濟(jì)貧甲;而只是浪費(fèi)錢財(cái)以求左右人笑,這是無視百姓的憂愁,而尊崇左右的笑,這樣國家就沒希望了。再說百姓中的孤寡老人凍死餓死,而您的狗卻有祭祀,百姓中那些鰥寡孤獨(dú)的人您不去救濟(jì),而不幸死去,您的狗卻有棺材。君王行為如此乖僻,百姓聽說后必然埋怨,諸侯們聽說了,必然看不起我們國家。怨恨的情緒聚集于百姓,君王的權(quán)力被諸侯所看輕。而您卻把這看成小事,君王您再好好想一想這個(gè)問題吧。”景公說:“好”。于是,催促廚師趕快把狗肉做好供大家吃。
【闡釋】這個(gè)故事生動(dòng)地說明了晏子見微知著,諫而深刻有理的進(jìn)諫策略和風(fēng)格;景公能及時(shí)納諫,接受批評(píng),也不失為一位明君。分析景公納諫的原因,一是他個(gè)人的道德修養(yǎng);二是晏子析理透徹,人木三分,一針見血。一樁葬狗取樂小事,他卻能陳述其性質(zhì)、危害和后果,小則浪費(fèi)錢財(cái),大則亡國。晏子這種分析方法值得我們借鑒。
遒人以木鐸徇于路
【原文】先王克謹(jǐn)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guī),工執(zhí)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尚書叫軋征》)
【譯文大意】賢明的君主能夠小心地對(duì)待上天給他的警告,勤勞為政;臣子能夠奉行先王的常法,克盡職守。其他眾多的官員也都能忠心耿耿地來輔佐自己的君王。君臣之間關(guān)系處得這么好,說明君主和臣子都很賢明。于是諫言之路大開。每年孟春之季,派那些發(fā)布命令的官員以木鐸徇于路,以號(hào)召臣下,大膽地互相規(guī)諫,批評(píng)個(gè)人和朝政得失。即使是百工之人,也要執(zhí)其藝能之事來指出上層當(dāng)權(quán)者的錯(cuò)誤。如果發(fā)現(xiàn)有人玩忽職守,國家一定依據(jù)已有的法律進(jìn)行嚴(yán)懲。
【闡釋】賢明的君主如能勤勞為政,則其下屬也能克盡職守。君臣關(guān)系為什么能處理得這樣好呢?關(guān)鍵是廣開言路。這樣,君主能及時(shí)地改正錯(cuò)誤。而臣下呢?君主作出了榜樣,他一定要效仿的。
蹇叔哭秦師
秦穆公準(zhǔn)備出兵偷襲鄭國,上大夫蹇叔上前勸阻道:“不行。我聽說,偷襲別國城邑,用戰(zhàn)車不能超過百里,用步兵不能超過30里。作戰(zhàn)都是憑著士氣高漲、力量強(qiáng)大時(shí)到達(dá),進(jìn)攻才能勝利,而撤離才能迅速。現(xiàn)在要行軍幾千里,還要經(jīng)過其他諸侯國的領(lǐng)土。調(diào)動(dòng)大軍偷襲很遠(yuǎn)的國家,人馬趕得精疲力竭,而對(duì)方卻早已有了防備。請(qǐng)三思而后行。”穆公沒有聽他的勸告。于是蹇叔將遠(yuǎn)征的軍隊(duì)送到東城外,對(duì)主將孟明痛哭著說:“孟朋啊,我能看到你們出發(fā),卻看不到你們回來了!”他向隊(duì)伍中他的兒子鄭重告別說:“晉軍如果狙擊秦師的話,一定是在崤山。那兒有兩座山,南山有夏王皋的墳?zāi)梗鄙绞俏耐醣苓^風(fēng)雨的地方,地勢(shì)十分險(xiǎn)惡。你們一定會(huì)死在這兩山之間。我就到那里給你們收尸吧!”穆公知道了這事很不高興,叫人責(zé)備蹇叔:“我派兵出征,勝負(fù)未決,你卻哭著送行,這是在給我的軍隊(duì)哭喪啊。”蹇叔回答說:“我怎膽敢給軍隊(duì)哭喪。我已年老,兩個(gè)兒子都跟著軍隊(duì)一起出征。等到班師回國,不是他們戰(zhàn)死,就是我老死了,所以我才忍不住哭啊!”
秦師出征經(jīng)過周的都城,行進(jìn)到臨近晉國的時(shí)候,遭到晉軍的突然襲擊。晉國的先軫率軍將秦軍截在崤山,將他們打得大敗,秦軍的三個(gè)主帥都做了俘虜。當(dāng)他們幾經(jīng)周折終于回到秦國時(shí),秦穆公身穿白色喪服,到城外迎接,后悔沒有聽從蹇叔的意見,害他們吃了敗仗。
【闡釋】由于秦穆公犯了“勞師以襲遠(yuǎn)”的兵家大忌,又不聽蹇叔很有遠(yuǎn)見的勸告,終使秦師遭到了慘重的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