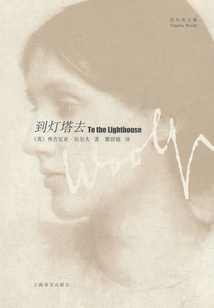
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第1章 譯本序
如果說(shuō)伍爾夫在《達(dá)洛衛(wèi)夫人》中描寫了她自己和她丈夫的一部分性格,那么她在一九二七年發(fā)表的長(zhǎng)篇小說(shuō)《到燈塔去》中描繪的是她父母的性格。她在日記中寫道:“這部作品將是相當(dāng)短的;將寫出父親的全部性格;還有母親的性格;還有圣·艾夫斯群島;還有童年;以及我通常寫入書中的一切東西——生與死,等等。但是,中心是父親的性格,……。”[1]這部小說(shuō)中的主要人物拉姆齊夫婦的原型,就是弗吉尼亞的父母。
《到燈塔去》的情節(jié)極其簡(jiǎn)單:拉姆齊先生全家和朋友們到海濱別墅去度暑假。拉姆齊夫人答應(yīng)六歲的小兒子詹姆斯,如果翌日天晴,可乘船去游覽矗立在海中巖礁上的燈塔。由于氣候不佳,詹姆斯到燈塔去的愿望在那年夏天始終沒有實(shí)現(xiàn)。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后,拉姆齊先生和子女、賓客重游故地,詹姆斯終于如愿以償,和父親、姊妹駕了一葉輕舟到燈塔去。但是歲月流逝、物是人非,拉姆齊夫人早已溘然長(zhǎng)逝。
這部小說(shuō)在結(jié)構(gòu)上分為三個(gè)部分。
第一部“窗”,占全書篇幅三分之一以上。時(shí)間是九月的某一個(gè)下午和黃昏;地點(diǎn)是拉姆齊的海濱別墅;人物包括拉姆齊夫婦,他們的八個(gè)子女、幾位賓客。客廳的窗口是溝通窗內(nèi)和窗外兩部分的一個(gè)框架;在窗內(nèi)給詹姆斯講故事的拉姆齊夫人,時(shí)刻意識(shí)到在窗外平臺(tái)上躑躅的丈夫和在草坪上作畫的莉麗。在這個(gè)平凡的下午,沒有發(fā)生任何不尋常的事情。莉麗把窗口的母子圖作為她油畫的背景,但她覺得眼花繚亂,把握不住眼前的景象。拉姆齊先生在夫人講故事時(shí)走過(guò)來(lái)干擾,并且堅(jiān)持說(shuō)第二天不會(huì)晴朗,不能到燈塔去,使小詹姆斯十分惱火。拉姆齊夫人給丈夫以安慰和鼓勵(lì),使充滿自卑感的塔斯萊先生恢復(fù)自信,促成了保羅和敏泰的姻緣,并且希望莉麗和班克斯結(jié)合。最后,可愛的黃昏在她主持的晚餐宴會(huì)上融洽無(wú)間的談笑聲中結(jié)束。
第二部“歲月流逝”,開始時(shí)書中人物準(zhǔn)備就寢,在這部分結(jié)束時(shí),一些同樣的人物又重復(fù)同樣的動(dòng)作,但是在時(shí)間上已相隔了整整十年。這十年時(shí)間,作者用一段簡(jiǎn)短而抒情的散文來(lái)加以描述,它所占的篇幅不到十分之一。似乎經(jīng)過(guò)一夜的睡眠,十年時(shí)間就朦朧恍惚地消逝了。在這段時(shí)間里,爆發(fā)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拉姆齊夫人逝世了,普魯難產(chǎn)而死,安德魯在戰(zhàn)爭(zhēng)中犧牲了,詩(shī)人卡邁克爾贏得了拉姆齊先生所沒有的聲譽(yù)。大戰(zhàn)結(jié)束后,拉姆齊一家重返別墅,其中有些人準(zhǔn)備來(lái)完成他們?cè)诘谝徊恐袥]有完成的業(yè)績(jī),以了心中的宿愿。
第三部“燈塔”,比第一部略短。拉姆齊先生決心到燈塔去,并且命令詹姆斯和凱姆同去。這一部分記述了航行過(guò)程中父子三人的內(nèi)心活動(dòng)。和這次航行并行交錯(cuò)的另一條敘事線索,是莉麗試圖完成以母子圖為背景的那幅油畫。拉姆齊先生躍上燈塔時(shí),在畫架旁邊目送他們的莉麗,隱隱約約地看到他們登上彼岸,她得到了創(chuàng)作的靈感,揮筆完成了她的畫。航行和繪畫圓滿結(jié)束,小說(shuō)也就此告終。
三部分的標(biāo)題各有其不同的象征意義。第一部的標(biāo)題“窗”是一個(gè)溝通內(nèi)外的框架,它象征拉姆齊夫人的心靈之窗。夫人憑她敏銳的感覺,由內(nèi)向外直觀地洞察人們的思想情緒;各種人物和事件,由外向內(nèi)投射到夫人的意識(shí)屏幕上來(lái)。第二部的標(biāo)題“歲月流逝”,象征時(shí)間、寂靜和死亡取得了暫時(shí)的主宰地位。夫人的一切努力,似乎都成了“轉(zhuǎn)瞬之間就會(huì)消失的彩虹”。第三部的標(biāo)題“燈塔”,象征拉姆齊夫人內(nèi)在的精神光芒。夫人在世時(shí),經(jīng)常意識(shí)到“那遠(yuǎn)遠(yuǎn)的、穩(wěn)定的光,就是她的光”。夫人死后,拉姆齊先生到燈塔去朝覲,莉麗完成她的油畫,都是為了紀(jì)念她。這說(shuō)明夫人雖死猶生,盡管經(jīng)歷了時(shí)間和死亡的嚴(yán)峻考驗(yàn),她的精神之光終未泯滅,仍長(zhǎng)存于人們的記憶之中。既然燈塔象征夫人的內(nèi)在精神,那么小說(shuō)的總標(biāo)題《到燈塔去》,就是象征人們戰(zhàn)勝時(shí)間和死亡去獲得這種內(nèi)在精神的內(nèi)心航程。三個(gè)部分在長(zhǎng)度上的變化“長(zhǎng)——短——長(zhǎng)”,恰巧合乎燈塔之光在黑夜中茫茫大海上照耀的節(jié)奏。
在西方音樂的“曲式學(xué)”中,有一種三部形式,其結(jié)構(gòu)的排列方式是A——B——A’:
《到燈塔去》的結(jié)構(gòu)恰恰和這樂曲的結(jié)構(gòu)形式相吻合。第一部以拉姆齊夫人為主題(第一主題);第二部以時(shí)間的流逝為主題(第二主題);第三部以對(duì)于拉姆齊夫人的回憶為主題(第一主題的再現(xiàn)和變奏)。這樣的結(jié)構(gòu)安排,在對(duì)比和勻稱的基礎(chǔ)之上,給人以美的感受。
《到燈塔去》體現(xiàn)出現(xiàn)代資本主義社會(huì)中生活的混亂本質(zhì)。女主人公拉姆齊夫人和主要配角莉麗與拉姆齊先生都清楚地意識(shí)到包圍著他們的混亂而無(wú)秩序的氣氛。他們被混亂所困擾,又力圖從一片混亂之中辨認(rèn)出一個(gè)清晰的圖案,摸索出一些規(guī)律,建立起某種秩序。
拉姆齊夫人被某些文學(xué)評(píng)論家看作夏娃、圣母或女神的化身。[2]然而,她是一個(gè)真實(shí)的、活生生的人。她是一位溫柔善良、富于直覺、風(fēng)姿綽約的夫人。她善于持家和社交,喜歡為親友排難解紛,促使他們和睦共處,并且經(jīng)常訪貧問(wèn)苦,助人為樂。就像莉麗所說(shuō)的那樣,要了解夫人的各個(gè)方面,你需要“有五十雙眼睛”來(lái)觀察,但還不足以窺其全貌。拉姆齊夫人意識(shí)到,“爭(zhēng)吵、分歧、意見不合、各種偏見交織在人生的每一絲纖維之中”。對(duì)于這些人生的缺陷,她總想全力加以補(bǔ)救。在晚餐桌上,她苦心孤詣地調(diào)動(dòng)每一個(gè)人的積極性,吸引大家參加談話,創(chuàng)造出一種融洽無(wú)間的友好氣氛。她終于在流動(dòng)變遷的日常生活潮流之外,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煥發(fā)著心靈之美的孤島,使參加晚宴的親友們感到,他們至少暫時(shí)處于一個(gè)受到庇護(hù)的穩(wěn)定的世界中。夫人的社交藝術(shù)和莉麗的繪畫藝術(shù)所追求的目標(biāo)是一致的——把混亂的日常生活整理得有條不紊,從而探索人生的意義,發(fā)掘深藏于表象之下的內(nèi)在真實(shí)。
莉麗必須作畫,因?yàn)樗灰环N“真實(shí)感”所驅(qū)使,她覺得非要用色彩和形態(tài)來(lái)把它表現(xiàn)出來(lái)不可。她企圖用藝術(shù)來(lái)給雜亂無(wú)章、變動(dòng)不居的生活創(chuàng)造出一個(gè)井然有序、穩(wěn)定鞏固的外貌。對(duì)她說(shuō)來(lái),“一支畫筆,就是這個(gè)充滿斗爭(zhēng)、毀滅和混亂的世界中唯一可以信賴的東西”。正是繪畫藝術(shù),使莉麗體會(huì)到:“在一片混亂之中,存在著一定的形態(tài);這永恒的歲月流逝(她瞧著白云在空中飄過(guò),樹葉在風(fēng)中搖曳),被鑄成了固定的東西。”莉麗說(shuō),“你”、“我”、“她”,都“隨著歲月的流逝而灰飛煙滅,什么也不會(huì)留存,一切都在不斷變化之中;但是,文字和繪畫卻不是如此,它們可以永存”。因此,莉麗的畫究竟是掛在大廳里還是扔在沙發(fā)下,是無(wú)關(guān)緊要的;就像詩(shī)人的文字一樣,只要它是真誠(chéng)地表現(xiàn)了某種被深深地感覺到的內(nèi)在的“真實(shí)”,就達(dá)到了目的。
不論復(fù)雜多變的生活使拉姆齊先生感到多么痛苦,他都能從他的工作中得到安慰。那就是企圖用理性和邏輯從混沌之中發(fā)現(xiàn)規(guī)律和秩序。他向人類理解力的極限進(jìn)軍,在朦朧之中辨認(rèn)出一個(gè)思想的模式,而那一片混亂幾乎將他壓倒。他在解答了“Q”之謎以后,又向新的未知領(lǐng)域“R”挺進(jìn)。他那種夸張的英雄主義,有時(shí)令人啞然失笑;但他自動(dòng)承擔(dān)探索真理的任務(wù),又令人肅然起敬。
作者企圖在《到燈塔去》這部書中探討人生的意義和自我的本質(zhì)。第一,是否有可能在不犧牲自我的個(gè)性特征這個(gè)前提之下,來(lái)獲得人與人之間的相互諒解和同情?第二,自我是否有可能在一片混沌之中認(rèn)識(shí)和把握真實(shí),在一個(gè)混亂的時(shí)代里建立起某種秩序?第三,自我是否有可能逃脫流逝不息的時(shí)間的魔掌,不顧死亡的威脅而長(zhǎng)存不朽?
作者通過(guò)莉麗等人物之口提出了這些疑問(wèn),并且通過(guò)情節(jié)的發(fā)展逐步回答了這些問(wèn)題。拉姆齊先生和夫人的性格截然不同,但是他們相輔相成、伉儷情深。拉姆齊夫人和塔斯萊先生的性格也迥然相異,但她也能給他以同情和幫助。不僅如此,她還促使互相反感的塔斯萊和莉麗的關(guān)系融洽起來(lái)。莉麗把她和塔斯萊在海濱的片刻友誼和諒解作為一種美好的回憶,“像一件藝術(shù)品一般”永遠(yuǎn)珍藏在心中。拉姆齊夫人就是一位把充滿分歧、爭(zhēng)論和混亂的人與人之間關(guān)系變得和諧融洽的藝術(shù)家。可見作者對(duì)第一個(gè)問(wèn)題的答案是肯定的。
夫人在她親友的小圈子里尋求真實(shí)、建立秩序。她取得的成功是有限度的。她所最器重的子女夭折了;她所促成的婚姻破裂了;莉麗和班克斯也未按照她的心愿結(jié)合。拉姆齊先生在理性的王國(guó)內(nèi)尋求真理和秩序,但他的哲學(xué)研究始終囿于“Q”的范圍,難越雷池一步。莉麗的油畫在心中構(gòu)思了十年,最后終于完成,但她自己未必滿意,亦無(wú)知音欣賞。個(gè)人的能力畢竟是有限度的,但只要在各自力所能及的范圍之內(nèi)真誠(chéng)地追求探索,人生還是有意義的。這就是作者對(duì)第二個(gè)問(wèn)題的回答。
在第二部中,混亂、寂靜和死亡似乎占了上風(fēng);拉姆齊夫人死了,她的一切努力似乎皆付諸東流。但是,在結(jié)尾部分,拉姆齊夫人的形象又在莉麗眼前浮現(xiàn)出來(lái),莉麗完成了她的畫,拉姆齊先生抵達(dá)了燈塔,這都說(shuō)明夫人的人格光芒像燈塔一般在人們的記憶中閃耀不滅。歸根結(jié)蒂,還是愛戰(zhàn)勝了死,人類的奮斗戰(zhàn)勝了歲月的流逝。這就是作者對(duì)第三個(gè)問(wèn)題的回答。這,也就是《到燈塔去》這部小說(shuō)的主題。
《到燈塔去》的第一個(gè)藝術(shù)特征,是敘事的主觀性,也就是從人物主觀的角度來(lái)敘述,作者本人毫不介入,采取隱退到幕后的超脫態(tài)度。伍爾夫在《雅各之室》和《達(dá)洛衛(wèi)夫人》中已經(jīng)使用了這種方法,在《到燈塔去》中,她對(duì)于這種方法的運(yùn)用更加爐火純青。現(xiàn)實(shí)主義小說(shuō)采用“全知角度”的敘述,優(yōu)點(diǎn)是作者洞察一切,敘述明白曉暢;缺點(diǎn)是作者夾在讀者和書中人物之間,指手劃腳,使人感到失真而浮淺。于是伍爾夫就廢棄了“全知角度”而改用“內(nèi)心獨(dú)白”、“內(nèi)部分析”和“感性印象”。“內(nèi)心獨(dú)白”是作者使用第一人稱,讓人物把他在某一特殊情景中的思想情緒、主觀感受用自言自語(yǔ)的方式直接敘述出來(lái),而且這往往是一種無(wú)聲的敘述,實(shí)際上是一種沉思冥想,是一種內(nèi)心的意識(shí)流動(dòng)。伍爾夫的短篇小說(shuō)《墻上的斑點(diǎn)》就是用內(nèi)心獨(dú)白寫成的。《到燈塔去》中也有這種筆法,如第三部中莉麗的獨(dú)白。《到燈塔去》的第一部,主要是使用“內(nèi)部分析”寫法,這種寫法仍用第三人稱,但作家不是站在她自己的立場(chǎng)來(lái)敘述,而是通過(guò)書中不同人物的視角來(lái)敘述,其內(nèi)容不是作家本人的想法,而是人物的觀念、感受和思索,這實(shí)際上是一種間接的內(nèi)心獨(dú)白。使用這種方法,角度可以不斷變換,十分靈活,而且可以使不同的角度互相補(bǔ)充,取得一種全面的效果。因此,伍爾夫特別愛用這種筆法。《到燈塔去》的第二部主要是“感性印象”,這是作者用她自己的語(yǔ)言來(lái)記錄純粹的五官感覺,描述對(duì)于客觀世界的主觀印象,人物受腦中不時(shí)掠過(guò)的各種印象的支配。伍爾夫的感覺既精細(xì)入微,又包羅萬(wàn)象,通過(guò)她那種力透紙背的印象主義筆觸,我們看到了各種畫面,聞到了花的香氣,聽到了大海的濤聲。
這部作品自始至終是從主觀的、內(nèi)省的角度來(lái)表達(dá)的。伍爾夫通過(guò)人物的意識(shí)流動(dòng)、自我感覺和沉思遐想,巧妙地表現(xiàn)人物的性格,展示人物的經(jīng)歷,勾勒人物的面貌。她對(duì)人物的觀察細(xì)致入微,甚至能夠捕捉意識(shí)之流中一剎那間的情緒波動(dòng)和思想轉(zhuǎn)折,把它如實(shí)地記錄下來(lái),從而把每個(gè)人物錯(cuò)綜復(fù)雜、變化萬(wàn)端的心理狀態(tài)描摹得淋漓盡致。因此,愛·摩·福斯特說(shuō):“伍爾夫是在原子和秒的宇宙中工作。”莫洛亞認(rèn)為,伍爾夫打開了讀者的眼界,“使他能在表面事件之下,發(fā)現(xiàn)那種剛剛能知覺到的思想和感情的活動(dòng)。”[3]
我們只要閱讀《到燈塔去》的開頭三節(jié),拉姆齊夫婦、塔斯萊和詹姆斯四個(gè)人物的性格就躍然紙上。我們對(duì)他們的衣著穿戴、外形輪廓,印象不很深刻;但是對(duì)于他們的個(gè)性特征、心理活動(dòng),卻了如指掌。拉姆齊夫人的慈母心腸,拉姆齊先生的嚴(yán)酷、求實(shí),詹姆斯的“戀母情結(jié)”和塔斯萊的“自卑情結(jié)”,都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伍爾夫使我們不但能夠把握住人物個(gè)性特征的總體,而且通過(guò)描寫“同情心的上漲和退縮”、瞬間印象、回憶和幻想等等,使我們對(duì)于人物心理上每一個(gè)微妙的變化,都覺得歷歷在目。
我不妨在這里舉兩個(gè)例子。塔斯萊給小詹姆斯?jié)娎渌蚱屏怂綗羲サ拿缐?mèng),使拉姆齊夫人覺得他十分討厭。他向夫人吐露心曲,敘述了自己的身世,贏得了她的好感。他不想去看馬戲,那股冬烘味兒,又叫她難受。夫人最關(guān)心的還是她的丈夫。拉姆齊先生需要犧牲別人來(lái)滿足他的虛榮心,塔斯萊做了犧牲品,她又有點(diǎn)幸災(zāi)樂禍。伍爾夫描寫拉姆齊夫人聽到她丈夫和塔斯萊在窗外的談話聲突然中斷,她的心情陡然變化,覺得海浪的節(jié)奏和響度也改變了,可謂神來(lái)之筆。伍爾夫就是這樣把握住瞬息萬(wàn)變的情緒和若即若離的現(xiàn)實(shí)之間的關(guān)系,把主觀的、內(nèi)在的精神世界和客觀的、外在的現(xiàn)實(shí)世界交織在一起。
塔斯萊陪拉姆齊夫人進(jìn)城,在出發(fā)時(shí)還充滿著自卑感,歸來(lái)時(shí)卻感到十分自豪,其中曲折微妙的心理變化過(guò)程,也都寫得絲絲入扣。這段插曲看來(lái)似乎是在寫塔斯萊,實(shí)際上是通過(guò)他主觀感覺的變化來(lái)烘托拉姆齊夫人的性格。伍爾夫?qū)懭宋锏男睦砘顒?dòng),就像抽絲剝繭一樣,一層又一層地向縱深挖掘。
從敘事的主觀性,又派生出這部小說(shuō)的另外三個(gè)藝術(shù)特征——象征性,抒情性,主觀時(shí)間和客觀時(shí)間的交叉、對(duì)比。
意識(shí)流小說(shuō)家使用主觀性的敘事方法來(lái)探索內(nèi)心的奧秘、發(fā)掘內(nèi)在的真實(shí),就免不了要借助于象征。因?yàn)椋⒚畹男睦砘顒?dòng)本來(lái)就是捉摸不定、只可意會(huì)、難以言傳。所以,柏格森說(shuō):“我們研究純粹情緒性的心理狀態(tài)時(shí),……我們就‘先天地’知道:除非通過(guò)某種象征的表示,我們幾乎無(wú)法數(shù)出它們。”[4]
后期象征派詩(shī)人托·斯·艾略特提出,要通過(guò)“客觀對(duì)應(yīng)物”的象征暗示,來(lái)表現(xiàn)思想情緒。伍爾夫受到他的影響,把這種方法運(yùn)用到她的意識(shí)流小說(shuō)之中,通過(guò)各種比喻、意象、聯(lián)想,甚至結(jié)構(gòu)來(lái)達(dá)到象征暗示的效果。《到燈塔去》這部小說(shuō)的整個(gè)結(jié)構(gòu)和各部分的標(biāo)題都具有象征意義。這一點(diǎn)我在前面已經(jīng)作了分析。
在《到燈塔去》第二部中,作者經(jīng)常用象征暗示來(lái)表達(dá)主觀的感覺印象。例如,她把海風(fēng)描述為“探頭探腦”的幽靈,把跛足的管家婆的行動(dòng)描寫為“像一條船一樣在大海里顛簸蕩漾”,“看上去就像一條熱帶魚在映出萬(wàn)道金蛇的一泓清水中穿梭游泳”。這種寫法,宛如象征派的詩(shī)歌,具有極其強(qiáng)烈的主觀色彩。它的藝術(shù)效果,使我們想起國(guó)畫中“但求神似、不求形似”的“寫意”畫。
有時(shí)候,象征手法也會(huì)產(chǎn)生一種模棱兩可、撲朔迷離的感覺。例如,伍爾夫在第二部中描寫寂靜的空屋,其中有一句是:“蒼蠅在充滿陽(yáng)光的房間里結(jié)成了一張網(wǎng)。”讀者也許會(huì)奇怪:蒼蠅如何能結(jié)網(wǎng)?這里就需要使用一下我們的想象力。也許是空屋久無(wú)人跡,群蠅在陽(yáng)光下飛舞,密如蛛網(wǎng);也許是空屋無(wú)人打掃,屋角的蛛網(wǎng)上黏了好多死蠅。如果用傳統(tǒng)的客觀敘述手法,寫成“群蠅在充滿陽(yáng)光的房間里飛舞”或“屋角的蛛網(wǎng)上粘滿了死蠅”,就削弱了主觀色彩,使我們沒有使用想象力的余地,讀起來(lái)就索然無(wú)味了。因此,象征派詩(shī)人瑪拉美說(shuō):“要明白地指出對(duì)象來(lái),無(wú)異于把詩(shī)給予我們的滿足削弱了四分之三。”[5]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伍爾夫不僅借用了詩(shī)歌中的象征手法,而且借鑒了音樂中的“主導(dǎo)動(dòng)機(jī)”,用反復(fù)出現(xiàn)的“主導(dǎo)意象”來(lái)象征人物的性格。在《雅各之室》中,伍爾夫就開始使用這種方法。在《到燈塔去》中,她又進(jìn)一步運(yùn)用這種方法來(lái)表現(xiàn)拉姆齊夫婦的性格,實(shí)際上也就是她父母的性格。
拉姆齊夫人……立即迸發(fā)出一陣能量的甘霖,一股噴霧般的水珠;……她生氣蓬勃、充滿著生命力,好像她體內(nèi)蘊(yùn)藏的全部能量正在被熔化為力量,在燃燒、在發(fā)光……。那個(gè)缺乏生命力的男性,猛然躍入這股甘美肥沃的生命的泉水和霧珠中去,就像一只貧乏而空虛的厚臉皮的鳥嘴,拼命地吮吸。[6]
拉姆齊夫人生就一副菩薩心腸,她對(duì)周圍的一切人都十分關(guān)切,特別是對(duì)于她的丈夫,更是無(wú)微不至地關(guān)懷,時(shí)常給他以安慰和愛撫,使他暴躁的情緒平靜下來(lái)。伍爾夫把這種慈母胸懷比作化育萬(wàn)物的雨露、甘霖。拉姆齊先生是個(gè)自我中心的人物,他在學(xué)術(shù)上太過(guò)分的抱負(fù)難以實(shí)現(xiàn),精神上受了挫折,就要到他的夫人那兒去求得庇護(hù)與安慰。因此伍爾夫把他比作拼命吮吸甘霖的鳥嘴。這兩個(gè)“主導(dǎo)意象”在《到燈塔去》中反復(fù)不斷地出現(xiàn),成了這兩個(gè)人物性格的象征。她又用另外一個(gè)意象來(lái)象征他們兩人之間夫唱婦隨的親密關(guān)系:“就像同時(shí)奏出一高一低兩個(gè)音符,讓它們和諧地共鳴所產(chǎn)生的互相襯托的效果。”弗吉尼亞的姐姐文尼莎認(rèn)為,《到燈塔去》一書中對(duì)于她父母性格的刻劃,是非常成功的。
勃盧姆斯伯里的青年作家莫蒂默說(shuō):“誰(shuí)也沒寫出過(guò)弗吉尼亞·伍爾夫那樣好的散文。人們羨慕她所看到的世界是如此美麗——她眼中‘看到的盡是一塊塊翠玉和珊瑚,好像整個(gè)世界都是寶石鑲成的’。”她受到羅杰·弗賴伊的影響,敘事寫景不是對(duì)于外部世界自然主義的描摹或“照相式”的再現(xiàn),而是要像后印象派的繪畫那樣,表現(xiàn)出有強(qiáng)烈個(gè)性的自我眼中所觀察到的世界,追求獨(dú)特的意境和藝術(shù)效果。這使她優(yōu)美抒情的文字帶有與眾不同的詩(shī)情畫意,甚至看到桌上一盤普通的水果,也會(huì)聯(lián)想到海神的宴會(huì)和酒神的葡萄。她對(duì)于遣詞造句,又處處精心推敲斟酌,不但注意到結(jié)構(gòu)的勻稱,甚至注意到音節(jié)的對(duì)稱和諧,產(chǎn)生一種音樂和詩(shī)歌的效果。
西方評(píng)論家們普遍認(rèn)為,《到燈塔去》的第二部,是伍爾夫獨(dú)特的抒情風(fēng)格的典范。多·斯·富爾寫道:
她那印象主義的細(xì)膩筆觸,驚人洗煉的描寫,在《到燈塔去》這部熱情洋溢的小說(shuō)中,達(dá)到了臻于完善的地步。海洋與黑夜渾然一體,時(shí)間圍繞著一個(gè)中心流逝。晶瑩的海水,以其濤聲和波浪,賦予日常生活、巖石結(jié)構(gòu)、布滿水洼、流沙和海風(fēng)的世界以節(jié)奏。創(chuàng)造了友善、微妙而又敏感的氣氛。表現(xiàn)了永恒的情趣。[7]
同時(shí),我們也應(yīng)該注意到,伍爾夫那種娓娓談心的文體,是和她的意識(shí)流技巧默契配合的。作品中的對(duì)話有時(shí)不加引號(hào),宛如人物無(wú)聲的思索。有時(shí)對(duì)話突然中斷,語(yǔ)氣突然改換,文字突然轉(zhuǎn)折,透露出人物的思維或情緒發(fā)生了波折或變化。我們閱讀伍爾夫的文字,就好像作者在對(duì)我們低聲細(xì)語(yǔ),和我們促膝談心,在不知不覺之間,帶領(lǐng)我們進(jìn)入了人物的內(nèi)心世界,隨著他們一塊兒思潮起伏,分享他們的喜怒哀樂,體驗(yàn)到意識(shí)流手法所造成的特殊效果。可見伍爾夫優(yōu)美抒情的文體和意識(shí)流技巧是珠聯(lián)璧合、渾然一體的。
柏格森把人們常識(shí)所公認(rèn)的時(shí)間觀念稱為“空間時(shí)間”,把它看作各個(gè)時(shí)刻依次延伸的、表現(xiàn)寬度的數(shù)量概念。他認(rèn)為“心理時(shí)間”才是“純粹的時(shí)間”、“真正的時(shí)間”,它是各個(gè)時(shí)刻互相滲透的、表現(xiàn)強(qiáng)度的質(zhì)量概念。他認(rèn)為,我們?cè)绞沁M(jìn)入意識(shí)的深處,“空間時(shí)間”的概念就越不適用[8]。柏格森的“心理時(shí)間”理論,對(duì)意識(shí)流小說(shuō)家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他們“在寫書時(shí)可以像一把扇子似地把時(shí)間打開或者折攏”[9],或者把幾分鐘時(shí)間擴(kuò)展到好幾頁(yè)篇幅,或者把一段較長(zhǎng)的時(shí)間加以壓縮,或者把眼前所看到,所回憶,所想象的現(xiàn)在、過(guò)去、將來(lái)的各種情景交織、穿插、匯集起來(lái),彼此交錯(cuò)地呈現(xiàn)在讀者眼前,取得一種特殊的戲劇化效果。伍爾夫在《達(dá)洛衛(wèi)夫人》中就曾使用這種時(shí)間處理方法。有些學(xué)者認(rèn)為,可能她并未讀過(guò)柏格森的哲學(xué)著作,也許她是通過(guò)閱讀普魯斯特的意識(shí)流小說(shuō),間接地受到了柏格森的影響[10]。
在《到燈塔去》這部小說(shuō)中,伍爾夫?qū)τ跁r(shí)間的特殊處理方法,比前面一部小說(shuō)中的更加引人注目。此書的第一部,從客觀時(shí)間來(lái)說(shuō),只有一個(gè)下午和黃昏,但從“心理時(shí)間”來(lái)看,由于記錄人物的意識(shí)流動(dòng),穿插了許多回憶和想象,現(xiàn)在、過(guò)去、將來(lái)交錯(cuò)在一起,因此就顯得很長(zhǎng)。第二部從客觀時(shí)間來(lái)說(shuō),有十年之久,但是因?yàn)榭瘴轃o(wú)人居住,從“心理時(shí)間”的角度來(lái)看,它不過(guò)是短暫的瞬間而已。在第一部的末尾,夫人在餐桌上回憶起二十年前她與曼寧一家的友誼,這過(guò)去的景象如同靜止而美麗的“夢(mèng)幻世界”一般,保存在她的記憶之中,回想起來(lái),“就像重新閱讀一本好書”。在這個(gè)例子中,拉姆齊夫人的思緒飄流到往昔的歲月中去,它是清清楚楚地被包含在客觀時(shí)間的框架之中的。但是,有時(shí)伍爾夫在描述人物的回憶或想象之時(shí),并不用傳統(tǒng)的方式來(lái)標(biāo)明時(shí)間從當(dāng)前客觀時(shí)刻的轉(zhuǎn)移。例如,第一部中塔斯萊陪拉姆齊夫人進(jìn)城那一段,似乎是按照外部的客觀時(shí)間在直接敘述。其實(shí)不然。塔斯萊堅(jiān)持說(shuō)第二天氣候不佳,不能到燈塔去。拉姆齊夫人心中覺得他討厭:“真的,他可說(shuō)夠了……她對(duì)著他瞧。他真是個(gè)丑八怪,孩子們說(shuō)……”從孩子們的評(píng)語(yǔ),夫人想到他的咬文嚼字和拘泥于事實(shí)。接著,夫人注意到,孩子們吃完午飯之后像小鹿一般溜走了。這使她想起,有一天當(dāng)孩子們走后,塔斯萊跟著她進(jìn)了餐廳,她感覺到他手足無(wú)措的窘態(tài),就請(qǐng)他陪伴她進(jìn)城。接下去的好幾頁(yè),詳細(xì)地描寫這兩個(gè)人物在進(jìn)城途中的內(nèi)心感受。
但是,作者并未指明這段插曲是在意識(shí)屏幕上出現(xiàn)的回憶畫面,而不是眼前發(fā)生的事實(shí)。但是,當(dāng)讀者順著塔斯萊意識(shí)流動(dòng)的線索經(jīng)歷了整個(gè)插曲之后,站在窗前的塔斯萊對(duì)于天氣的評(píng)論,及時(shí)地打斷了拉姆齊夫人的思路,使她回到當(dāng)前的現(xiàn)實(shí)中來(lái)。作者在第二小節(jié)中寫道:
塔斯萊站在窗前說(shuō),“明兒燈塔去不成了。”討厭的小伙子,拉姆齊夫人想道:為什么老是說(shuō)那句話呢?
這里雖然沒有像傳統(tǒng)小說(shuō)那樣使用任何標(biāo)點(diǎn)符號(hào)或附加說(shuō)明來(lái)指出前面使用了“心理時(shí)間”,但細(xì)心的讀者可以不很困難地依據(jù)拉姆齊夫人的聯(lián)想和第二小節(jié)中客觀時(shí)間的框架,判斷出上面一段插曲顯然是屬于主觀的回憶。
然而,在伍爾夫筆下,客觀時(shí)間和主觀時(shí)間的區(qū)別是極其顯著的:外界的各種事件,在整部小說(shuō)中只占極小的篇幅,而主觀意識(shí)屏幕上對(duì)這些外界事件的反映,卻浮想聯(lián)翩,發(fā)揮得淋漓盡致。在《到燈塔去》全書中所表現(xiàn)出來(lái)的主要“真實(shí)”,是染上鮮明主觀色彩的內(nèi)在真實(shí)。在小說(shuō)的第三部,詹姆斯終于來(lái)到了燈塔腳下,呈現(xiàn)在他眼前的是赤裸裸的筆直的塔身,上面有小窗,周圍曬著衣服,雖然他多年來(lái)在心目中還存在著另一幅燈塔的圖景:“一座銀色的、煙霧朦朧的塔,有一只黃色的大眼睛。”他覺得兩幅圖畫都是精確的,兩種景象都是“真實(shí)的”。“因?yàn)椋澜缟蠜]有任何東西只是簡(jiǎn)單的一回事兒。”作者的用意很清楚:每一件事物都有其客觀的和主觀的形態(tài),前者是物質(zhì)的、軀體的,后者是精神的、心靈的。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伍爾夫本人,顯然是偏重于精神方面的唯靈論者[11]。
如果我們把伍爾夫的三部意識(shí)流小說(shuō)加以比較,我們就會(huì)發(fā)現(xiàn):《雅各之室》雖然富有詩(shī)意,但是枝節(jié)過(guò)多,主人公雅各有點(diǎn)兒虛無(wú)縹緲;《達(dá)洛衛(wèi)夫人》雖然克服了前面一部小說(shuō)太過(guò)空靈的缺點(diǎn),但又顯得過(guò)于模式化;只有《到燈塔去》在詩(shī)的境界與現(xiàn)實(shí)的生活之間維持著微妙的平衡,達(dá)到了更高的藝術(shù)水準(zhǔn)。在《到燈塔去》這部小說(shuō)中,客觀時(shí)間和心理時(shí)間、主觀真實(shí)與客觀真實(shí)、直接描述和象征暗示,錯(cuò)綜復(fù)雜地交織在一起。因此,既需要有五十雙眼睛來(lái)觀察一個(gè)人物,又需要從不同的角度來(lái)觀察一座燈塔;對(duì)于顯然非常簡(jiǎn)單的事件,也可以有截然不同的觀念和感受。具有多方面性格的人物,沉思著超越時(shí)空限制的各種問(wèn)題;帶有詩(shī)情畫意的抒情語(yǔ)言;富于象征意義的結(jié)構(gòu)形式——所有這些因素,使《到燈塔去》成為伍爾夫意識(shí)流小說(shuō)中的壓卷之作。評(píng)論家布萊克斯東說(shuō):“在閱讀了《燈塔》之后去閱讀任何一本普通的小說(shuō),會(huì)使你覺得自己是離開了白天的光芒而投身到木偶和紙板做成的世界中去。”“這本書內(nèi)涵異常豐富,……充滿著思想,充滿著感情……它是一個(gè)活生生的整體。”[12]我認(rèn)為,這是一個(gè)十分恰當(dāng)?shù)脑u(píng)價(jià)。
瞿世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