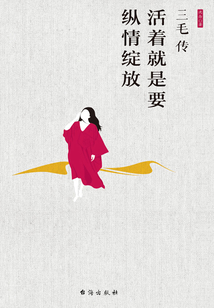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前言
1943年3月,三毛出生于重慶。她叛逆,敏感,極端,自閉,從幼年時代就散發出跟其他兄弟姐妹與眾不同的個性。或許是因為想成為一名運動員,最終卻成了一名律師,三毛的父親陳嗣慶在對女兒的教育上給予了最大的寬容。比如小時候的三毛因為覺得“懋”字難寫,就將自己的名字改為陳平;因為感覺被數學老師侮辱,就再不肯上學,一度休學在家……誠如三毛所說:“學校并沒有給我什么樣的教育,而且,我一直希望離家出走,見識更廣闊的世界。”她這樣說,父母和家庭也都由著她這樣做了。
三毛在幼年即顯示出文學創作上的天賦,成為她離家出走的底氣。三毛的姐姐陳田心對此評價:“妹妹從小作文就很好,遣詞造句的能力極強,更重要的是有思想。她的感情流露于筆尖,從文章到家信,都相當自然不造作。”三毛從未刻意想過成為一名作家,她因出版書籍而走紅是一種偶然。但她在文學上的天賦以及行為上的自由,令她的走紅成為一種必然。同時,她的文字和行為都體現出身體和靈魂的自由,她畢生追求真善美以及人性美好、渴望愛與自然、渴望平凡的風格特質,令她從一眾作家中脫穎而出,并被追認為“現代文藝女青年的創刊號”。
三毛淡泊名利,沒有過分關注過自己的寫作成就,卻在寫作上獲得巨大成功。她說她的寫作完全是游于藝:“從沒想到會有這么多的讀者,也很少想到稿費,只要文章刊登出來,看到排版鉛字,就是一種快樂。”她對寫作的這種淡薄,以及不求結果的態度,是很多文藝青年所欽羨的。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是文藝青年奉為圭臬的游戲規則,卻只有三毛一個人用畢生的時間去身體力行,并且收效甚大。在今天這個無比流行“成功學”和信奉“金錢至上”的年代,幾乎沒有一個文藝青年敢像三毛一樣,專心致志去做自己的文藝夢。因此,大部分人心中的夢想飄在天空里,只有三毛在腳踏實地實踐著。
再看三毛的穿著:白色麻紗綴花上衣,藍色牛仔褲,衣服往往是舊的、老的,隨心搭配。她根本不屑什么新潮、時尚,連結婚都只是穿一件藍色的裙子,把廚房拿來的芹菜插在頭上當花使。這種隨性隨心的作風,正體現了文藝青年的靈魂核心——自由。三毛不喜交際與熱鬧,而是喜歡在大自然中深思反省,這是靈魂自由的極致體現。何況她不惜為了追求原始的真善美,摒棄喧囂繁華的都市生活,與戀人定居在四下荒涼、環境嚴酷的撒哈拉沙漠。
三毛酷愛寫信,對朋友真誠,不管是誰,一旦她心里認定對方,都要在信中將自己的近況甚至一些心底事和盤托出。甚至通常會在寫完一封短的信件后,第二天起床再補上一封長的信。三毛在信中毫不掩飾當日當時的心境,對任何人都沒有心防,是真正的至真至純。
三毛還有著令文藝青年稱羨甚至妒忌的愛情傳奇。與荷西相識十二年、相戀六年,在荷西死后,郁郁寡歡的她最終選擇自殺追隨。三毛就如愛與美的化身,一生都在追求真正的人性之美。試問,誰能做到如三毛般純真不世故?
面對愛情,三毛從不顧忌世俗看重的部分——身份、地位甚至年齡。荷西死后,三毛更加封閉自己,她曾經因為愛情而熱愛這個世界,后又因為愛情對所有人甚至家人變得無情。在她身上,仿佛能看到水火相容。
全世界的人都在長大,變得成熟。只有三毛和迷戀她的文藝青年們,還活在對愛情的憧憬里,還肯為愛情付出一切。
三毛這種固執的文藝特性是與生俱來的,更是父親陳嗣慶始終默許的。在某個離家的早上,三毛給父母留下一封辭別的信件。換作別的父母,早已崩潰,陳嗣慶卻留言給女兒:“為父的我,跟你在許多心態上十分接近,除了公務之外,十分渴望一個人孤獨地生活。我想,我之所以不能‘了’,并非因為那么多的責任,我只是怕疼。你的‘了’,也不是沒有責任,是你比我能忍痛而得到的。”
三毛的感情是真摯的,她從不掩藏。她說自己筆下的故事,都是真實發生過的,因為“虛假的我寫不來”,并且承諾,如果有天三毛不寫了,并不是她不肯寫,而是沒有更多真實的話可以說。
三毛是個自信的人,這是她能全然不顧世俗的眼光、以一己之力搏擊人生的基礎。她說自己是一個賭徒,只要想做的事沒有辦不到的。“山不過來,你就自己走過去”是她的人生信條,也給很多瘋狂迷戀她的人以力量。
三毛一生追求愛、自然與平凡,她說她恥于成為一個特殊的人。但她偏偏擁有極為特殊的人生,這就與她喊出的口號形成一種反差。她要平凡,但她注定不平凡,甚至處于巔峰的她極力呼吁要以平凡為美,這是令文藝青年愛她的又一大理由。多讀幾遍三毛的作品,你就會發現,她的作品就是她的一生。不管是在撒哈拉,還是在中南美洲;不管是當一名作家,還是當一名家庭主婦,三毛對生活的熱愛、對美的追求是一貫到底的。她心懷赤誠,熱烈美好,永遠是你我17歲時的模樣。
凡人不能留住時光,只有圣人才行。三毛像個圣人,她不按世俗標準成長,不會隨意將自己塑造成適應世界的模樣。最令人稱羨的是,她沒有走一條保險安全的路,卻也活得成功漂亮。
孤獨,自由,熱烈,無情,這些看似矛盾的特質被三毛像變魔術一般,很好地融合于一身。
三毛遼闊如“遠方”。每個心中充滿文藝夢想卻沒勇氣走出去的人,都將肉體凡胎留在應盡的責任、日復一日的奔波中受苦,而那渴望自由飛翔的靈魂,早已追隨三毛飛往大千世界流浪。只要是對遠方和愛還有渴望的人,就忘不了三毛。
人們艷羨她不喜歡上學就休學,想去遠方就用14年去流浪;艷羨她可以以文字為生、跟相愛的人定居夢中之地的浪漫愛情;甚至艷羨她別具一格的長裙長發、抽煙的姿勢以及黑白照片里的灑脫眼神。連她的自殺,都可以被神化為一種有勇氣離開世界的極致自由。
年輕的文藝青年愛極了她的任性與瀟灑,年長有經驗的文藝青年愛極了她表象之下所指向的人性之美、生命之美。
中國近代史上,曾出現過多少文藝范十足的女作家:張愛玲猶如青灰色天空里的一彎滄月,薄涼悲憫,淡漠地眼望蕓蕓眾生;蕭紅好似青銅色池塘里的一朵浮萍,孤單凄苦,感同身受地體察人間百態;亦舒則是20世紀90年代繁華香港的精致女性,不甘平凡,遺世獨立,“體面”是最重要的;瓊瑤好比女兒閨房里干了又濕的一塊手帕,把一個只屬于少女的夢重復又重復。
只有三毛,不回避、不抗拒,真誠地渴望做一個普通人。她寫尋常人家的生活,文學不是她逃離和擺脫平凡現實的武器。相反,她熱愛自己所處的一切環境。她那自由的天性、奔放熾熱的情感以及走遍萬水千山追逐真理的決心,普世而不拘泥于時間,無論是在少年、成年還是在老年,都有屢屢重溫的珍貴價值。
所以,多讀幾遍三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