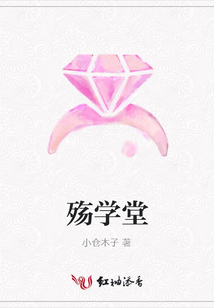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初春,一片春意盎然,柳枝剛發出嫩芽,一抹新綠搭在岸邊石橋下,蜻蜓落在枝上,柳尖向下微微碰到湖面,激起一小圈漣漪。石久鎮一如既往的熱鬧,今年初春不少新鋪子開張,鞭炮聲噼里啪啦隔三差五就響一回,石久鎮不大卻一應俱全,零零散散的小吃沿著街邊一路鋪到街對頭,糖耳朵,爾耳卷,于蘭豆,商販一個個笑顏滿面的吆喝著,明亮的聲音里也夾帶著不少那些蜚短流長的是非,哪個小鎮沒有些搬弄是非的三姑長五姑婆,趁著春意,曬著太陽,說的口水橫飛,什么光怪陸離的事情到他們嘴里都說的那叫一個真,就跟親眼看見了似的。
“陳家的媳婦回娘家了,聽說是因為他相公在青樓夜夜笙歌,弄得媳婦一氣之下回了娘家,這才干忙著跑到娘家去要人,著一去都去了大半個月了,看來是死活不肯回來呀。”
“是嗎?這些個男人就是喜歡花天酒地,沒幾個正經的東西。”
茶樓下許銘賢聽得“嘖嘖”,一邊搖頭一邊往自己杯中倒茶,這些個喜歡嚼人舌根的婦人,什么事情都讓他們說的天花亂墜,越說越離譜,明明上個月陳家帶著陳家媳婦提著一袋子桂花糖上了先生家,笑盈盈的說是陳家媳婦有喜了,想回娘家住幾天,先來給先生送喜糖,便等孩子出世,讓孩子跟著兩位先生好好念書。許銘賢當時就在先生院落,一雙眼睛看的真真的,到這些婦人嘴里竟成了東家長西家短的是非,心里一陣陣發笑。
“林氏也是好生奇怪啊。”一個婦人先提起。
“是啊,是啊。”后面你一句我一句的又起了新話題。
“一個繡娘帶個孩子還算正常,但是家里兩個男人,算是怎么回事?“
“著還不算什么,昨天我去林氏家取繡緞,親耳聽見林氏的孩子管白先生和甄先生叫爹爹。“
“啊?!“一片驚呼聲四起“兩個都叫爹爹?”
“是啊,”那婦人講得有滋有味,津津樂道,“一夫二妾的事我見的多了,這一女嫁二夫還是同時,還真是沒見過。”語畢,一群婦人笑的前仰后合。
“王夫人。”許銘賢終是聽不下去,重重放下茶壺,一個冷眼瞥向正說的開心的婦人“你家方兒的書是念好了,不必再去學堂了?”
一群婦人忙才回頭瞧見許銘賢坐在背后的茶館,不知聽了多久了,一臉尷尬,連解釋的話都吭哧半天說不出口,干脆陪個笑臉,一哄而散了。
誰人不知,這許銘賢與林氏家人頗有往來。這鎮上也是每家每戶看林氏家里都心生幾分疑惑,想必著鎮上唯一知道這種維持著奇妙關系家庭的原因,也就只有許銘賢了。
兩位教書先生,一位繡娘,一個孩子,四人住一間小院。孩子管繡娘叫娘,管兩位先生都叫爹,更奇怪的是,四人四姓。誰家不會多心?誰人不會猜疑?婦人更是喜歡站在墻頭嚼舌根,這種家庭關系,越嚼越有嚼頭。
“喜歡說便讓他們說去,我們現在挺好。”甄先生總是摸著麟兒的頭對許賢銘說,一臉的淡然。看的是麟兒的臉,答的是許銘賢的話,但似乎是說給另一個人聽。
許賢銘看著走遠的婦人們,放下了茶錢,起身向魚市走去。
傍晚,初春的的太陽一落山,便涌上一陣涼意,許賢銘緊了緊領口,手里提著下午才買的鯉魚大大方方的邁進了林家的大門。
白先生坐在桌旁,抓著麟兒的胳膊,一臉笑意問他“你甄爹爹教你的《上邪》會背了沒有?”麟兒不過四歲半,這么小的孩子怎么能懂《上邪》這樣的句子,許賢銘卻奇怪,每次聽見先生們問他總是這一首,卻又沒有逼迫他一定要背。麟兒支支吾吾答不上來,白先生就抓著他手臂就是不讓他屁股挨上凳子,笑著逗他“麟兒不會背,爹爹不讓麟兒吃飯。”麟兒卻一點也不怕,只裝出一臉無辜相,一雙水靈靈大眼睛望向站在桌旁正擺碗筷的甄先生“甄爹爹,白爹爹他欺負我。”
“爹爹說他,不會背也讓我們麟兒吃飯。”
“你說話算數,還是我說話算數?”白先生一眼瞪過去。
“當然是我算數。”
“憑什么,你是膝蓋又癢癢了吧?”
“憑我是‘真’爹爹。”甄先生用一根筷子敲了一下碗沿,立刻發出一聲清脆的聲響。
林氏從屋里笑著出來,一眼看見正往里走的許銘賢,
“銘賢還帶魚來了?”趕緊上前接過來“我都做好了,你明天來吃吧,玲瓏姐明天給你做魚湯。”
“好嘞。”許賢銘到也不客氣。“麟兒又背不出詩啦?那不讓吃飯。”他自顧自坐下,絲毫不將自己當客。
“呵呵,”麟兒一副賊笑“‘真’爹爹說了,不用背也能吃。”
白先生一計癢癢抓在麟兒腰間,又是一陣咯咯的笑聲。
小院落不大,一張石桌,六把木椅,兩棵海棠,一張長椅倚在樹下,六副碗筷,多一副也拿不出來,家里就準備這么多。四葷,兩素,一湯,兩壇陳釀。兩個爹爹,一位娘,一個哥哥,一個小子滿院跑,一陣風吹過,一樹花瓣落下,滿地緋紅。
這種家庭關系確實奇怪,但總是有說不出的溫馨,又包含著說不出的心酸。
“今天我聽王夫人他們又在議論了。”許銘賢喝了一口酒,說道“在外還是別讓麟兒喊爹爹了,兩個爹爹著實怪了些。”
“行。”白先生爽快的答應,惹來林氏和甄先生一陣目瞪口呆。
“麟兒不叫他,”白先生眼睛又瞇起一條線,對著麟兒,指著自己旁邊坐著的甄先生“但還是要叫我。”又是玩笑話,天塌下來,爹爹和娘親都要還是要叫的。
“憑什么呀!我是‘真’的。”甄先生聲調都高了一度,桌下面,許銘賢真切的看著甄先生撒嬌似的扯白先生的衣角。
明明只大銘賢幾歲,還不到而立之年。稱了先生好似要老個幾十歲,私底下還不是一副玩心頗重的樣子。
這家里的事,銘賢最清楚,整個鎮上再找不到比他更清楚的人了。
銘賢剛認識他們的時候,是他們剛在書館教書的時候,銘賢那時候還不叫銘賢,后來因為甄先生說,又不當臣做宰,要那么賢明有何用?銘諸肺腑,賢聲遠答,銘賢比賢明好。就這么許賢明就變成了許銘賢。
那時候銘賢剛剛十七歲,便是不想考功名也想跟著先生多學些學問,他人都笑話他,這個年紀還進學堂學學問?要考到什么時候去?怕不是考的兒子都會打醬油了還在考?甄先生到是爽快
“也是,在學堂里學是年紀大了些。”轉眼看向白先生的方向
“不如讓在家里學吧?”似是等一個準許。
便就這樣,銘賢即是先生的學生,又是他們的知己,打從去年開始,又成了他們的生意伙伴。
曾經許家也是有錢人家,綢緞生意,銘賢自小也念過私塾,哪個孩子小時候不是一副乖巧的模樣,長大后也生生都是一副大戶人家,富家公子的不學無術的樣子,結果十七歲,也就是林家來石久鎮的那一年,父母留下一屋子綢緞,三進三出的大宅子,夠他生存的積蓄便撒手人寰。那時候的銘賢滿眼疲憊一身孝衣跪在墳頭對白先生說:心里不疼,很酸。
白先生抬手摸著他一頭烏黑的長發溫和的笑:是不是連眼睛也是酸的,卻生生流不出一滴眼淚。
從那時起,銘賢就成了林家的座上客,也許是因為有似曾相識的遭遇,亦或者因為相同的感知,又也許就是因為瞧著對眼,總之那一年后,林家的凳子碗筷就多了一副,銘賢也慢慢便知道是什么經歷早就了這樣一個奇怪的家庭,一副陳年往事結成舊夢,歷歷往昔卻又難以忘懷的一家五口,滿是欣慰,又滿是辛酸,滿是幸福,又滿是遺憾。
“今天銘賢鋪子里進了一匹新緞子,我看跟我們那時候學堂的紋路很像,扯一匹給你再做一身。”甄先生笑著對白先生說。
“做他干什么又不上學堂。”白眼橫他。
“你穿那身紅衣最好看。”甄先生從背后拉過他的手,毫不顧忌眼前的銘賢,反正銘賢早已習慣,也笑盈盈的說“那我明天扯一匹給憶文哥做一身。”白先生叫白憶文。
“那也少不了他們的,我穿,你們幾個都跑不了。”白先生臉漲的緋紅,指著甄先生和林氏說。
后來,就真的做了紅衣,但不是一匹,銘賢心里明白,叫人扯了四匹,做了四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