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評價他為賢臣,司馬光則評價他為小人。
戰國時期,戰亂四起,出了很亮眼的文臣、武將,范雎是其中的佼佼者。范雎,或稱范睢,是戰國時期(一代名臣),的著名政治家、軍事謀略家、戰略家、外交家,對戰國歷史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同時也是秦國的宰相。
他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有個成語:睚眥必報就是出自他),對秦國的崛起和統一六國起到了重要作用。
李斯對范雎的評價——“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范雎原為魏國中大夫須賈門客,因被懷疑通齊賣魏,差點被魏國相國魏齊鞭笞致死,后在鄭安平的幫助下,易名張祿,潛隨秦使王稽入秦。
范雎入秦后,他憑借自己的智慧和謀略,上書秦昭襄王,提出使得他名留青史的計策——“遠交近攻”的策略,昭王識大才,遂拜范雎為客卿,不久彼還重用范雎,使之為相,負責秦國對外事務及國事。
“遠交近攻”戰略是范雎最為人所知的戰略思想。他主張秦國在對外擴張時,應與較遠的國家交好,以消除后顧之憂,同時集中力量攻擊鄰近的國家,以逐漸擴大疆土和勢力范圍,這一策略極大地加速了秦國的擴張步伐,使秦國在戰國末期逐漸嶄露頭角。
這一戰略被秦國長期采用,據守函谷關,應對春秋六戰國,這計策所采用的的遠交近攻策略使得秦國好幾次獲得良好、充分的發展時間,對秦國的統一大業起到了關鍵作用。
說點題外話,范雎遠交近攻之策,一可強秦,二可報血仇,豈不快哉!
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在軍事上也有著不俗的表現,參與并策劃了多場重要戰役——出名的如長平之戰。范雎運用自己的智謀,成功地說服了秦昭王采用“反間計”,使趙國撤換了名將廉頗,換上了只會紙上談兵的趙括。這一計策的實施,直接導致了趙軍在長平之戰中的慘敗,在秦國統一六國的進程中立下了汗馬功勞。
除了這個最馳名的計策之外,范雎還在秦國推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加強了中央集權,削弱了舊貴族的勢力,積極推動了一系列內政改革,包括加強中央集權、整頓吏治、發展經濟等。這些改革措施不僅提高了秦國的行政效率,也增強了秦國的經濟實力,為秦國的統一戰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此外還主張“廢太后之權,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于關外”,并建議秦昭襄王“固其根本,制諸侯”,即加強國君的權力,使國家更加穩固,以控制其他諸侯國,使秦國王室加強了王權,在宗親氏族中削弱了他們的貴族勢力,壓制了貴族對王權的掣肘。范雎以其敏銳的洞察力和果斷的決策能力而著稱。他善于分析形勢,把握時機,能夠在復雜的政治和軍事環境中做出正確的判斷。在處置秦國對外事務時,還具有犀利的外交才能,能夠在外交場合中游刃有余地處理各種復雜的關系。
他的“遠交近攻”戰略不僅為秦國的統一奠定了基礎,也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此外范雎在秦國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加強了中央集權,推動了秦國社會乃至春秋末期的發展和進步。
但是他的一生也充滿著爭議和批評。
司馬遷在《史記》中,認為范雎不僅是一個賢臣,還“垂功于天下”,而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則認為范雎是一個“傾危之士”,是一個十足小人。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區別呢,司馬遷認為他是屬于那種有恩必報、有仇必報的人,恩怨分明;而司馬光是以“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為標準再結合其他事例,認為他是小人。
有部分記錄顯示:
認為范雎是一個天才戰略家、天才陰謀家,但為人極為冷血殘酷,思謀極為深遠,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簡直天生就是為亂世所存在的,注定要在亂世攪起腥風血雨的存在。
還有部分記載認為他過于專權獨斷,很多人認為他是嫉賢妒能、睚眥必報、自私自利的小人,而且這些說法的確是有證據支撐的,他因妒忌白起功勞而向秦昭襄王進讒,賜死了白起。
他因早年經歷,逼死須賈,羞辱平原君趙勝;因收受趙國賄賂,導致白起沒能在長平之戰后進一步擴大戰果等等...
我呢,還是那句——“莫經他人苦,莫勸他人善”,范雎一飯之德必償,暇眥之怨恨必報,豈非大丈夫也?盡管如此,范雎在歷史上以及秦國的史書上的貢獻和影響仍然是不可忽視的。
范雎相秦傾九州,一言立斷魏齊頭。
世間禍故不可忽,簀中死尸能報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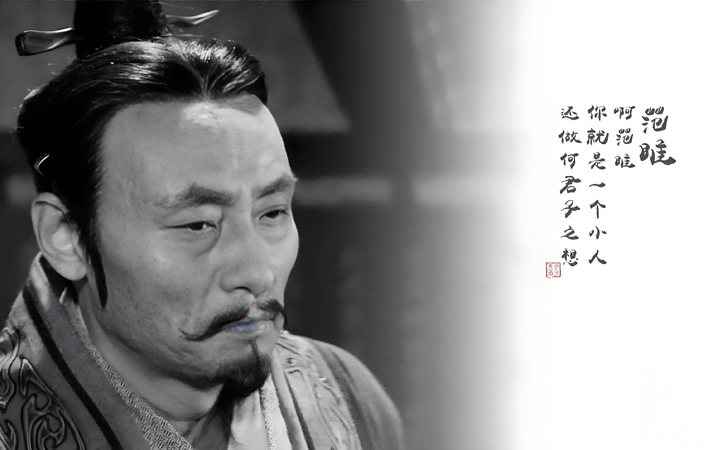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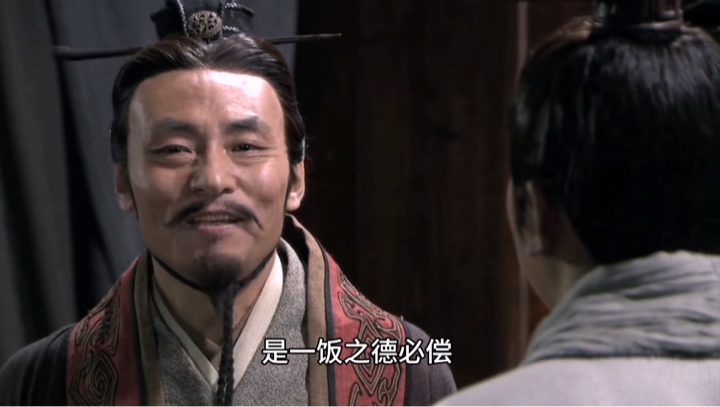


![[表情]](https://iyuedu.reader.qq.com/image/emoji/Emoj_80.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