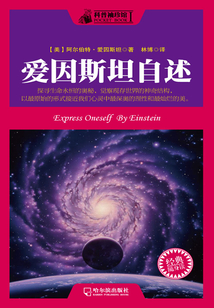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47評論第1章
自述一
我今年已經67歲,半截入土,也該到了總結自己人生的時候了,因而我寫下這些東西,權當訃告吧。我覺得做這件事很有意義,所以希爾普博士這么建議的時候,我也就沒有推辭。我想,講一講自己對人生的體驗,說一說自己是怎樣看待當年努力和探索過的事情,對于那些奮斗中的人來說,也不無裨益。可是,在考慮了一番之后,我必須承認,這種嘗試的結果不可能是完美無缺的,對它抱有任何完美的幻想與期望都是不切實際的。因為無論我工作的一生是何等的有限與短暫,無論我其間經歷過多少歧途,畢竟現在的我跟50歲、30歲或20歲時的我已全然不同,所以要清楚地講述我一生中值得講的東西,著實不是件容易的事。由于當下的心境和狀態會扭曲回憶的原貌,所以記憶也并非是完全可靠的。這一類的困難曾經讓我有打退堂鼓的想法,可是我最終還是覺得嘗試一下比較好,因為有這么一個信念在我的心里,即,一個人完全可以向別人講述自己的一些經驗。
我在少年時代就已經深切地意識到一個道理,即大多數人為追逐一些毫無價值的東西而花費了自己畢生的時間。隨后我就發現,這種追逐看似輕松,實則殘酷。可是無論是以前還是現在,人們總是用偽善而漂亮的字句裝扮這些毫無實質意義的東西。上天讓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胃,因而我們就不得不參與這種追逐。一般而言,人們的溫飽能從這種追逐中獲得。當然,感情豐富、思想敏銳的人不會滿足于此。不滿足者的第一條出路,就是宗教,每個孩子獲得第一手宗教理論的渠道正是傳統的教育機構。我的父母是猶太人,缺乏宗教信仰,可在十二歲之前,我的信仰之根都扎在宗教的土壤中。十二歲那年我讀了一些科學書籍,是它們中止了我的宗教信仰。我對《圣經》故事的真實性的質疑,就受到了這些書籍的啟發。于是,狂熱的自由思想猛烈地沖擊著我,這么一個讓人目瞪口呆的疑問也在我心中生根發芽:國家總是用謊言欺騙年輕人。這種體驗帶給我的是一種懷疑態度,它深刻地影響了我一生的歷程。我敢于懷疑任何社會中的一切既存信念,敢于懷疑一切權威。后來,因為要對因果關系有更深入的認識,我懷疑精神的鋒利性有所頓挫,然而它從未從我心中消失過。
少年時代的宗教天堂永遠逝去了,對于這一點,我非常清楚。這是我首次反抗“僅僅是一個個體”這個桎梏,這是我在嘗試實現自我救贖,這個結果是最原始的愿望、希望與感情融匯、撞擊而成的。在我們之外,存在著一個不可知的世界,我們人類的主觀愿望無法決定它的存在與否。雖然它是個永恒而深奧的謎,所幸人類依舊可以利用自己的思維和觀察部分地觸及到它。這個有著無比魅力的世界吸引著我們的深思和凝視,一如爭求解放和自由對我們的吸引。并且,很快我就發現,很多我所欽佩和敬重的人,在深入此項事業的時候,獲得了內心的安詳與自由。一個最高目標總會有意無意地浮現在我的腦海中,即借助一切所能借助的條件和力量,在有可能達到的范圍內,盡量用思想把握這個外部世界。在古今中外的各個行業、領域當中,有太多這樣和我志趣相投的朋友,他們都有著求索的熱情和深刻的思維。有一條平坦而誘人的道路通往宗教的天堂,可通向這個天堂的道路卻崎嶇泥濘。可是,對于我的選擇,我從未后悔過,因為它的值得信賴已經被證明無誤了。
我想我必須要說明一下,我這些說法的正確性也不是絕對的,就好像我面對的是一個細節紛亂的復雜對象,我的這些言辭僅僅是對之隨筆勾勒,只能對其有限的意義有所反映。一個人要是有著條理清晰的思想,那么,他若是付出了其他方面的代價,就能越來越彰顯這一本性,他的精神狀況也就愈加受到此特點的影響。所以,他的實際經驗雖然或多或少帶著某種偶然性,然而當回首來路時,很可能就看到一條清晰而明顯的規律的發展。之所以會出現個人生活的原子化現象,是因為外界情況總是多種多樣、變化萬端的,而意識則相對而言較為狹窄。在我看來,對于那些短暫的、僅僅作為個體的興趣,漸漸地被“努力從思想上掌握和理解事物”的興趣所取代,我人生發展的轉折點就在此處。如此說來,雖然前面這些評述僅僅是一種簡要的綱要,卻已經包含了盡可能多的真理。
應該怎樣準確地界定“思維”呢?接受感官印象時產生的記憶形象,或者在構成一個系列的一些印象中,由一個形象而聯想到另一個形象,這些心理過程都不是“思維”。可是,在很多這樣的系列里面,要是反復出現某一個形象,因為這種“反復出現”,那些本身與之沒有聯系的系列與之聯結了起來,這個形象也就成了此系列的支配因素。也就是說,此元素就成為了一個概念或一種工具。我想,“概念”在其中起到了多大的支配作用,構成了思維和自由想象(即“做夢”)之間的根本區別。雖然概念不一定必須通過感覺聯系起能夠再現的符號,然而若是缺乏這樣的聯系,思維的交流也就無法實現。
也許有人會問,某人為什么能夠在這樣一些領域中不用給出證明,就能夠輕松地運用觀念呢?我的回答就是:概念化的自由選擇是我們一切思維的本質,我們概括經驗能達到怎樣的程度,思維的合理性就有多高。因此在這個結構當中沒有“真理”這個概念的存身之地,因為“真理”的一個必要前提就是,人們已經一致認可了這種規則和元素。按照我的經驗來說,在很多時候,我們在無意識狀態下無需符號也能進行思維。否則,那種對某一經驗突然覺得“吃驚”的情況也就不會出現了。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吃驚”,是因為發現一些經驗溢出了我們所建立的概念世界。當我們的經驗和概念之間出現不可調和的激烈沖突時,我們就要修補、揚棄乃至重建自己的概念世界,反思自己的思維。從這個角度而言,不斷地“吃驚”并擺脫“吃驚”的過程,就是思維進步的過程。
我記得在四五歲的時候首次經歷了這種“吃驚”:我從父親那兒得到一個羅盤,我無比震驚于指南針那奇特而準確的行動方式,因為我無法在自己的頭腦中,也就是在我無意識的概念世界里面找到一個合適的位置來安置它。這次經驗給我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象,直至現在。我想我那時就應該在思索:肯定有什么東西在它的后面深深地隱藏著。對于刮風下雨,對于月亮以及月亮不會掉落而物體會下落,對于生物和非生物之間巨大的差別等,人們都毫不驚訝,因為這些事物都太常見,大家已經見怪不怪了。
在我12歲的時候,因為接觸到一本關于歐幾里得平面幾何的小書,感受到了另一種性質迥然有異的“吃驚”。這本書是我在剛開學時得到的,書中很多可靠而明確無誤的斷言給我留下的印象極為深刻,雖然也有的命題并不是很明顯,卻也都被確切地證明了,沒有給“懷疑”留下一點可鉆的空子。比如,三角形的三條高在一點相交。這些公理“無需證明就要承認”的這個性質,并未使我產生懷疑。我覺得,從有效性的角度就可以判斷命題的真偽,對此我感覺很滿足。比如說,在我的印象中,在尚未讀到這本幾何學小書之前,我的一位叔叔就已經跟我說過畢達哥拉斯定理。我從三角形的相似性這一點入手,花費了一番大氣力之后,對此定理進行了成功的“證明”。我當時就認定,直角三角形的一個銳角決定了它各個邊的關系,這一點無須證明,顯然是成立的。需要證明的只有那些在此類方式中并未表現出這種“顯然”的東西。并且,那些看得見摸得著的、擺在明面上的東西,我覺得完全相同于幾何學研究的對象,它們都是同一類型的。我想,將幾何概念與直接經驗對象不自覺地聯系起來的想法,是我這種原始觀念的根源所在。康德很可能就是以這種原始觀念為依據,提出了“先驗綜合判斷”是否存在這一問題。
用純粹的思維無法獲得關于經驗對象的準確知識,否則產生這種“吃驚”的依據也就是錯誤的了。對于第一次接觸幾何學的人來說,都能從希臘人那里得到這么一種印象:純粹的思維居然可以達到這么令人震驚的精確而可靠的程度。
說了一大堆,已經跟起初說的“訃告”離得很遠了,可是既然說到此處,我也干脆將我的認識論觀點用幾句話概括出來,雖然有些話在上文已經說過了。這個觀點有些不同于我年輕時的觀點,事實上這個觀點經過了很長時間的積累、修正,最后才總結出來的。對于所有的感覺經驗,以及書中所載的所有概念和命題,我一樣也不忽略或輕視。有一定的邏輯關聯性存在于命題和概念之間,而且也需要一些既定規則來實現命題和概念之間的相互關系,邏輯學就以此為研究對象。命題和概念必須要通過感覺經驗的參與,才能獲得其“內容”和“意義”。命題、概念與感覺經驗之間只有純粹的直覺聯系,而沒有邏輯關聯性。科學真理與幻想之間的區別就在于這種聯系,一些命題之所以是真理,就是因為它能得到這種直覺的驗證。邏輯概念體系本身雖然沒有任何限制,然而這樣一個目標卻是它們都要遵循的,既要盡量與感覺經驗的總和相對應,又要完備而可靠,并且,它們應該有一些類似于基本概念和公理的邏輯獨立元素,即其概念無法被定義,其命題無法被推導,當然這種概念和命題不宜過多。
從某一邏輯體系出發,按照嚴格的邏輯規則進行推導,則得出的命題就是真命題。而體系的內容有多大的真理性,在于其完備程度及可靠性(即在多大程度上能得到經驗總和的驗證)。真命題所屬體系的“真理性”,來自于其中的真理內容。
休謨認為,無法根據邏輯方法從經驗材料中推導出諸如因果性概念之類的概念。而康德則對某些概念的必備性確信無疑,他認為一切思維都要以這些被挑選出的概念作為其必要前提,并且它們跟那些來自于經驗的概念是不同的。可我認為,這種區分是不正確的,因為它并未按照自然的方式正確地對待問題……
繞了一大圈,我們還是回到訃告上面來吧。我在12到16歲之間,對包括微積分原理在內的基礎數學都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此時,我很幸運地與這方面的一些書籍有所接觸,它們有著突出的內容和簡單明了的基本思想,雖然在邏輯上它們也不無瑕疵,然而我還是從中獲得了很多啟發。總體而言,我確實沉醉于那次學習,在我看來,它一點也不弱于初等幾何,乃至于有數次都達到了頂峰。那時我專心致志地讀了許多著作,比如《白恩斯坦的自然科學通俗讀本》,這部優秀的通俗讀物有五六卷,它基本上都限定于定性敘述而沒有拓展。通過這次幸運的閱讀,整個自然科學領域中的主要方法和成果都被我了解到了。17歲時,我已經具備了一些理論物理學的知識,并進入蘇黎世工業大學準備攻讀數學和物理學。
就讀于蘇黎世工業大學時,幾位杰出的老師如胡爾維茲、明可夫斯茨等被我遇到了,照一般情況而言,我理應成為一位數學家。可事實并未按“一般情況”發展,我因為太過于癡迷直接接觸,所以在物理實驗室中度過了大部分時間。而在家中閱讀基爾霍夫、亥姆霍茲、赫茲等人的著作,則占據了我其他的時間。在一定程度上我忽略了數學,這是為什么呢?我想,原因之一就是我對數學的興趣遠不如對自然科學的興趣大,另外還有一次奇遇也對此產生了影響。我覺得,數學里面有很多專門的領域,我們往往耗費畢生精力也只能在其中一個領域有所成就。所以,我不知如何選擇,為此很是煩惱。當然有很多最重要也最根本性的東西包含在數學當中,可是因為我的數學天賦不怎么樣,所以并未將之學好。并且,我更感興趣于自然知識,當時我還只是學生,并不清楚要想在物理學獲得更大的成果,最精密的數學方法是必不可少的。我是在獨立科學研究之后好幾年,才逐漸明白到這一點的。
確實,物理學也跟數學一樣,分支領域眾多,而一個研究者即便在某一個領域中終生跋涉,也不一定能獲得令自己滿意的成果。況且,還有很多已經存在但其相互聯系尚未充分建立起來的實驗數據。可是不同于數學的是,在此領域當中,挑選、鑒別知識的眼光我很快就練出來了,挑出那種有用的知識,放棄其他多余的東西,特別是那些只會引領我偏離主要目標、占用我大腦容量的東西。
當然,還有個問題就是考試。即使不愿意,也要記住很多廢物,因為要應付考試。在最后的考試通過之后,大約有整整一年時間,因為之前強迫學習造成的不快,使我喪失了對科學問題的興趣。可是,公正地來說,我們在瑞士的學習要遠遠好過其他很多地方,少了很多那種讓人窒息的強制。在瑞士,除了兩次考試,人們可以隨著自己的興趣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于是大家就可以自由選擇,去聽自己想聽的課,直到考試前數月。我當時就是這樣,乃至比一般學生更甚。我有個朋友是個標準的好學生,認真地去聽每次課,并記錄、整理講課內容。我覺得這不過是略有瑕疵的小問題,雖然偶爾會有些內疚,總體來說還是挺享受的。正因如此,我才得以保留下了研究問題的神圣好奇心。現代的教學方法脆弱得如同一株幼苗兒,在鼓勵之外,自由更為重要。能挽救它免于過早夭折的,唯有自由。我覺得,為了增進學生的觀察及其探索的樂趣而使用強制手段,或將責任觀灌輸給學生,是一個嚴重的錯誤。一頭猛獸如果不餓,卻被人用鞭子強逼著不停地進食,而且是吃那種經過千挑萬選的食物,它必然會得上厭食癥的。現代教學也是這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