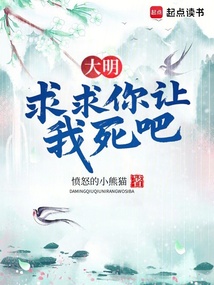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直言天下第一疏
大明永樂初年,金陵城。
夜已深了,坐落在金陵城鐘山腳下的大明皇宮,依舊燈火通明。
武英殿中,身材魁梧的朱棣正埋頭案上,一面批閱奏章,一面朝下方問話道:“老二,那些建文余孽,是否都抓干凈了?”
靖難的硝煙雖已散去,金陵城中的殺戮遠未停止。
朱棣成功登基后,開列“奸臣榜”,將站隊建文帝的朝臣抓了個干凈,盡數處斬。
要誅殺的可不止這些“罪臣”,他們的親眷家人,以及一些冥頑不靈、試圖為這些人開脫的儒生文士們,也都被抓進大牢,朱棣誓要用他們的鮮血,洗清建文遺毒,為即將到來的永樂王朝拉開序幕。
聞言,老二朱高煦站來出來,粗狂的面容上,雙眼閃爍著森冷寒芒,道:“還請父皇放心,所有建文余孽的家人及其擁躉,都已盡數落網,只消父皇一聲令下,隨時都可將他們處斬,以儆效尤!”
他素來果斷狠辣,更深知這些建文余孽深為朱棣忌憚,為討老爹歡心,自是要趕盡殺絕。
緊接著,老三朱高燧也出面附和道:“二哥所言極是,這些人冥頑不靈,若不嚴懲,難以震懾天下。”
朱棣聞言,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靖難一役后,大明改天換地,現今他永樂帝初登大寶,正需要雷霆手段,震懾天下,他要讓所有人都知道,敢于挑戰他權威的人,都要付出血的代價!
話音剛落,一直靜默不語的老大朱高熾站了出來,朝朱棣拱了拱手,神情緊肅道:“父皇,那些反對您的官員都已伏誅,您已然達到威服天下的目的,至于剩下的老弱婦孺,壓根掀不起半點風浪,何必趕盡殺絕呢?”
聽到這里,朱棣已極輕微地蹙了下眉頭,眼神中閃過一抹不悅。
將朱棣反應看在眼里,朱高煦立馬站了出來,粗聲駁斥道:“大哥此言差矣,這幫建文余孽死有余辜,若不全都殺絕,日后定成禍患!”
當下朱棣尚未立儲,皇子之間,其實隱有爭鋒。
老大朱高熾素有仁望,深為文官們所敬重;老二朱高煦能耐出眾,在武將中頗有威信。
而朱棣更曾在靖難之初,許諾給朱高煦太子之位,可靖難成功后,朱棣好像就完全忘記了這件事,這讓朱高煦很是著急,故而見到老大朱高熾惹朱棣不悅,他自然要出面討好父皇,打壓競爭對手。
一旁的老三朱高燧見狀,也連忙說道:“大哥未免太過婦人之仁,你今日放過這些建文余孽,豈知他日這些人不會陰謀造反,你要知道建文可生死未明呢!”
朱高燧和朱高煦向來是穿一條褲子的,兩人自然是一個鼻孔出氣。
朱高熾倒仍很鎮定道:“如今新朝新氣象,只需行仁恕之道,國朝就能安定,而且父皇今日放過這些人,他們必定會對父皇感激涕零,怎么會再行叛亂之事呢?”
“呵呵!大哥你能保證嗎?”朱高煦冷笑一聲,說道。
還沒等朱高熾回答,朱棣卻已輕咳一聲,打斷這場兄弟間的交鋒,抬眼看向三個兒子,最終目光落在朱高熾身上:“老大,你的想法許是好的,但你太過婦人之仁,只想著保全那些老弱婦孺,可你焉知他們日后不會造反?不會成為我大明的禍亂根由?”
此言一出,朱高煦、朱高燧二人臉上,立即露出得意笑容。
而朱高熾顯然還想開口爭辯,卻又被朱棣的話給堵了回去:“如今新朝初立,萬不可婦人之仁,否則便是害人害己,這些人,還是都殺了干凈!”
這話一出,朱高熾還想說什么,但最終沒有說出口,而一旁的朱高煦、朱高燧兩人,則是眉飛色舞,趾高氣揚,這一場交鋒,他們大獲全勝。
而朱棣并沒有管三兄弟之間的爭斗,而是再次拿起了一份奏折,看了起來。
看著看著,他的鼻孔漸漸喘起了粗氣,雙目變得赤紅起來,整個人如同一頭被激怒的猛虎一般,一把將案上的奏折橫掃在地。
三兄弟見此情景,頓時驚駭失色,他們從未見過父皇如此憤怒的樣子,哪怕當初建文帝逼死湘王朱柏時,朱棣聽到后也沒有如此的憤怒。
當即,三人害怕得連忙跪了下來,嘴里大叫著:“請父皇息怒!”
聞言,朱棣那赤紅的雙目望向三人,掠過朱高熾和朱高燧,最終定格在了朱高煦身上,他憤怒冰冷帶有殺氣的聲音在他的耳邊響起:“朱高煦,你不是說建文余孽都已被你抓捕下獄嗎?為何這里還有一個?”
說話間,朱棣手里的奏折直接砸在了朱高煦的額頭上,只見一道鮮血從他的額頭流了下來。
若是往常,老二朱高煦被老爹朱棣如此對待,朱高熾只會高興,但現在,他心里只剩下害怕。
而此時的朱高煦也顧不得額頭上的鮮血,他連忙叫道:“父皇明察,兒臣的確已將所有余孽抓捕,未曾放過一個漏網之魚!”
“那這是什么,此人非但漏網脫罪,竟還敢堂而皇之地給咱上奏,為建文余孽求情!”朱棣指著地上的奏折,大聲怒吼道。
一聽這話,朱高煦心下咯噔一聲,他趕忙跪伏上前,將那奏折撿起來,打開一看,內容很簡單,不過寥寥數百字。
臣都察院御史蕭弘彥謹奏,為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職、求萬世治安事。
自宋末崖山之后,我中原淪喪于胡虜百年之久,及至元末,太祖高皇帝舉紅巾大旗,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大明,故自三代以來,唯我大明得國最正。
然建文帝承太祖高皇帝之帝位,卻廢高皇帝之政,更殘害叔伯,陛下應太祖之命,承高皇帝遺烈,于北平起兵靖難,終成偉業,此乃正統所歸,天命既成,誠當受海內咸服,宇內共拜!
只看這第一段,倒寫得極是妥切,先是肯定了大明的正統,然后表示是建文帝破壞太祖高皇帝的政策,殘害叔伯,朱棣才不得不起兵靖難的,這是太祖高皇帝的旨意,所以朱棣這個皇位是天命所歸的。
可從第二段開始,語氣便急轉直下。
然則,自古仁君,以寬仁為懷,以德化民,未有以殺戮為能者,昔漢高祖功成而封雍齒,光武帝不記前仇以賞朱鮪,今陛下即位之初,便欲對建文余孽趕盡殺絕,此豈乃仁君之所為乎?
臣聞,上天有好生之德,君子有容人之量,陛下若欲成千秋偉業,傳之萬世,必當以德服人,以寬濟猛,今若以殺戮立威,則天下之人皆將懼陛下之威,而非懷陛下之德,此非長治久安之道也。
臣本北平一下吏,蒙陛下之恩德,提為都察院御史,是以‘監察百官、糾察弊病’之責,今陛下肆意殺戮,行殘暴不恤之舉,則朝野上下,人心惶惶,長以久之,必將招致國本動蕩,社稷危難。
大臣貪祿而希世,小臣畏罪而順旨,陛下有不得知而改之,臣恐自誤耳,是以昧死竭忠,庶陛下少加意焉。
望陛下改容更濾,寢殺戮之詔命,此宗廟社稷之幸,亦蒼生之幸也,臣頓首再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