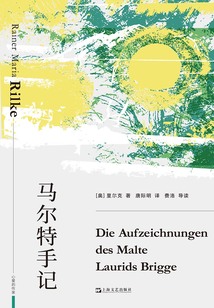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導讀 “成長者”馬爾特
偉大的德國小說,在堪與媲美的英國、法國和俄國小說之外,孕育出兩個獨擅勝場的類別,一類是“成長小說”(Bildungsroman),另一類是“藝術家小說”(Künstlerroman)。“成長小說”的主人公是一位心智初開的青年,立志于探索人生和心靈的最高境界,克服重重困難實現向這一境界的成長,當成長的力量來自詩和藝術,“成長小說”便會與“藝術家小說”融合。“藝術家小說”敘述一位特立獨行的藝術家,他是詩歌、音樂或繪畫精神的化身,憑靠此種精神成為英雄,完成他的偉業;藝術家小說探討他的生活方式所涉及的各種問題(愛情、婚姻、家庭、友情、與社會的關系等等),當藝術家的心靈成長凸顯為主要問題,“藝術家小說”便與“成長小說”融合了。
里爾克的這部《馬爾特手記》,正是融“成長小說”與“藝術家小說”為一體的“藝術家——成長小說”(Künstler-Bildungsroman),且以最為獨特的方式將之推向巔峰。有別于同類小說此前著名的先例,如歌德的《威廉·麥斯特的學習時代》和諾瓦利斯的《海因里希·馮·奧弗特丁根》,其主人公踏上一條“外在的”游歷之路,去追尋某種理想中的事物(當然,游歷于外部世界的追尋過程,象征著內心世界的成長過程),《手記》的主人公來到巴黎并居留于此,但巴黎并非他游歷外部世界的終點,倒是他內心世界之成長的起點,是他踏上的那條“向內之路”(Weg nach Innen)的起點。
《手記》的主人公馬爾特出生于北國丹麥,全名馬爾特·勞里茨·布里格。于某個秋日,他獨自抵達巴黎,落腳于拉丁區圖利耶路上的一家小旅館,窮困潦倒地度過了那年的秋天和冬天,迎來了次年的春天。他何時離去,無從知曉,他的離去和到來一樣不著痕跡。可是,逗留巴黎的這段時間內,他在四壁蕭然的旅館房間里寫下一篇篇手記,記錄了內心發生的深刻改變和脫胎換骨的成長。
這位默默無聞的青年,形單影只,身無長物,他是背井離鄉的遠行者,是與傳統脫離聯系的現代人。最初的抵達,立即在他身上觸發了一系列的“巴黎印象”,這些印象圍繞感官遭受的種種外界刺激——聞到的氣味、聽到的聲音和見到的景象。巴黎日常生活里的各種氣味和噪音,甚至片刻的寂靜,都會令他不安;而目之所見,與疾病和死亡聯系在一起的醫院更是帶來恐懼。這些印象緊緊纏繞著他,讓他無論走到哪里都帶著恐懼與不安,揮之不去,至多只有短暫的停歇。
巴黎市中心由先賢祠、盧森堡公園、圣米歇爾大道、盧浮宮、杜伊勒里公園和香榭麗舍大道組成的令人流連忘返的空間,馬爾特也徜徉于此。秋日清晨旭日東升的杜伊勒里公園(11——指《手記》的節數,下同),月色皎潔的新橋(12),軒敞明亮的(老)國家圖書館閱覽大廳(16),拉辛路的豪華商店(16),塞納河畔的舊書販和古董鋪(17),空蕩的田野圣母院路(5),寬闊且同樣空蕩的圣米歇爾大道和廣場(21),展示巴黎主保圣女《圣日南斐法的一生》壁畫的先賢祠(22),懸掛《獨角獸旁的夫人》壁毯的克呂尼中世紀博物館(38),所有這些,都讓他駐足遐思。——然而,那些到處可見的醫院,卻更加觸目驚心。他最初記下的印象便是一家婦產醫院(1)和圣雅克大街上的“圣寵谷軍醫院”(1),另外又述及巴黎圣母院附近的“主公醫院”(6—7)和薩伯特慈善醫院(19),描寫的類似處所還有價格低廉的夜宿所(1),把垂死之人載往醫院、每小時收費兩法郎的出租敞篷馬車(6)。
所有這些感官的“印象”都引向“恐懼與不安”的在世體驗,歸結于“生與死”的對立。這正是現代生活的癥結所在。馬爾特深切感受到,無孔不入的噪音讓人不再擁有屬于自我的“寂寞”,人的自我被各種噪音輕易穿透;而“死”也不再具有完成生命的意義,醫院里毫無個性的批量的死代替了“自己的死”。
如何對抗這無所不在的“恐懼與不安”?馬爾特是一位詩人,求助于寫作。可他此前寫過的詩受著情感的擺布,都是不成熟的吟風弄月。事實上,他的詩尚未開始。他必須首先成為“初學者”,一位“成長者”。這意味著,不再執念于自己是遲到的“后來者”,而要將人類的一切發明、進步、文化、宗教和世界歷史置諸腦后,讓自己從“先來者”的數不盡的遺物里掙脫,回到自己此在之初的本原,從而成為“最先者”。如此方能在成就自己的寂寞里成長,開始他的工作。這正是他在綱領性的第14節手記里做出的決定:
這位年輕的、無足輕重的外國人,布里格,得在五層階梯高之處坐定,書寫,日以繼夜。是的,他必須寫,這將會是個了結。(見本書第23頁)
為了回到此在之初的本原,他著手“童年回憶”的寫作(15)。盡管這個主題很快被打斷,他還要一次次地對抗自己的不安和恐懼(16—26),但最終,他得以在“五層樓上的”寂寞里聚精會神,專注對童年的回憶(27—44)。
回憶童年,不是人們通常以為的那樣,讓自己重返假想中的天真無邪、無憂無慮的美好年代,而是把生命之初的各種體驗,以其本真的狀態召喚到眼前。只有向著童年回憶,栩栩如生地再現那些人生之初的銘心體驗,才能將自己究竟是“誰”,從何而來,“我”的本質揭示出來。這些體驗幾乎與天真無邪、無憂無慮全不相干,既包含愛、快樂、驚異和神奇之感,也包含焦慮、不安、畏懼和驚恐。對于像馬爾特這樣的現代人而言,后者的比重更勝于前者,更有必要予以特別關注。一旦他通過回憶把這些體驗本真地召喚到眼前,他也就回到了自己此在的本原。他觀看著身處這些體驗的“童年之本我”,有如金蟬脫殼一般地從“一己小我”當中脫離出另一個更高的“我”,一個寓托“人”之存在的“大我”。這個“我”在“童年回憶”里不斷地壯大,不斷地提升。“一己小我”愈是向“童年之本我”敞開,愈是被后者充盈,這種脫殼和蛻變的過程就愈是徹底,好比是被之靈魂附體后,突然釋放出一種久已塵封的生命活力。
這個意義上的“童年回憶”,在馬爾特的手記里由“童年體驗”和“家族往事”兩個相互交織的面向組成。“童年體驗”圍繞著“恐懼與不安”(20:童年的種種恐懼;27:媽媽的恐懼;29:“手的故事”,對離奇事物的恐懼;32:鏡前,看到戴著面具的“我”變成陌生人的恐懼;42:造訪鄰居舒林家,對鬼魂和幽靈的恐懼)、“生病”(30:發高燒的譫妄)和“無法理解的經驗”(43:一切都出了差錯的生日),但也有快樂(31—32:變裝和變身的樂趣)、著迷的時刻(41:翻卷和欣賞蕾絲花邊),以及童年友誼的喜悅(34:畫廊里的意外相逢;35:唯一的朋友小艾立克)。凡此種種,都是他人生之初的銘心體驗,蘊蓄著此在的本真狀態。
“家族往事”則主要述及父系和母系的家族成員,他們對馬爾特“自我”的塑形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維系父系一族的主題是“死”,最突出的是馬爾特的祖父,侍從官克里斯多夫·德特勒夫·布里格,他在烏斯加爾德莊園祖宅里的宏大的死,是“自己的死”之典范(8);此后,父親之死已趨沒落,他在城里一間出租公寓里做了“穿心手術”后最終死去(45);孤僻嚴厲、無法理解“死”的祖母瑪格麗特則是祖父的一個對立面(另一個對立面是媽媽的死:不同于祖父之死發生于內里,它發生于表面和感官,33)。
相比之下,母系一族的成員人數更多,也更為奇特。首先是居住于烏楞克羅斯特古堡的外祖父布萊伯爵,他熱衷于超自然力量和靈異事件,擁有無視時間順序而對生死一視同仁的能力,并且最擅講述。他的兒子,克里斯蒂安·布萊伯爵,云游四海,過著冒險的生活。他還有三個女兒,馬爾特的媽媽,媽媽的妹妹英格褒,以及最小的妹妹阿伯瓏妮。馬爾特最喜愛這位美麗的阿伯瓏妮,因她善于歌唱,迷戀寫作,教導童年的他閱讀、觀看和愛。另外還有一位以少校軍銜退伍的叔父隱居古堡從事煉金術;媽媽的一位遠方表親,與奧地利某招魂師通信并聽命于此人的瑪蒂德·布萊;一位堂姐的兒子,有一只眼睛無法轉動的小艾立克,他與外祖父無需語言交流而直接心靈相通。最后是那位很久以前死于分娩的克莉絲汀·布萊,她的鬼魂屢次出現于家族晚餐的廳堂里。
“講述”是維系母系家族的最重要主題。“媽媽給我講述英格褒”(27),“媽媽給我講述狗的故事”(27—28),“我想給媽媽和艾立克講述手的故事,但最終只能對自己講述”(29),“我也許可以向你(艾立克)講述一些事情”(35),“阿伯瓏妮給我講述媽媽的少女時代”(37),“我不愿講述你,阿伯瓏妮”(37),“老伯爵向阿伯瓏妮講述自己的童年”(44)。這最后一段講述經由馬爾特的回憶被重新講述,構成了“童年回憶”的高潮(也是一幅馬爾特自己所做“童年回憶”的鏡中像):擁有把“曾在的與未來的統統當成實在的”能力的外祖父,“回憶”他自己的童年,通過“講述”賦予存在,“仿佛將什么永存之物置入空間之中”,并讓被述者真的“看見”。從外祖父到阿伯瓏妮到媽媽再到馬爾特,也是一個真正的“講述”能力沒落的過程,但是馬爾特通過自己對“童年體驗”和“家族往事”的講述,尤其是重述外祖父布萊伯爵對他自己的童年的講述,開啟了相反的上升過程,讓“講述”成為他所經歷的內心“成長”的樞紐。
為何是“講述”?因為馬爾特是一位詩人,一位還在“成長中”的詩人。他自稱過早地開始寫詩(14),但整部《手記》里并沒有記錄他的任何一首詩,卻完全用散文寫就。仿佛他故意回避作詩,還如此辯解:
寫詩需要耐心等待,并且搜集寓意與甜分,花一輩子的時間,如果可能的話,一個長的輩子,然后,在生命的盡頭或許能夠寫出十個詩句,真正好的。因詩并非,如世人以為的,情感(這個人們在早年就已充分具備了),——它是經驗。(14,見本書第18頁)
“情感的詩人”,如每位多愁善感的青少年所是,只是“主觀的詩人”。那無休無止的即興抒情,把他局限于一己之小我當中無法自拔。他必須掙脫這些表層的情感,沉潛到人和萬物的存在的深處,成長為“經驗的詩人”,把一己之小我擴大到無我之大我,出離“主觀”而成為“旁觀的詩人”。
于是,馬爾特暫且擱下他的詩筆,用散文來淬礪“經驗”,去認識和感受人與物,回憶自己的童年,也“回憶”他人的經歷。這些散文體的手記是向著詩歌創作的準備,是一個從情感到經驗的轉變過程。他訴諸“講述的藝術”來實現這一轉變,因為真正的“講述者”恰恰是一位沉潛到萬物和人的存在深處的“旁觀者”,他從經驗——而非情感——構筑一個全新的“被講述的世界”,從根本上轉化世界的意義。
馬爾特對“講述的藝術”的學習在《手記》里逐步展開。初抵巴黎的他還是一位主觀的抒情詩人,完全生疏于“講述的藝術”,他只能記下一些印象的片段,無法跳脫這些飄忽不定、支離破碎的印象,但他的成長也于此起步:他努力剔除“巴黎印象”里的“情感”成分,從中提煉出“經驗”,經由“回憶”掌握“講述的藝術”,而“巴黎印象”部分插入的兩段關鍵的“童年回憶”——“祖父之死”(8)和“外祖父之家”(15)——便是最初的成功嘗試;《手記》的中間部分集中于“童年回憶”,都在運用“講述的藝術”深入“童年之本我”,把此種藝術漸漸帶入得心應手之境;末尾部分更是由近及遠,從兩則“鄰居”的故事開始(49—50),到歷史典范人物的故事(54:偽沙皇格里戈里·奧特列皮耶夫的終結;55:大膽查理的敗亡;61—62:瘋子查理六世;61:教皇若望二十二世),最后到超脫歷史的神話典范人物的故事(68:怪人沉思薩福;71:浪子回家),這些故事把“講述的藝術”發揮至爐火純青,與其他關于相同主題的反思性文字,以及對“童年回憶”的講述(如56:“學習閱讀”)和從“童年回憶”轉化而來的講述(如69:“阿伯瓏妮在威尼斯的歌唱”)相互穿插,構成了一個旁觀的敘事詩人的“經驗”和“回憶”。終于,到了圓滿結尾之時,詩人馬爾特才借著“威尼斯的丹麥女歌者”之口,唱出一首“愛之歌”(69)。對“講述的藝術”的掌握過程,讓馬爾特突破一己之小我,貫通人類歷史與神話,進入歷史人物與神話人物最獨特的愛與死的體驗,實現了一種深層的向內成長。
這條向內的成長之路,正是走向一門新的“藝術宗教”之路。來到巴黎的馬爾特好比是來到沃爾普斯韋德的畫家們開始他們的成長,又像是定居于巴黎的羅丹那樣成長于巴黎;在他身上發生的,猶似沃爾普斯韋德畫家們向著更偉大的羅丹的成長。這門新的“藝術宗教”,一如沃爾普斯韋德畫家們所確立的“風景畫的藝術宗教”和羅丹所確立的“雕塑的藝術宗教”,是“講述”的“藝術宗教”。馬爾特向著這門新的“藝術宗教”的成長之路,把“講述的藝術”所特有的藝術體驗推衍到極致,成為人最本真的生命體驗,與之相關的藝術創作成為人最本真的存在方式,從事這種藝術創作的人成為以最本真的方式存在的人。他從“巴黎印象”當中提煉出最重要的幾個主題——恐懼和不安、死和愛——在他至深的寂寞里返回童年,圍繞這幾個主題訴諸“童年回憶”來學習“講述的藝術”;逐漸地,終于在日復一日的寫作中掌握了這門藝術,構造出一個整全的“被講述的世界”,從而完成了這幾個主題,圓滿于“浪子回家”這則被重新講述的寓言的全新世界。
所以,“手記”并不僅僅指稱這部小說的形式,而且也是它真正的主題:馬爾特記下的文字,從最初的印象到童年的回憶,再到故事的講述,既是藝術上的成長,亦是他向著人最本真的存在方式的深入。馬爾特作為藝術家的成長,不僅轉化了人的存在方式,也轉化了整個世界的意義。“成長者馬爾特”身上實現的這一雙重轉化,讓他成為“講述的藝術”這門新的“藝術宗教”的奠立者。盡管這位奠立者自己不知所終——就像回家的“浪子”不知是否真的會留下——卻用他的《手記》向我們昭示了這個成長過程的艱難與偉大。
費洛
二〇二三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