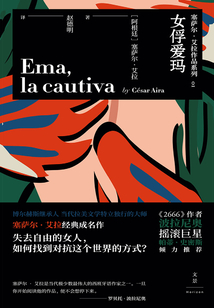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譯者序言
翻譯了幾部阿根廷當代作家塞薩爾·艾拉的小說,閱讀了一些關于他的生平、創作經歷、作品評論和分析的西班牙語資料,感覺有些想法應該提供給我們的讀者,希望能夠幫助中文讀者理解他的創作指導思想、藝術手法和題材的選取。
1949年,塞薩爾·艾拉出生于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省南部的普林格萊斯上校鎮。父親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更是個狂熱的庇隆主義者,堅決支持庇隆總統的獨裁統治,是個參加政治活動的積極分子。艾拉從小就對父親的不關心家務表示不滿,只能依賴母親的呵護。他是獨生子,母親對他百般寵愛,隨著時間的推移,他變得不愛說話,只喜歡讀書。由于家離首都不遠,他經常在阿根廷國立圖書館閱讀各類書籍,對文學、歷史、哲學、音樂、美術等人文科學類的圖書都有廣泛涉獵,他雄心勃勃,想要當個“百科全書式的作家”。進入青年時期,在大學里,他廣泛接觸了歐美先鋒派文學和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后現代主義思潮。其中阿根廷文壇上的博爾赫斯、羅貝托·阿爾特和曼努埃爾·普伊格,法裔美籍藝術家馬塞爾·杜尚、對超現實主義有重要影響的雷蒙·魯塞爾以及美國先鋒派音樂家、藝術家、哲學家約翰·凱奇對他后來的創作都有重大影響。
先鋒派文學的本質特征是反對傳統文化,刻意違反約定俗成的創作原則和欣賞習慣,主張獨創性、反叛性、不可重復性等原則。先鋒作家創造了新小說的概念、敘述方法和新的話語規范,尤其是對語法規則和邏輯性進行“顛覆”和“解構”。在思想內容方面,先鋒派作家講究直面人生,追求片面的深刻性,探求當代人的生存困境,表現作者的覺醒意識和身處邊緣的孤獨感。這在20世紀70到80年代的艾拉作品中多有印跡,其中馬塞爾·杜尚的“觀念藝術”理論對艾拉的影響尤其明顯。杜尚認為,藝術品的本質在于藝術家的思想,觀念是藝術的主體,文字、攝影、文件、表格、地圖、電影和錄影帶,加上觀眾的心智參與,都是觀念的表現形式。他還堅持認為,藝術價值在于“創意”(idea creativa),而不在于展出的物品是否具有美感。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在瓷質的小便池上貼了一個“泉”字,送到展覽會上要求展出,被組委會憤怒地拒絕了。他們不懂得“泉”字背后的“創意”所在,這個字卻改變了人們通常的審美視角。杜尚的“觀念藝術”是反理性的,是反對傳統審美觀念的。他尖酸刻薄地質問:外在美是真美嗎?這讓我們聯想到,安徒生童話中皇帝的“新衣”是真的新衣嗎?杜尚極端的批判精神摧毀了種種傳統的藝術觀念,為新藝術流派的誕生解除了精神枷鎖。艾拉的文學創作深受他的影響。
在阿根廷國內,對艾拉影響最大的人物當屬博爾赫斯。這位阿根廷文學大師的寫作特點很多,讓艾拉直接受益的有:博爾赫斯打破了小說、散文、詩歌三者之間的界限;他的散文像小說,小說是詩歌,詩歌像散文。溝通三者的橋梁是作者淵博的知識和睿智的思想,是有創意的“點子”。三位一體,獨一無二,旨在表現“世界的混沌性和文學的非現實感”。例如短篇小說《阿萊夫》中就匯集了諸多主題:夢幻、迷宮、圖書館、虛構的作家、作品、宗教信仰、神祇等題目,有故事,有哲理,有散文詩,多種元素自然而然地融合在一起,渾然天成。在類似《阿萊夫》這樣的小說中,作者采用了時間和空間的輪回與停頓、夢境和現實的轉換、幻想和真實之間的界限自然連同、死亡和生命共時、象征和符號之間神秘的暗示等手法,把歷史、現實、文學、哲學(尤其是不可知論和神秘的宿命論)之間的界限打通,模糊了它們之間的疆界,創造出一個神秘、夢幻的虛構世界,在真實和虛構之間,找到一條可以穿梭往來的通道,讓讀者獲得神奇的閱讀感受。
20世紀80年代末,歐美的后現代主義思潮延續和發展了先鋒派的沖擊力。從艾拉90年代的創作來看,他的確接受了后現代主義思想中的某些觀點,例如堅持反傳統的精神,堅持文學創作的不確定性,堅持寫作手法的多樣性、多元性和語言上的試驗,講究作品形式的光怪陸離,進一步打破真實和虛構之間的界限,消除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邊界,追求作品主體的零散化和故事情節的碎片化。
從1975年到2017年間,艾拉創作了八十多部文學作品,毫無疑問,這是一位高產作家。如果從創作題材上分類,70年代到整個80年代,艾拉的創作題材主要取自阿根廷潘帕斯大草原的風土人情,90年代的題材是“我”,2000年至今的主要題材是“藝術”。
大草原題材的主要代表是發表于1981年,也是艾拉成名作的《女俘愛瑪》。從選材的角度來說,《女俘愛瑪》與19世紀阿根廷浪漫主義文學大師埃斯特萬·埃切維里亞的長詩《女俘》是唱反調的,是反傳統的“女俘”形象的。長詩《女俘》的主人公是個被凌辱、被欺壓、被傷害的女性,而艾拉筆下的女俘卻是個在困境中努力奮斗的女子。她克服了種種生活中的困難,與軍人友好共處,善待印第安人,與要塞的上校結為好友,贏得了上校的支持,最終成功地創辦了一個養雞場。作者塑造了一個在逆境中勵志創業的模范典型。艾拉在另外一部小說《野兔》里,把印第安人各部落的矛盾沖突處理成了“家族大團圓”,把大草原描寫成美麗、富饒、適合人類居住的樂園。這些看法與19世紀的大作家、阿根廷總統多明戈·福斯蒂諾·薩米恩托對大草原和印第安人的認識大相徑庭。薩米恩托在他的巨著《文明與野蠻》中提出:印第安人是“野蠻因素”,阻撓了社會進步和國內的經濟發展。艾拉不贊成這種看法,認為印第安人創造了自己的文明,是個很有智慧的民族,很好地處理了人與自然生態的關系,應該向他們學習。
進入90年代,艾拉的創作題材轉向“我”,也就是“我”成為塑造的對象。“我”在他這個時期的作品中處于中心地位。艾拉用自傳的內容和形式來表現小說故事的真實性,但是其中有很多虛構成分,實際上是真實與虛構的對立統一,真真假假,難以分辨。但是,作品的基礎仍然是作者自己的生活經驗。《彈子游戲》和《晚餐》就是這類作品的代表。兩部小說的主要情節都是“我”的切身經歷,前者是“我”去華人超市購物發生的故事,后者是“我”與一位脾氣怪異的朋友共進晚餐的故事。作品中發生的怪人怪事顯然都是虛構的,但是與真實的場景融會在一起,產生了十分逼真的藝術效果。
而到了21世紀,艾拉的題材選取轉向了“藝術”,“藝術”成為他最重要的創作源泉之一。艾拉通過筆下的人物,對某樣藝術品做出判斷和評論,進而引申到對文學自身問題的關注。比如在《巴拉莫》(Varamo)中,作者讓人物出來發表意見,批評專業寫作現象,主張自由快速書寫,強調藝術的生命在于創新。艾拉的藝術追求是打破文學、美術、音樂、魔術、舞蹈等藝術門類之間的界限,文學家、畫家、作曲家、魔術師、舞蹈演員齊聚一堂,各抒己見,旨在打破森嚴壁壘,支持新藝術家即興發揮。
縱觀艾拉三十多年來的文學創作,他十分在意寫作手法的藝術創新。不錯,他的確深受國內外文藝思潮的影響,但是,他更注重文學創作的“個性化”。原創構思講究“智慧”,寫作手法講究“新奇”,敘述話語講究“怪異”,整個故事情節安排要“碎片化”。艾拉的這些表現在阿根廷當代文學的大合唱中屬于“不和諧音”。尤其是他遵循前輩博爾赫斯的教導,追求文學創作的世界性傾向。比如他的《小和尚》和《一部中國小說》,把小說的舞臺搬到了韓國、中國、巴拿馬、委內瑞拉,甚至包括歐洲和非洲國家。艾拉上述表現的理論基礎是超現實主義。艾拉承認,超現實主義的藝術追求(例如表現驚奇、怪異、矛盾、荒謬、夢幻……駕馭意象,改變日常生活的現實感覺等)對他的創作有直接影響。但這僅僅是“影響”,是早期創作的表現。到了2016年,評論家伊格納西奧·埃切維里亞問他與先鋒派文學的關系時,他回答說:“我沒有先鋒派的外殼,我更喜歡傳統小說。我刻意追求創作新東西,其實骨子里,我喜歡老東西。如果有人非要說我是先鋒派作家,那只能說明我喜歡寫一些荒唐、怪誕的故事,因為我不喜歡老東西里的裝腔作勢,我要借助藝術手段打假。”他堅信文學高于其他藝術門類,因為文學有自己的秘訣,可以囊括別的藝術門類,反之則不可能。
最近十幾年,塞薩爾·艾拉的文學作品和文藝思想在歐美文壇日益受到重視。早在21世紀初,拉美著名作家、《2666》的作者羅貝托·波拉尼奧就說過:“艾拉是西語文壇上為數不多的最優秀的作家之一。”面對贊譽和批評,艾拉都處之泰然。2018年4月25日曾有記者問他:“您總是能從日常瑣事里找到快樂嗎?”他回答說:“是的,這正是因為我的寫作理想就是每天都追求變化。快樂就在于此,就在于做些天天有新意、不同的事情。我不擔心將來某一天沒了發現新意的能力,因為我已經習慣了寫完一部作品之后的大腦空白期。但是,第二天我總會冒出新想法。從天而降的新主意,新點子。誰也不知道是從哪里來的,也許是看書,也許是道聽途說產生的聯想。因此可以肯定,新東西總會有的。讓我產生聯想的主要來源是閱讀。我認為作家的營養來自我們自身的第二人格、來自讀書的秘密‘超人’。想法可能來自任何地方,電視節目啊,生活瑣事啊,隨便一次談話啊。但是,通過讀書可以看到別的方面,會刺激我們繼續寫下去。我非常感謝閱讀,因為它曾經挽救了我的生命。小時候,我膽小又近視,只好藏到書堆里,天長日久成了習慣,結果成了寫書人,寫出書來,再讓別人藏進去。”
他還對記者說:“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讀書的趣味也在逐漸改變。一開始,我喜歡讀兒童讀物,連環畫、動漫故事、歷險記、海盜傳奇都是我的最愛。我還記得十一二歲時閱讀的海盜傳奇,作者是法國作家儒勒·凡爾納,多達二十一卷。后來,到了十四五歲,我發現了真正的文藝圖書,講藝術的圖書,還發現了博爾赫斯的作品,從此看起書來就變得非常挑剔了。”記者請艾拉說一說對圖像小說的看法。他說:“我深入過圖像小說的世界。如今,我不喜歡新的圖像小說,可我兒子是畫家,專門為美國出版圖像小說的出版社工作。我問兒子為什么總是畫僵尸還魂、外星人登陸、海盜搶劫、納粹入侵,這些東西分分合合,沒有新花樣,毫無創意可言。我兒子成了圖像小說的雇傭軍。有人建議,讓我兒子為我的作品畫漫畫,可是我不感興趣。我一批評兒子的東西沒有創意,他就說,您可以為我寫一個有創意的腳本啊。我不愿意寫腳本,我已經習慣了自己的寫作方式。”
記者問艾拉是否閱讀過《堂吉訶德》,他的回答引出了一段大學時的讀書經歷,也值得說給讀者聽一聽:“我曾多次閱讀《堂吉訶德》,真是眼花繚亂,那是在大學期間,可以說是《堂吉訶德》把我領進了學術研究的世界。我當時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文學系念書,大學畢業時,一位非常賞識我的老師派我去語言文學研究所做關于《堂吉訶德》的研究,選定的研究題目是《論作為對話體小說的〈堂吉訶德〉》。我開始讀書,做筆記,可是后來不知怎么回事,雖然有了工作,收入也不錯,卻總覺得自己在學術研究領域做不出什么成果。經過努力,我或許可以成為優秀的研究員,成為一名文學史專家,但是我寧愿選擇放棄學術研究,去書寫自己的作品。我也不適合教書,口才不行。”
從上述這段話可以看出,艾拉個性很強,不愿意做自己不喜歡的事情。這樣的個性反映在文學創作上,更是如此:自己想寫什么就寫什么,絕對不做社會、道義方面的承諾。針對尼加拉瓜著名作家塞爾希奧·拉米雷斯強調的“面對社會現實不肯睜開眼睛的作家,就是背叛了自己的職業”的觀點,艾拉明確表態:“我不同意這個說法。我安安靜靜地閉上眼睛,不認為自己背叛了自己的職業。我不明白,為什么文學家一定要對周圍的社會政治現實做出承諾呢?為什么?為什么呢?可能是為了拿到文學獎吧。國內有些朋友總是勸我,稍稍努力一下,爭取拿諾貝爾文學獎。這個‘稍稍努力一下’,就是要我開口談談人權,談談民主。我可不想說這個。我寧肯生活在象牙塔里,跟自己的圖書、詩歌和藝術在一起。我認為我有權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對身邊發生的一切當然感興趣,但感興趣的方式非常普通。我生來如此,有些東西我就是不感興趣。很多人喜歡政治和足球,我不喜歡。我喜歡的東西,幾乎沒人喜歡,這不是我的過錯。喜歡和不喜歡,互相彌補而已。”艾拉對精神自由的追求表現在方方面面。在阿根廷,公民投票是憲法規定的權利和義務,艾拉卻不在乎;他也去投票站,但是投棄權票,因為他不相信候選人的口頭承諾。但是,在他熱愛的文學藝術領域,他卻是忠貞不渝的。年輕時他也很喜歡美術,但是開始寫作之后,他就下決心要寫出好作品來。他堅信寫作這個行當全靠時間和實踐,創作的道路只能自己走,別人的建議只是參考。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寫作方式,如果只是按照別人的方式寫作,往往有害無益。他這樣說,是有他自己的理論基礎的。他說:“社會得以幸存,是因為有誤會。以文學為例,作家寫的東西,他心里明明白白,到了讀者手里卻產生了誤會,難以被人理解。文學的寶貴之處就在這里,因為簡單的理解可能就是傳達一個信息(今天有雨,明天放晴),而文學遠遠超出了傳達信息的功能,這超出的部分就在作家的明明白白和讀者的誤會之間。我經常想到我自己就是個讀者,這個讀者身份讓我嚴格控制自己寫的東西。”
艾拉的作品日漸受到歐美各國評論界和讀書人的關注。墨西哥大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生前曾經預言:2020年艾拉將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近幾年來,在入選諾貝爾文學獎的外圍名單中,艾拉的聲望也逐漸提升,阿根廷國內很多人也希望除球星梅西之外,再來一個文學明星。對此,艾拉的態度是:“對我來說,這毫無意義,一旦獲得了如此重要的文學獎項,就會變成公眾人物,這可是個大麻煩,因為會失去眼下默默無聞的地位;那樣一來,如果出門騎自行車,就會有人指指點點……不不不,太可怕了。我還是盡量保持現在的狀態吧,我連電視都還沒上過呢。不是因為我犯了法或者干了壞事要隱姓埋名,而是我想繼續低調地做好事呀。”
“繼續做好事”包括寫散文。2017年11月19日,文學評論家霍爾赫·卡里翁發表了《塞薩爾·艾拉:優秀的小說家還是杰出的散文家?》一文。他介紹說:“塞薩爾·艾拉有一本散文集,其中有許多精彩段落,比如他說‘要寫出好文章,是可以學習的;但是,下決心寫作絕非易事,因為寫作拼的是生命’。這類關于寫作和藝術的看法收在他的散文集《各種思想的延續》中,多數文章都談及當代文藝問題。他堅決捍衛浸透作家每個細胞的純文學,態度絕對是浪漫主義的。我們很容易在艾拉身上看到后現代主義和新先鋒派文學的影子,但是他還有少見的浪漫主義的一面。他的散文的確反映出他是個浪漫主義作家,很像是墨西哥大作家、偉大詩人帕斯在《污泥的兒女們》中刻畫出的浪漫主義和超現實主義延續者的形象。近年來,他的散文創作轉向論述他的創作經驗和小說敘事理論,集中收在《各種思想的延續》、《論當代藝術》和《論遁詞》中。”這篇文章的最后,作者得出如下結論:“艾拉的散文篇篇優秀,而小說則參差不齊,原因是小說是他創作的實驗室,有探索的性質,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具有隨機性。而他的散文是深思熟慮的結果,是反思創作經驗教訓的結果,針對性很強,篇篇打中靶心。因此,他的散文勝過小說。”看來還需要把他精彩的散文引進到我國來啊。
最后,我從譯者的角度說三句話:一是要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二是理解艾拉,尊重艾拉;三是是否借鑒艾拉,應該根據每人的實際情況而定,何況借鑒終歸是借鑒,沒人能代替自己的雙腳走路。
趙德明
2018年6月25日于觀瀾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