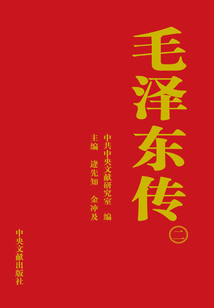
毛澤東傳(2)
最新章節(jié)
- 第22章 籌建新中國(guó)
- 第21章 將革命進(jìn)行到底
- 第20章 大決戰(zhàn)的日日夜夜(下)
- 第19章 大決戰(zhàn)的日日夜夜(上)
- 第18章 決戰(zhàn)前夕
- 第17章 東移西柏坡
第1章 全民族抗戰(zhàn)的爆發(fā)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深夜,在北平的南大門(mén)盧溝橋附近,日本侵略軍突然向駐守在這里的中國(guó)軍隊(duì)發(fā)動(dòng)進(jìn)攻,中國(guó)軍隊(duì)被迫奮起還擊。盧溝橋反抗日本侵略軍的槍聲,標(biāo)志著中國(guó)人民期待已久的全民族抗戰(zhàn)終于開(kāi)始。
第二天,消息傳到延安。
那時(shí)候,整個(gè)局勢(shì)會(huì)怎樣發(fā)展,還不十分明朗。這以前,日本在華北已曾多次制造過(guò)地方性的武裝挑釁事件。盧溝橋所發(fā)生的,究竟是一次地方事件,還是日本帝國(guó)主義對(duì)華發(fā)動(dòng)全面軍事進(jìn)攻的開(kāi)始?許多人一時(shí)還不能看得那么清楚。毛澤東和中共中央?yún)s立刻作出判斷:中華民族已處在生死存亡的關(guān)鍵時(shí)刻,只有全民族團(tuán)結(jié)抗戰(zhàn),才是中國(guó)生存和發(fā)展的唯一出路,必須立刻旗幟鮮明地喊出這個(gè)口號(hào)。
七月八日,也就是盧溝橋事變剛剛發(fā)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率先向全國(guó)發(fā)出通電,大聲疾呼:“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shí)行抗戰(zhàn),才是我們的出路。”號(hào)召:“全中國(guó)同胞,政府與軍隊(duì),團(tuán)結(jié)起來(lái),筑成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堅(jiān)固長(zhǎng)城,抵抗日寇的侵掠!”[1]
這是根據(jù)歷史發(fā)展進(jìn)程提出的基本政治口號(hào)。這個(gè)口號(hào),成了全國(guó)人民一致行動(dòng)的具體目標(biāo)。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如果不能及時(shí)地提出這種具體目標(biāo),是談不上政治領(lǐng)導(dǎo)的。
國(guó)民黨政府在空前嚴(yán)重的民族危機(jī)面前,鑒于自身的統(tǒng)治已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guān)頭,也在進(jìn)行抵抗侵略的準(zhǔn)備。但他們沒(méi)有完全放棄對(duì)日媾和的幻想,仍希望把盧溝橋事變限制在“地方事件”的范圍內(nèi)。他們對(duì)共產(chǎn)黨的疑忌太深了,在國(guó)共合作的談判中不斷橫生枝節(jié),使談判遲遲不能取得突破性的進(jìn)展。當(dāng)時(shí)在延安擔(dān)任軍委參謀長(zhǎng)的蕭勁光回憶道:“國(guó)家的危亡迫在眉睫,而我黨與國(guó)民黨關(guān)于建立統(tǒng)一戰(zhàn)線,紅軍改編為國(guó)民革命軍的具體問(wèn)題的談判卻遲遲沒(méi)有結(jié)果。我們?cè)谘影驳耐径既缱槡郑箲]萬(wàn)分。”[2]
面對(duì)這種復(fù)雜的局勢(shì),毛澤東始終保持著沉著冷靜的態(tài)度,進(jìn)行總攬全局的考慮和部署。七月十四日,他在內(nèi)部發(fā)出指示,提出當(dāng)前工作的總方針。這個(gè)總方針包括兩個(gè)方面:“此時(shí)各方任務(wù),在一面促成蔣氏建立全國(guó)抗戰(zhàn)之最后決心(此點(diǎn)恐尚有問(wèn)題);一面自己真正地準(zhǔn)備一切抗日救亡步驟;并同南京一道去做。”“蓋此時(shí)是全國(guó)存亡關(guān)頭,又是蔣及國(guó)民黨徹底轉(zhuǎn)變政策之關(guān)頭,故我們及各方做法,必須適合于上述之總方針。”[3]毛澤東深知,要促成蔣介石下定全國(guó)抗戰(zhàn)的最后決心,單靠共產(chǎn)黨的力量是不夠的,必須推動(dòng)社會(huì)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努力在全國(guó)造成一種聲勢(shì)。毛澤東指定南漢宸,以毛澤東及紅軍代表的名義同華北當(dāng)局及各界領(lǐng)袖協(xié)商團(tuán)結(jié)抗日的具體辦法。他自己在七月十四日至二十日間四次寫(xiě)信或致電給閻錫山,要求“密切合作,共挽危局”。他又指定張?jiān)埔荼甲邇蓮V當(dāng)局之間,“求得他們贊助堅(jiān)決抗戰(zhàn)與國(guó)共合作的方針,求得他們開(kāi)展愛(ài)國(guó)運(yùn)動(dòng),積極救亡”。[4]他還和張聞天一起致電葉劍英:“請(qǐng)答復(fù)救國(guó)會(huì)及各方:他們要求各事,我們都同意,并且正在做。請(qǐng)他們努力在外面與政府黨部及各界領(lǐng)袖協(xié)商,迅速組成對(duì)付大事變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惟有全國(guó)團(tuán)結(jié),才能戰(zhàn)勝日本。”[5]
在推動(dòng)蔣介石下定抗日決心的同時(shí),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和紅軍自身積極地進(jìn)行抗日參戰(zhàn)的一切準(zhǔn)備,并表明愿同南京一道去做。七月十三日,在延安召開(kāi)共產(chǎn)黨員和機(jī)關(guān)工作人員的緊急會(huì)議,毛澤東到會(huì)動(dòng)員,號(hào)召“每一個(gè)共產(chǎn)黨員與抗日的革命者,應(yīng)該沉著地完成一切必須準(zhǔn)備,隨時(shí)出動(dòng)到抗日前線”。十四日,毛澤東等致電葉劍英,要他轉(zhuǎn)告蔣介石:“紅軍主力準(zhǔn)備隨時(shí)出動(dòng)抗日,已令各軍十天內(nèi)準(zhǔn)備完畢,待令出動(dòng)。”[6]十八日,延安召開(kāi)市民大會(huì),毛澤東到會(huì)講演。據(jù)當(dāng)時(shí)報(bào)紙記載:“演詞激昂,聽(tīng)眾均磨拳擦掌,熱血沸騰,愿赴抗日戰(zhàn)場(chǎng),與日寇決一死戰(zhàn)。”[7]
空前的民族危機(jī)和共產(chǎn)黨的積極主張,一掃國(guó)內(nèi)的沉悶政治空氣。要求武裝抵抗日本侵略的熱情空前高漲,到處沸騰起來(lái)了。“各地的大資產(chǎn)階級(jí),國(guó)民黨的各地黨部,國(guó)民革命軍的將領(lǐng)及各地方的軍政長(zhǎng)官,也表示了他們的積極,提出了抗戰(zhàn)的要求。全國(guó)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到處要求行動(dòng)的統(tǒng)一,并且到處組織了這類統(tǒng)一救亡的組織,這使全國(guó)抗日救亡運(yùn)動(dòng)前進(jìn)了一大步。”[8]
七月十七日,盧溝橋事變后的第十天,蔣介石在廬山發(fā)表談話,宣布:“如果戰(zhàn)端一開(kāi),就是地?zé)o分南北,年無(wú)分老幼,無(wú)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zhàn)之責(zé)任。”[9]這對(duì)蔣介石來(lái)說(shuō),是一個(gè)大的進(jìn)步。
蔣介石談話發(fā)表后,毛澤東很快就表示歡迎,他說(shuō):“這個(gè)談話,確定了準(zhǔn)備抗戰(zhàn)的方針,為國(guó)民黨多年以來(lái)在對(duì)外問(wèn)題上的第一次正確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們和全國(guó)同胞的歡迎。”[10]同時(shí),他也清醒地看到蔣介石在對(duì)內(nèi)政策上沒(méi)有提出任何改進(jìn)措施,特別是沒(méi)有宣布全國(guó)人民的總動(dòng)員,沒(méi)有改革舊的政治機(jī)構(gòu),沒(méi)有提出改良人民生活的綱領(lǐng),對(duì)中國(guó)共產(chǎn)黨仍不允許公開(kāi)活動(dòng)。這是一個(gè)很大的矛盾。
局勢(shì)越復(fù)雜,對(duì)毛澤東說(shuō)來(lái),仿佛倒越能顯示出他善于在千頭萬(wàn)緒中迅速抓住要領(lǐng)的本事。蔣介石廬山講話后不到一個(gè)星期,毛澤東在七月二十三日發(fā)表《反對(duì)日本進(jìn)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旗幟鮮明地提出對(duì)付日本的進(jìn)攻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方針、兩套不同的辦法和兩個(gè)不同的前途。一種是堅(jiān)決抗戰(zhàn)的方針,一種是妥協(xié)退讓的方針。在堅(jiān)決抗戰(zhàn)的方針下又必須有一整套的辦法,才能達(dá)到目的。這就是:(一)全國(guó)軍隊(duì)的總動(dòng)員;(二)全國(guó)人民的總動(dòng)員,給人民以愛(ài)國(guó)的自由;(三)改革政治機(jī)構(gòu),使政府和人民相結(jié)合;(四)抗日的外交;(五)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綱領(lǐng),并立即開(kāi)始實(shí)行;(六)國(guó)防教育;(七)抗日的財(cái)政經(jīng)濟(jì)政策;(八)全中國(guó)人民、政府和軍隊(duì)團(tuán)結(jié)起來(lái),筑成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堅(jiān)固的長(zhǎng)城。另一套是同它相反的辦法。毛澤東指出:實(shí)行前一種方針和辦法“就一定得一個(gè)驅(qū)逐日本帝國(guó)主義、實(shí)現(xiàn)中國(guó)自由解放的前途”。實(shí)行后一種方針和辦法“就一定得一個(gè)日本帝國(guó)主義占領(lǐng)中國(guó)、中國(guó)人民都做牛馬奴隸的前途”。他表示:共產(chǎn)黨人“愿同國(guó)民黨人和全國(guó)同胞一道為保衛(wèi)國(guó)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對(duì)一切游移、動(dòng)搖、妥協(xié)、退讓,實(shí)行堅(jiān)決的抗戰(zhàn)”。
文章又指出,為了這樣做,“中心關(guān)鍵在國(guó)共兩黨的親密合作”,“團(tuán)結(jié)要是真正的團(tuán)結(jié),爾詐我虞是不行的”。他強(qiáng)調(diào):“國(guó)人應(yīng)從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頓在恰當(dāng)?shù)奈恢谩T诮裉欤l(shuí)要是在團(tuán)結(jié)兩個(gè)字上不生長(zhǎng)些誠(chéng)意,他即使不被人唾罵,也當(dāng)清夜捫心,有點(diǎn)兒羞愧。”[11]這幾句話正是對(duì)國(guó)民黨的批評(píng)。但是這種批評(píng),正如英國(guó)記者貝特蘭所說(shuō):“是很坦白的,而且非常誠(chéng)懇的。顯然他注重的并不是指摘‘缺點(diǎn)’,而是堅(jiān)持他認(rèn)為更好的政策,他的正面主張是很充足的。”[12]
在推動(dòng)國(guó)民黨進(jìn)行全國(guó)性抗戰(zhàn)的同時(shí),紅軍參戰(zhàn)的實(shí)際準(zhǔn)備工作也在加緊進(jìn)行。七月十四日,毛澤東、朱德已向彭德懷、任弼時(shí)等紅軍將領(lǐng)下達(dá)“十天準(zhǔn)備完畢,待命抗日”的命令。同時(shí)要紅軍各路將領(lǐng)到云陽(yáng)集中,討論紅軍改編問(wèn)題,并對(duì)紅軍參戰(zhàn)、部隊(duì)編制等做了周密的部署。聶榮臻回憶道:“到七月中旬,盡管同國(guó)民黨政府的談判還沒(méi)有結(jié)果,我們已經(jīng)根據(jù)黨中央的指示,開(kāi)始醞釀部隊(duì)的改編工作,著手進(jìn)行開(kāi)赴前線的準(zhǔn)備了。”[13]
隨著華北局勢(shì)日趨嚴(yán)重,蔣介石仍不肯下達(dá)紅軍改編的命令,但幾番催促紅軍迅速出動(dòng)。七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張聞天致電周恩來(lái)等,決定:“紅軍八月十五日改編好,二十日出動(dòng)抗日。”但紅軍“三個(gè)師以上必須設(shè)總指揮部,朱正彭副,并設(shè)政治部,任弼時(shí)為主任,鄧小平為副主任(不要康澤),以便指揮作戰(zhàn)”[14]。
由于紅軍即將開(kāi)赴前線,一個(gè)新的問(wèn)題提到中國(guó)共產(chǎn)黨的面前:紅軍在抗日前線應(yīng)該怎樣作戰(zhàn)?這時(shí)周恩來(lái)、博古已赴云陽(yáng)出席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召開(kāi)的紅軍高級(jí)干部會(huì)議。毛澤東和張聞天致電他們,對(duì)會(huì)議提出明確的指導(dǎo)意見(jiàn),其中最重要的是把發(fā)展游擊戰(zhàn)爭(zhēng)提到突出的地位。這是一個(gè)有著遠(yuǎn)大戰(zhàn)略眼光的創(chuàng)見(jiàn)。電報(bào)說(shuō):“(甲)在整個(gè)戰(zhàn)略方針下執(zhí)行獨(dú)立自主的分散作戰(zhàn)的游擊戰(zhàn)爭(zhēng),而不是陣地戰(zhàn),也不是集中作戰(zhàn),因此不能在戰(zhàn)役戰(zhàn)術(shù)上受束縛,只有如此才能發(fā)揮紅軍特長(zhǎng),給日寇以相當(dāng)打擊。(乙)依上述原則,在開(kāi)始階段,紅軍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為適宜,兵力過(guò)大,不能發(fā)揮游擊戰(zhàn),而易受敵人的集中打擊,其余兵力依戰(zhàn)爭(zhēng)發(fā)展,逐漸使用之。”[15]
同一天,毛澤東和張聞天又致電朱德、周恩來(lái)轉(zhuǎn)彭德懷、任弼時(shí),針對(duì)蔣介石已經(jīng)表露出來(lái)的準(zhǔn)備將紅軍分割使用、同日軍硬拼消耗、逐步給以削弱以至消滅的企圖,提醒他們:“紅軍抗日出動(dòng)的路線、出動(dòng)的兵力、作戰(zhàn)的方法都不應(yīng)請(qǐng)求蔣介石決定頒發(fā),這些都只能待適當(dāng)?shù)臅r(shí)機(jī),由我們提出與之商定方不吃虧。”[16]這些意見(jiàn),對(duì)紅軍改編后保持獨(dú)立性和黨對(duì)這支軍隊(duì)的領(lǐng)導(dǎo)有重要意義。
七月三十日,北平、天津相繼陷落。“平津的失守是‘九一八’后中華民族的最大損失,這使中國(guó)失去華北與中國(guó)西北部的最重要的屏障”[17]。接著,日軍沿平漢、平綏、津浦三條鐵路作扇形推進(jìn),向華北地區(qū)展開(kāi)大規(guī)模進(jìn)攻。在日軍的進(jìn)逼下,蔣介石密邀毛澤東、朱德、周恩來(lái)到南京共商國(guó)防問(wèn)題[18]。中共中央決定由朱德、周恩來(lái)、葉劍英前往。八月四日,毛澤東和張聞天又電請(qǐng)朱、周、葉到南京后代表中共提出對(duì)整個(gè)國(guó)防問(wèn)題的建議,指出:“總的戰(zhàn)略方針暫時(shí)是攻勢(shì)防御,應(yīng)給進(jìn)攻之?dāng)骋詺灉绲姆垂ィ瑳Q不能是單純防御。將來(lái)準(zhǔn)備轉(zhuǎn)變到戰(zhàn)略進(jìn)攻,收復(fù)失地。”這個(gè)方針是中肯的,是切中當(dāng)時(shí)國(guó)民黨軍隊(duì)?wèi)?zhàn)略上的弊端的。意見(jiàn)中還說(shuō):“正規(guī)戰(zhàn)與游擊戰(zhàn)相配合,游擊戰(zhàn)以紅軍與其他適宜部隊(duì)及人民武裝擔(dān)任之,在整個(gè)戰(zhàn)略部署下給與獨(dú)立自主的指揮權(quán)。”“擔(dān)任游擊戰(zhàn)之部隊(duì)依地形條件及戰(zhàn)況之發(fā)展適當(dāng)使用其兵力,為適應(yīng)游擊戰(zhàn)性質(zhì)原則上應(yīng)分開(kāi)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意見(jiàn)最后強(qiáng)調(diào):“發(fā)動(dòng)人民的武裝自衛(wèi)戰(zhàn)是保證軍隊(duì)作戰(zhàn)勝利的中心一環(huán),對(duì)此方針游移是必?cái)≈馈!盵19]
五日,毛澤東收到紅軍總部從云陽(yáng)發(fā)來(lái)的《關(guān)于全國(guó)對(duì)日抗戰(zhàn)及紅軍參戰(zhàn)問(wèn)題的意見(jiàn)》和《關(guān)于紅軍主力出去抗戰(zhàn)的意見(jiàn)》,主張:我們對(duì)參戰(zhàn)不遲疑,但要求獨(dú)立自主擔(dān)任一方面作戰(zhàn)任務(wù),發(fā)揮紅軍運(yùn)動(dòng)戰(zhàn)、游擊戰(zhàn)、持久戰(zhàn)的優(yōu)點(diǎn);不拒絕紅軍主力出動(dòng),但要求足夠的補(bǔ)充與使用兵力的自由;不反對(duì)開(kāi)赴察、綏,但要求給便于作戰(zhàn)的察、綏、晉三角地區(qū)與便于補(bǔ)充聯(lián)絡(luò)的后方。毛澤東和張聞天在回電中強(qiáng)調(diào):紅軍擔(dān)負(fù)的作戰(zhàn)任務(wù)應(yīng)該是“獨(dú)立自主的游擊運(yùn)動(dòng)戰(zhàn),鉗制敵人大部分,消滅敵人一部”;要求指定冀察晉綏四省交界地區(qū),而不是三角地區(qū),作為協(xié)助友軍作戰(zhàn)的地區(qū);“我們事實(shí)上只宜作側(cè)面戰(zhàn),不宜作正面戰(zhàn),故不宜于以獨(dú)當(dāng)一面的語(yǔ)意提出”;同時(shí),要求本著“按情況使用兵力的原則,在此原則下,承認(rèn)開(kāi)拔主力”[20]。顯然,毛澤東對(duì)紅軍作戰(zhàn)方針及兵力使用等問(wèn)題采取慎重的態(tài)度。
他所以一再?gòu)?qiáng)調(diào)這些問(wèn)題,除考慮到對(duì)日作戰(zhàn)的長(zhǎng)期性和紅軍自身的特點(diǎn)外,還由于看到蔣介石對(duì)待國(guó)共關(guān)系問(wèn)題上已表現(xiàn)出許多不正常的現(xiàn)象:一面要紅軍全部出動(dòng),一方面卻在陜甘一帶部署了十個(gè)師兵力。不久前在南方游擊隊(duì)改編時(shí)又出現(xiàn)閩粵邊部隊(duì)被國(guó)民黨軍隊(duì)誘騙繳槍的事件,毛澤東認(rèn)為這是“極嚴(yán)重教訓(xùn),紅軍各部都應(yīng)引為深戒”[21]。他還認(rèn)為:“平津失陷后蔣之困難更加,但抗戰(zhàn)決心與合作誠(chéng)意增加至何種程度待爾后證明,此時(shí)宜緩不宜急,緩則有效,急則無(wú)功。”[22]
由于紅軍出兵在即,對(duì)有些問(wèn)題的認(rèn)識(shí)又未必完全一致,毛澤東認(rèn)為有必要對(duì)平津失守后的形勢(shì)和黨的任務(wù)進(jìn)行一次全盤(pán)的討論,統(tǒng)一思想。他提出:“在紅軍開(kāi)動(dòng)時(shí)開(kāi)一次政治局會(huì)議,同時(shí)討論作戰(zhàn)問(wèn)題,地點(diǎn)在洛川。”[23]
當(dāng)時(shí)中央政治局成員一時(shí)來(lái)不及集中,因此,八月九日,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和各部門(mén)負(fù)責(zé)人先開(kāi)了一次會(huì)。
這是盧溝橋事變發(fā)生后,中共中央召開(kāi)的一次重要會(huì)議。會(huì)上,由張聞天作報(bào)告。毛澤東在會(huì)上講話,分析了國(guó)內(nèi)的政治形勢(shì),他十分明確地?cái)嘌裕骸皯?yīng)估計(jì)大戰(zhàn)已經(jīng)到來(lái),新的階段在七月七日晚上即已開(kāi)始。抗戰(zhàn)已經(jīng)開(kāi)始,準(zhǔn)備抗戰(zhàn)的階段已經(jīng)結(jié)束。”對(duì)國(guó)民黨的狀況,他采取有分析的態(tài)度,說(shuō)道:“國(guó)民黨轉(zhuǎn)變已大進(jìn)一步,離徹底轉(zhuǎn)變還遠(yuǎn)”。“蔣介石的抗戰(zhàn)決心是日本逼起來(lái)的,應(yīng)戰(zhàn)主義是危險(xiǎn)的。但這還要很多的工作才能轉(zhuǎn)變,應(yīng)戰(zhàn)主義實(shí)際是節(jié)節(jié)退卻”。談到紅軍的下一步行動(dòng)時(shí),毛澤東說(shuō):“紅軍今日以前是準(zhǔn)備調(diào)動(dòng),今日以后是實(shí)行開(kāi)動(dòng)。紅軍應(yīng)當(dāng)是獨(dú)立自主的指揮與分散的游擊戰(zhàn)爭(zhēng),必須保持獨(dú)立自主的指揮,才能發(fā)揮紅軍的長(zhǎng)處,集團(tuán)的作戰(zhàn)是不行的。同時(shí),還要估計(jì)到特別的情形,防人之心不可無(wú),應(yīng)有戒心,保障紅軍之發(fā)展擴(kuò)大!”在反傾向問(wèn)題上,毛澤東同意張聞天報(bào)告中所指出的:“一是急躁病,二是適應(yīng)國(guó)民黨的適合主義”。提出要“保持組織的獨(dú)立性、批評(píng)的自由”。[24]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八月五日和張聞天一起發(fā)出的電報(bào)中說(shuō)的是紅軍應(yīng)當(dāng)實(shí)行“獨(dú)立自主的游擊運(yùn)動(dòng)戰(zhàn)”,而在僅僅四天后的這次會(huì)議上他卻談到“紅軍應(yīng)當(dāng)是獨(dú)立自主的指揮與分散的游擊戰(zhàn)爭(zhēng)”。可見(jiàn),游擊戰(zhàn)和運(yùn)動(dòng)戰(zhàn)的關(guān)系是他在紅軍出動(dòng)前夜這個(gè)關(guān)鍵時(shí)刻反復(fù)思考的關(guān)鍵問(wèn)題。
這次會(huì)上,毛澤東還對(duì)七月二十三日文章中的抗日八項(xiàng)辦法提出補(bǔ)充,初步形成“十大綱領(lǐng)”。四天后,毛澤東在會(huì)見(jiàn)美國(guó)女記者海倫?斯諾時(shí),將這個(gè)文件交給她。海倫后來(lái)回憶:“毛澤東拍案而起,他滿面通紅,兩眼閃光地說(shuō):如果有南京政府的合作,這十大綱領(lǐng)就能實(shí)現(xiàn),我們就能打倒日本帝國(guó)主義。否則,中國(guó)就要滅亡!他憤怒地重復(fù)著后一句話。”[25]
這次會(huì)議為十多天后召開(kāi)的洛川會(huì)議做了準(zhǔn)備。
紅軍各部已陸續(xù)準(zhǔn)備就緒,隨時(shí)準(zhǔn)備開(kāi)赴前線。但是,在南京的談判卻并不順利,國(guó)民黨方面在各種問(wèn)題上諸多留難。直到八月十三日淞滬抗戰(zhàn)爆發(fā),談判才出現(xiàn)轉(zhuǎn)機(jī)。
日本軍隊(duì)的大舉進(jìn)攻上海,使抗日戰(zhàn)爭(zhēng)的形勢(shì)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它直接威脅到國(guó)民黨統(tǒng)治集團(tuán)的心臟地區(qū)和英、美等國(guó)的在華利益,使蔣介石感到不得不進(jìn)行全國(guó)性的抵抗,否則自身的統(tǒng)治也難以保持,于是,在國(guó)共談判中表現(xiàn)出較多的合作愿望。周恩來(lái)后來(lái)回憶:“我同葉劍英參謀長(zhǎng)到南京,開(kāi)始蔣介石還沒(méi)有決定給八路軍以名義,但是到上海打響了,他(指蔣介石)從廬山跑回來(lái),覺(jué)得這是全面戰(zhàn)爭(zhēng)了,才發(fā)表了八路軍的番號(hào),緊跟著又發(fā)表了十八集團(tuán)軍的番號(hào),要我們的軍隊(duì)去打仗。”[26]根據(jù)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周恩來(lái)等同國(guó)民黨經(jīng)過(guò)反復(fù)談判,終于達(dá)成協(xié)議:朱德、彭德懷為八路軍正、副總指揮;主力紅軍充任戰(zhàn)略游擊隊(duì),執(zhí)行側(cè)面戰(zhàn)、協(xié)助友軍、擾亂與鉗制日軍大部并消滅一部的作戰(zhàn)任務(wù)。
這時(shí),在外地的政治局委員已陸續(xù)趕回陜北。中共中央認(rèn)為在洛川召開(kāi)政治局會(huì)議的條件已經(jīng)成熟。由于會(huì)議要討論軍事問(wèn)題,吸收了前方主要將領(lǐng)參加,實(shí)際上成為一次政治局?jǐn)U大會(huì)議。
八月二十日,毛澤東從延安出發(fā)前往洛川。會(huì)址設(shè)在洛川城郊馮家村的一所小學(xué)里,這是一個(gè)比較偏僻而安全的地方,又正處在延安同前方將領(lǐng)所在的云陽(yáng)的中間。毛澤東住在村中一座破廟里。蕭勁光回憶說(shuō):“黨中央就在這樣一個(gè)條件簡(jiǎn)陋的小村里,召開(kāi)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洛川會(huì)議。”[27]
洛川會(huì)議是在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召開(kāi)的。會(huì)議的議程是:(一)政治任務(wù)問(wèn)題;(二)軍事問(wèn)題;(三)國(guó)共兩黨關(guān)系問(wèn)題。毛澤東在會(huì)上做了軍事問(wèn)題和國(guó)共兩黨關(guān)系的報(bào)告,并作了多次發(fā)言。
他分析了抗日戰(zhàn)爭(zhēng)的形勢(shì),指出:現(xiàn)在已經(jīng)開(kāi)始政府的抗戰(zhàn),而且得到人民的擁護(hù),但人民還沒(méi)有大規(guī)模地參加,這就成為現(xiàn)在的弱點(diǎn)與今后的任務(wù)——使成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zhàn)。“我們的方針最基本的是持久戰(zhàn),不是速?zèng)Q戰(zhàn),持久戰(zhàn)的結(jié)果是中國(guó)勝利。”[28]
關(guān)于紅軍的基本任務(wù),他提出了五條:“(一)創(chuàng)造根據(jù)地;(二)鉗制與消滅敵人;(三)配合友軍作戰(zhàn)(戰(zhàn)略支援任務(wù));(四)保存與擴(kuò)大紅軍;(五)爭(zhēng)取民族革命戰(zhàn)爭(zhēng)領(lǐng)導(dǎo)權(quán)。”并且說(shuō)明:前四條是要實(shí)現(xiàn)的,后一條是要爭(zhēng)取的。他著重談了紅軍的戰(zhàn)略方針,那就是:“獨(dú)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zhàn)爭(zhēng)(包括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tuán)與在平原發(fā)展游擊戰(zhàn)爭(zhēng),但著重于山地)”。這種獨(dú)立自主是在統(tǒng)一戰(zhàn)略下的“相對(duì)的獨(dú)立自主”。游擊戰(zhàn)爭(zhēng)的作戰(zhàn)原則是:“分散以發(fā)動(dòng)群眾,集中以消滅敵人,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29]
毛澤東在洛川會(huì)議上明確地提出紅軍在抗日戰(zhàn)爭(zhēng)現(xiàn)階段的戰(zhàn)略方針以游擊戰(zhàn)爭(zhēng)為主。這是一個(gè)重大的戰(zhàn)略轉(zhuǎn)變。中國(guó)共產(chǎn)黨的軍事戰(zhàn)略,從國(guó)內(nèi)戰(zhàn)爭(zhēng)到抗日戰(zhàn)爭(zhēng)前期,經(jīng)歷過(guò)兩次戰(zhàn)略轉(zhuǎn)變:第一次是國(guó)內(nèi)游擊戰(zhàn)爭(zhēng)向國(guó)內(nèi)正規(guī)戰(zhàn)爭(zhēng)的轉(zhuǎn)變,這個(gè)轉(zhuǎn)變?cè)龅胶艽蟮睦щy;第二次是國(guó)內(nèi)正規(guī)戰(zhàn)爭(zhēng)向抗日游擊戰(zhàn)爭(zhēng)的轉(zhuǎn)變。毛澤東一年多后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huì)上談到后一次戰(zhàn)略轉(zhuǎn)變時(shí)說(shuō):這個(gè)轉(zhuǎn)變是處于兩個(gè)不同的戰(zhàn)爭(zhēng)過(guò)程之間,是在敵人、友軍、戰(zhàn)場(chǎng)都有變化的特殊情況下進(jìn)行的一個(gè)極其嚴(yán)重的轉(zhuǎn)變。“在這些特殊的情況下,必須把過(guò)去的正規(guī)軍和運(yùn)動(dòng)戰(zhàn),轉(zhuǎn)變成為游擊軍(說(shuō)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說(shuō)的組織性和紀(jì)律性)和游擊戰(zhàn),才能同敵情和任務(wù)相符合。但是這樣的一個(gè)轉(zhuǎn)變,便在現(xiàn)象上表現(xiàn)為一個(gè)倒退的轉(zhuǎn)變,因此這個(gè)轉(zhuǎn)變應(yīng)該是非常困難的。”[30]這一轉(zhuǎn)變,對(duì)整個(gè)抗日戰(zhàn)爭(zhēng)的堅(jiān)持、發(fā)展和勝利,對(duì)中國(guó)共產(chǎn)黨的前途,關(guān)系非常之大。毛澤東在抗日戰(zhàn)爭(zhēng)剛剛開(kāi)始、紅軍還沒(méi)有開(kāi)赴前線的時(shí)候,在仔細(xì)考察并分析了主客觀實(shí)際情況后,便明確地及時(shí)地提出要實(shí)行這個(gè)戰(zhàn)略轉(zhuǎn)變,充分表現(xiàn)了他的遠(yuǎn)見(jiàn)卓識(shí)。
關(guān)于國(guó)共關(guān)系,他指出現(xiàn)在統(tǒng)一戰(zhàn)線正在成熟中,但國(guó)民黨還在限制和破壞我們,我們是繼續(xù)有原則地讓步,即保持黨和紅軍的獨(dú)立性,要有自由,而采取不決裂的方針。根據(jù)大革命失敗的教訓(xùn),“獨(dú)立性是組織的、政治的獨(dú)立問(wèn)題兩方面”[31]。
在會(huì)上,毛澤東還提出,主力部隊(duì)開(kāi)赴前線后,要留下一支部隊(duì)鞏固陜甘寧根據(jù)地,使它成為中國(guó)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抗日力量的大本營(yíng)。這支部隊(duì)稱為留守兵團(tuán),以后在保衛(wèi)陜甘寧根據(jù)地的斗爭(zhēng)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會(huì)議在民主的氣氛中進(jìn)行討論。來(lái)自不同崗位的與會(huì)者對(duì)毛澤東提出的黨對(duì)紅軍的領(lǐng)導(dǎo)、堅(jiān)持獨(dú)立自主的指揮原則、開(kāi)展山地游擊戰(zhàn)及紅軍擔(dān)負(fù)的任務(wù)等問(wèn)題,取得了一致意見(jiàn)。對(duì)游擊戰(zhàn)和運(yùn)動(dòng)戰(zhàn)的關(guān)系,會(huì)上有些不同意見(jiàn),但由于紅軍急于出發(fā),沒(méi)有展開(kāi)充分的討論。出席這次會(huì)議的蕭勁光回憶道:
“洛川會(huì)議上在討論軍事指導(dǎo)方針中盡管意見(jiàn)不同,但出發(fā)點(diǎn)都是一個(gè),就是如何在出征以后更有利地打擊敵人,更有利于我軍的發(fā)展壯大。當(dāng)然,它也說(shuō)明同志們?cè)诋?dāng)時(shí)對(duì)中國(guó)革命戰(zhàn)爭(zhēng)的規(guī)律性、對(duì)抗日游擊戰(zhàn)爭(zhēng)的戰(zhàn)略地位問(wèn)題在認(rèn)識(shí)上有差異。在以后抗日戰(zhàn)爭(zhēng)的實(shí)踐中,逐步證明了毛澤東同志的意見(jiàn)是正確的,是高瞻遠(yuǎn)矚的。”[32]
為了適應(yīng)戰(zhàn)爭(zhēng)形勢(shì)的需要,會(huì)議決定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huì)成員增加為十一人,書(shū)記是毛澤東,副書(shū)記是朱德、周恩來(lái)。
會(huì)議還通過(guò)了《中央關(guān)于目前形勢(shì)與黨的任務(wù)的決定》、《抗日救國(guó)十大綱領(lǐng)》和毛澤東為中央宣傳部門(mén)起草的宣傳鼓動(dòng)提綱《為動(dòng)員一切力量爭(zhēng)取抗戰(zhàn)勝利而斗爭(zhēng)》。毛澤東認(rèn)為這次通過(guò)的《抗日救國(guó)十大綱領(lǐng)》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他在發(fā)言中作了說(shuō)明:“兩個(gè)政策,兩個(gè)前途——單純政府的抗戰(zhàn)政策與我們?nèi)娴娜褡宓目箲?zhàn)政策。爭(zhēng)取堅(jiān)持抗戰(zhàn),爭(zhēng)取勝利的前途,避免大分裂、大叛變。”“目前極需要把國(guó)共兩黨區(qū)別清楚。十大綱領(lǐng)的提出,就是與國(guó)民黨單純抗戰(zhàn)的區(qū)別。”[33]這些,同他在《反對(duì)日本進(jìn)攻的方針、方法和前途》中的看法是相連貫的。以后一個(gè)月中的種種事實(shí),使他對(duì)問(wèn)題看得更清楚了,意見(jiàn)也更完備了。
洛川會(huì)議結(jié)束后,中共中央又在八月二十七日組織了一次座談會(huì),座談會(huì)所討論的,是毛澤東正在思考中的更深層次的問(wèn)題。討論的題目中,第一個(gè)就是:在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是共產(chǎn)黨吸引國(guó)民黨,還是國(guó)民黨吸引共產(chǎn)黨?毛澤東在座談會(huì)上先作了說(shuō)明。他說(shuō):“兩個(gè)階級(jí)的企圖,各在自己階級(jí)立場(chǎng)上出發(fā)。”“無(wú)產(chǎn)階級(jí)的政治和組織程度比資產(chǎn)階級(jí)高,所以統(tǒng)一戰(zhàn)線由無(wú)產(chǎn)階級(jí)提出。”他把這一次國(guó)共合作同第一次作了比較,認(rèn)為那時(shí)孫中山、廖仲愷所代表的國(guó)民黨左派要勇敢些,現(xiàn)在的國(guó)民黨當(dāng)局更膽小些,更小氣些,而且是自覺(jué)地來(lái)限制我們。他們正在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長(zhǎng)期過(guò)程中,有計(jì)劃地吸引共產(chǎn)黨,從各方面影響你,以幾千條線索來(lái)套我們。我們有些人容易上當(dāng),要有自覺(jué),要使農(nóng)民與小資產(chǎn)階級(jí)隨著我黨走。國(guó)民黨內(nèi)也有些人動(dòng)搖于國(guó)共兩黨之間,共產(chǎn)黨吸引國(guó)民黨的條件是存在著的。“兩黨互相吸引的問(wèn)題,要在斗爭(zhēng)中來(lái)解決。”[34]他在座談會(huì)結(jié)束時(shí)著重強(qiáng)調(diào),統(tǒng)一戰(zhàn)線建立以后,主要危險(xiǎn)是右傾機(jī)會(huì)主義,在各方面表現(xiàn)出來(lái)的就是投降主義傾向,要注意對(duì)黨內(nèi)加強(qiáng)教育。
為什么毛澤東在抗日戰(zhàn)爭(zhēng)初期就尖銳地提出這個(gè)問(wèn)題?這是當(dāng)時(shí)已經(jīng)出現(xiàn)的大量事實(shí)在他頭腦中引起的反應(yīng)。兩個(gè)月后,毛澤東回顧這一時(shí)期的情況:
“一方面,中國(guó)資產(chǎn)階級(jí)的妥協(xié)性,國(guó)民黨實(shí)力上的優(yōu)勢(shì),國(guó)民黨三中全會(huì)的宣言和決議對(duì)于共產(chǎn)黨的污蔑和侮辱以及所謂‘停止階級(jí)斗爭(zhēng)’的叫囂,國(guó)民黨關(guān)于‘共產(chǎn)黨投降’的衷心愿望和廣泛宣傳,蔣介石關(guān)于統(tǒng)制共產(chǎn)黨的企圖,國(guó)民黨對(duì)于紅軍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國(guó)民黨對(duì)于抗日民主根據(jù)地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國(guó)民黨七月廬山訓(xùn)練班提出的‘在抗日戰(zhàn)爭(zhēng)中削弱共產(chǎn)黨力量五分之二’的陰謀計(jì)劃,國(guó)民黨對(duì)共產(chǎn)黨干部所施行的升官發(fā)財(cái)酒色逸樂(lè)的引誘,某些小資產(chǎn)階級(jí)急進(jìn)分子在政治上的投降舉動(dòng)(以章乃器為代表),等等情況。”
“另一方面,共產(chǎn)黨內(nèi)理論水平的不平衡,許多黨員的缺乏北伐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兩黨合作的經(jīng)驗(yàn),黨內(nèi)小資產(chǎn)階級(jí)成分的大量存在,一部分黨員對(duì)過(guò)去艱苦斗爭(zhēng)的生活不愿意繼續(xù)的情緒,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遷就國(guó)民黨的無(wú)原則傾向的存在,八路軍中的新軍閥主義傾向的發(fā)生,共產(chǎn)黨參加國(guó)民黨政權(quán)問(wèn)題的發(fā)生,抗日民主根據(jù)地中的遷就傾向的發(fā)生,等等情況。”[35]
由于存在著這兩方面的嚴(yán)重的情況,他認(rèn)為,必須尖銳地提出誰(shuí)領(lǐng)導(dǎo)誰(shuí)的問(wèn)題,必須堅(jiān)決地反對(duì)民族的和階級(jí)的投降主義。否則,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和它所領(lǐng)導(dǎo)的軍隊(duì)就可能被國(guó)民黨吸引過(guò)去,被溶化或消滅掉,中華民族抗日戰(zhàn)爭(zhēng)的勝利前途也會(huì)被葬送掉。
由于大敵當(dāng)前,放在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和紅軍面前的最緊迫的現(xiàn)實(shí)課題,還是紅軍迅速完成改編,開(kāi)赴抗日戰(zhàn)爭(zhēng)前線,打擊日本侵略者。
八月二十二日,洛川會(huì)議的前一天,蔣介石正式發(fā)表朱德、彭德懷為國(guó)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副總指揮。二十五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lái)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和副主席的名義發(fā)布命令,宣布紅軍改名為國(guó)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九月改稱第十八集團(tuán)軍),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任弼時(shí)為政治部主任,鄧小平為副主任,葉劍英為參謀長(zhǎng),左權(quán)為副參謀長(zhǎng)。第八路軍下轄三個(gè)師:第一一五師,第一二〇師,第一二九師。命令指出各師改編為國(guó)民革命軍后,必須加強(qiáng)黨的領(lǐng)導(dǎo),保持和發(fā)揚(yáng)十年斗爭(zhēng)的光榮傳統(tǒng),堅(jiān)決執(zhí)行黨中央與軍委會(huì)的命令,為黨的路線及政策而斗爭(zhēng)。
為了在組織上確保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對(duì)八路軍的絕對(duì)領(lǐng)導(dǎo),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軍委決定,成立前方軍分會(huì)(后稱華北軍分會(huì)),以朱德、彭德懷、任弼時(shí)等九人組成。朱德為書(shū)記,彭德懷為副書(shū)記。十月十日,中共中央軍委又決定,成立軍委總政治部,毛澤東代理主任。
八月三十日,毛澤東由洛川回到延安。
這時(shí),紅軍主力師已改編完畢,從九月二日起,陸續(xù)從山西開(kāi)赴華北前線。
同日本軍隊(duì)作戰(zhàn),對(duì)八路軍來(lái)說(shuō),是一次新的嚴(yán)峻考驗(yàn)。紅軍雖然已有十年內(nèi)戰(zhàn)的經(jīng)驗(yàn),但從來(lái)沒(méi)有同具有現(xiàn)代軍事裝備的帝國(guó)主義國(guó)家軍隊(duì)交過(guò)手。八路軍的作戰(zhàn)方針雖已在洛川會(huì)議上確定下來(lái),但還需要在實(shí)戰(zhàn)中充實(shí)、檢驗(yàn)和完善。八路軍出動(dòng)到華北作戰(zhàn)的情況如何,不僅關(guān)系到自身的生存和發(fā)展,而且關(guān)系到抗日戰(zhàn)爭(zhēng)能否取得勝利。因此,洛川會(huì)議結(jié)束后的兩個(gè)多月里,毛澤東幾乎以全部精力指導(dǎo)八路軍在華北的作戰(zhàn)。
取道山西開(kāi)赴抗日前線,是毛澤東在八月中旬已經(jīng)確定下來(lái)的。為什么先開(kāi)入山西?毛澤東有幾方面的考慮:第一,山西是八路軍開(kāi)赴前線最便捷的地方,又是居高臨下地俯瞰河北平原的地方,可以有力地牽制華北日軍的行進(jìn)。憑借山西寬闊、險(xiǎn)峻而復(fù)雜的地形,不僅有利于阻滯日軍機(jī)械化部隊(duì)的前進(jìn),而且有利于八路軍開(kāi)展山地游擊戰(zhàn),消滅敵人。正如任弼時(shí)所說(shuō):“山西方面地形交通限制了敵人的長(zhǎng)處,恰又補(bǔ)足我們的短處,便利于我們的防守,持久斗爭(zhēng)與打擊敵人。”[36]第二,山西是地方實(shí)力派首領(lǐng)閻錫山的統(tǒng)治地區(qū)。他同日本侵略者和蔣介石之間既有聯(lián)系,又有錯(cuò)綜復(fù)雜的矛盾。日本侵略軍攻陷平津后向山西大舉進(jìn)攻,嚴(yán)重威脅了他在山西的統(tǒng)治地位。蔣介石的軍隊(duì)開(kāi)入山西,又使他深恐自己的地盤(pán)將落入他人之手。因此,他作出一些開(kāi)明的姿態(tài),想拉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和八路軍做他的暫時(shí)同盟者。早在一九三六年底,中共黨員薄一波等經(jīng)北方局同意同閻錫山建立了聯(lián)系。七七事變后,閻錫山又答應(yīng)毛澤東向他提出的建立公開(kāi)的八路軍駐晉辦事處的要求,并且同意八路軍經(jīng)山西開(kāi)赴前線。第三,當(dāng)時(shí)國(guó)民黨企圖將八路軍“分割”使用,規(guī)定八路軍以兩個(gè)師由渭南上車經(jīng)風(fēng)陵渡、同蒲路到代縣附近下車,開(kāi)往蔚縣一帶集中。另外一個(gè)師沿隴海鐵路轉(zhuǎn)平漢鐵路到河北徐水下車,開(kāi)往冀東玉田、遵化一帶開(kāi)展游擊戰(zhàn)爭(zhēng)。毛澤東敏銳地察覺(jué):這樣做,是“分路出動(dòng),使不集中,強(qiáng)使聽(tīng)命”[37],“包含著極大陰謀,決不能認(rèn)為有利,堅(jiān)決不能同意”。[38]因此,他提出“紅軍為安全計(jì),為蔭蔽計(jì),為滿足晉綏渴望計(jì),決走韓城渡河,在侯馬上車到大同集中,再轉(zhuǎn)至懷來(lái),蔚縣,決不走平漢路”,[39]把八路軍三個(gè)師都放在山西,以便于統(tǒng)一領(lǐng)導(dǎo),相互策應(yīng),避免因力量分散而遭遇不測(cè)。
為了落實(shí)八路軍進(jìn)入山西作戰(zhàn)的事宜,九月初,毛澤東派周恩來(lái)和彭德懷一起到太原同閻錫山當(dāng)面商談,可見(jiàn)他對(duì)這次行動(dòng)的極度重視。
當(dāng)時(shí)迫切需要解決的,是八路軍開(kāi)入山西后的作戰(zhàn)區(qū)域問(wèn)題。這就像下棋一樣,開(kāi)始時(shí)的布局是否恰當(dāng),對(duì)以后局勢(shì)的發(fā)展有著至關(guān)重要的影響。
毛澤東和張聞天在八月初曾考慮八路軍出師后集中部署在以恒山山脈為中心的冀察晉綏四省交界地區(qū)。但當(dāng)八路軍開(kāi)赴山西時(shí),華北局勢(shì)已發(fā)生變化。日本侵略軍發(fā)動(dòng)了強(qiáng)大的鉗形攻勢(shì):在北路,沿平綏鐵路西進(jìn),在攻占張家口后折而南下,已于九月十三日占領(lǐng)晉北重鎮(zhèn)大同;在東路,沿正太鐵路向西推進(jìn);準(zhǔn)備兩路會(huì)合,奪取太原。如果仍按原有設(shè)想行動(dòng),一旦出現(xiàn)這種情況,就可能使八路軍的全部主力陷于日軍的鉗形包圍圈內(nèi),這當(dāng)然是十分不利的。毛澤東看清山西戰(zhàn)局可能發(fā)生的這種重大變化,及時(shí)改變?cè)ú渴穑髮寺奋姷娜齻€(gè)師分別部署在晉東北、晉西北、晉南,再圖發(fā)展。他在九月十六日致電正率領(lǐng)八路軍總部準(zhǔn)備東渡黃河的朱德、任弼時(shí)提出:“擬以百十五師位于晉東北,以五臺(tái)為活動(dòng)重心,暫時(shí)在靈丘、淶源,不利時(shí)逐漸南移,改以太行山脈為活動(dòng)區(qū)。以百二十師位于晉西北,以管涔山脈及呂梁山脈之北部為活動(dòng)地區(qū)。以百二十九師位于晉南以太岳山脈為活動(dòng)地區(qū)。”[40]這幾個(gè)地區(qū),后來(lái)成為八路軍在山西敵后堅(jiān)持抗戰(zhàn)的主要支撐點(diǎn)。
第二天,毛澤東致電朱德、彭德懷等,對(duì)改變部署的原因作了進(jìn)一步的說(shuō)明:“此時(shí)如依原計(jì)劃執(zhí)行,將全部處于敵之戰(zhàn)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脈,亦在其大迂回中(設(shè)想敵占太原之情況下),將完全陷入被動(dòng)地位。”[41]兩天后他又提醒:“敵于太原,志在必得,此時(shí)部署應(yīng)遠(yuǎn)看一步。”[42]
在八路軍出師后不到半個(gè)月內(nèi),毛澤東根據(jù)局勢(shì)的發(fā)展,及時(shí)調(diào)整了八路軍作戰(zhàn)區(qū)域的部署,這對(duì)八路軍實(shí)行戰(zhàn)略展開(kāi),合理布局,創(chuàng)建華北敵后抗日根據(jù)地產(chǎn)生了極為深遠(yuǎn)的意義。
八路軍開(kāi)赴前線后,毛澤東關(guān)心的另一個(gè)焦點(diǎn)是:部隊(duì)在實(shí)戰(zhàn)中能不能堅(jiān)定不移地執(zhí)行洛川會(huì)議確定的“獨(dú)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zhàn)”方針。
實(shí)行這樣重大的戰(zhàn)略轉(zhuǎn)變,是很不容易的。這不僅因?yàn)榧t軍在十年內(nèi)戰(zhàn)后期已習(xí)慣于正規(guī)軍和運(yùn)動(dòng)戰(zhàn),一時(shí)不容易改變過(guò)來(lái);還因?yàn)榭谷諔?zhàn)爭(zhēng)爆發(fā)后,不少人十分興奮,對(duì)戰(zhàn)爭(zhēng)的長(zhǎng)期性和艱巨性認(rèn)識(shí)不足,急于想打一些大仗。聶榮臻回憶道:“在洛川會(huì)議上討論作戰(zhàn)方針時(shí),曾出現(xiàn)過(guò)不贊同游擊戰(zhàn)而主張打運(yùn)動(dòng)戰(zhàn)的分歧意見(jiàn),他(指毛澤東——編者注)擔(dān)心部隊(duì)挺進(jìn)前線后,一些同志蠻干。”[43]毛澤東還擔(dān)心:“整個(gè)華北都是危如累卵。個(gè)別同志對(duì)于這種客觀的必然的趨勢(shì)似乎還沒(méi)有深刻的認(rèn)識(shí),被暫時(shí)情況所誘惑,如果這種觀點(diǎn)不變,勢(shì)必紅軍也同閻錫山相似,陷入于被動(dòng)的、應(yīng)付的、挨打的、被敵各個(gè)擊破的境遇中。”[44]
對(duì)關(guān)鍵性問(wèn)題,毛澤東歷來(lái)是緊抓不放的。在九月中下旬,他接連五次致電前方,提醒他們要以最大決心實(shí)現(xiàn)這個(gè)戰(zhàn)略轉(zhuǎn)變。九月二十一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今日紅軍在決戰(zhàn)問(wèn)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dú)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zhàn)(不是運(yùn)動(dòng)戰(zhàn))。要實(shí)行這樣的方針,就要戰(zhàn)略上有有力部隊(duì)處于敵之翼側(cè),就要以創(chuàng)造根據(jù)地發(fā)動(dòng)群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群眾工作,做群眾工作則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則不能并舉。然而只有分散做群眾工作,才是決定地制勝敵人援助友軍的唯一無(wú)二的辦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無(wú)結(jié)果之可言的。”他強(qiáng)調(diào):“目前情況與過(guò)去國(guó)內(nèi)戰(zhàn)爭(zhēng)根本不同,不能回想過(guò)去的味道”。他要彭德懷“對(duì)于個(gè)別同志不妥當(dāng)?shù)挠^點(diǎn),給予深刻的解釋,使戰(zhàn)略方針歸于一致”。[45]九月二十五日,他又致電周恩來(lái)和北方局負(fù)責(zé)人劉少奇、楊尚昆,明確提出整個(gè)華北工作“應(yīng)以游擊戰(zhàn)爭(zhēng)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應(yīng)環(huán)繞于游擊戰(zhàn)爭(zhēng)。他指出:“華北正規(guī)戰(zhàn)如失敗,我們不負(fù)責(zé)任。但游擊戰(zhàn)爭(zhēng)如失敗,我們需負(fù)嚴(yán)重的責(zé)任。”[46]
為了堅(jiān)持?jǐn)澈蟮挠螕魬?zhàn)爭(zhēng),毛澤東又提出一個(gè)重要問(wèn)題:必須建立起鞏固的抗日根據(jù)地。如果游擊戰(zhàn)爭(zhēng)只是單純的軍事行動(dòng),而同當(dāng)?shù)厝罕姷慕?jīng)濟(jì)政治要求相脫離,不能取得他們的全力支持;那末,要開(kāi)展廣泛的游擊戰(zhàn)爭(zhēng),并且在戰(zhàn)爭(zhēng)中不斷得到發(fā)展壯大,是不可能做到的。不久,毛澤東在總結(jié)華北游擊戰(zhàn)爭(zhēng)和根據(jù)地的關(guān)系時(shí)指出:“游擊戰(zhàn)爭(zhēng)的根據(jù)地是什么呢?它是游擊戰(zhàn)爭(zhēng)賴以執(zhí)行自己的戰(zhàn)略任務(wù),達(dá)到保存和發(fā)展自己、消滅和驅(qū)逐敵人之目的的戰(zhàn)略基地。沒(méi)有這種戰(zhàn)略基地,一切戰(zhàn)略任務(wù)的執(zhí)行和戰(zhàn)爭(zhēng)目的的實(shí)現(xiàn)就失掉了依托。無(wú)后方作戰(zhàn),本來(lái)是敵后游擊戰(zhàn)爭(zhēng)的特點(diǎn),因?yàn)樗峭瑖?guó)家的總后方脫離的。然而,沒(méi)有根據(jù)地,游擊戰(zhàn)爭(zhēng)是不能夠長(zhǎng)期地生存和發(fā)展的,這種根據(jù)地也就是游擊戰(zhàn)爭(zhēng)的后方。”[47]
毛澤東的反復(fù)闡明和耐心說(shuō)服,使許多干部加深了把游擊戰(zhàn)爭(zhēng)提高到戰(zhàn)略高度和創(chuàng)建敵后抗日根據(jù)地重要性的認(rèn)識(shí)。聶榮臻在回憶錄中寫(xiě)道:“受命之際,讀到毛澤東同志的這些電報(bào),感到很重要,很親切,特別是對(duì)深入敵后,創(chuàng)建抗日根據(jù)地,開(kāi)展游擊戰(zhàn)爭(zhēng),堅(jiān)持長(zhǎng)期抗戰(zhàn)的思想,更為明確了。同時(shí)也覺(jué)得,他的這些電報(bào),對(duì)洛川會(huì)議所確定的戰(zhàn)略方針是堅(jiān)定不移的,唯恐在行動(dòng)中由于思想不統(tǒng)一而出現(xiàn)偏差。”[48]
毛澤東在戰(zhàn)略方針的重大決策一旦作出后,確實(shí)是堅(jiān)定不移的,不會(huì)因某些一時(shí)或局部的因素而輕易改變這種決心。同時(shí),他又密切注意研究變化著的情況,不斷總結(jié)經(jīng)驗(yàn),使作出的決策得到豐富和完善,使它更符合實(shí)際情況。九月二十五日,八路軍一一五師利用有利的時(shí)間和地形條件,集中兵力發(fā)動(dòng)平型關(guān)戰(zhàn)斗,取得了中國(guó)軍隊(duì)自抗戰(zhàn)以來(lái)的首次大捷。戰(zhàn)斗前,毛澤東已同意前方提出的想以一旅集中、相機(jī)給敵以打擊、暫時(shí)不分散的意見(jiàn)[49]。戰(zhàn)斗勝利的喜訊傳到延安后,毛澤東十分高興,立即致電前方,慶賀這一勝利。根據(jù)平型關(guān)戰(zhàn)斗的經(jīng)驗(yàn),毛澤東又進(jìn)一步明確地提出八路軍作戰(zhàn)的“根本方針是爭(zhēng)取群眾,組織群眾的游擊隊(duì)。在這個(gè)總方針下,實(shí)行有條件的集中作戰(zhàn)”。[50]十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同英國(guó)記者貝特蘭談話時(shí)說(shuō):“現(xiàn)在八路軍采用的戰(zhàn)法,我們名之為獨(dú)立自主的游擊戰(zhàn)和運(yùn)動(dòng)戰(zhàn)。”[51]以后,他在《論持久戰(zhàn)》中,總結(jié)十個(gè)月來(lái)華北抗戰(zhàn)的經(jīng)驗(yàn),把八路軍作戰(zhàn)的戰(zhàn)略原則確定為:“基本的是游擊戰(zhàn),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yùn)動(dòng)戰(zhàn)。”[52]這個(gè)提法,同洛川會(huì)議的規(guī)定是前后一貫的,而在具體表述上又更加完備了。
十月初,華北局勢(shì)進(jìn)一步惡化。日軍占領(lǐng)保定,河北正面戰(zhàn)場(chǎng)的抗戰(zhàn)基本結(jié)束。在側(cè)翼遭受嚴(yán)重威脅的情況下,國(guó)民黨軍隊(duì)放棄雁門(mén)關(guān)至平型關(guān)的內(nèi)長(zhǎng)城防線,退守太原的北方門(mén)戶忻口。
為了協(xié)助友軍作戰(zhàn),毛澤東仔細(xì)研究華北戰(zhàn)局后,在十月六日致電周恩來(lái)、朱德、彭德懷等,要他們轉(zhuǎn)告山西軍事當(dāng)局:敵人占領(lǐng)石家莊后,將向西面進(jìn)攻,因此龍泉關(guān)、娘子關(guān)兩點(diǎn)應(yīng)集結(jié)重兵堅(jiān)守,以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勝利;在正面忻口地區(qū)的守備和出擊中,出擊是主要的。并提出:八路軍一一五師、一二〇師主力將擔(dān)任從東、西兩方破壞忻口地區(qū)日軍的側(cè)后縱深地區(qū);一二九師主力或全部將使用于正太鐵路,發(fā)動(dòng)群眾,配合娘子關(guān)守軍作戰(zhàn)。[53]
根據(jù)毛澤東的指示,八路軍各主力師在忻口戰(zhàn)役期間有力地配合了友軍的行動(dòng)。第一二〇師一度收復(fù)雁門(mén)關(guān),伏擊日軍輜重部隊(duì),截?cái)嗔藦拇笸?jīng)雁門(mén)關(guān)到忻口的交通。第一一五師主力奪回平型關(guān),并收復(fù)淶源、定縣等七座縣城,切斷了日軍從張家口經(jīng)平型關(guān)到忻口的交通線。忻口前線日軍只能主要靠空運(yùn)來(lái)維持給養(yǎng)。第一二九師陳錫聯(lián)團(tuán)又在十月十九日乘黑夜突然襲擊陽(yáng)明堡日軍機(jī)場(chǎng),焚毀日機(jī)二十余架。日軍的機(jī)械化部隊(duì)的行動(dòng),依賴后方供給的程度很大。八路軍各部隊(duì)的行動(dòng),使日軍的后方補(bǔ)給線陷于半停頓狀態(tài),對(duì)正面防守忻口的友軍是有力的配合和援助。
在忻口戰(zhàn)役期間,右翼晉軍有十個(gè)團(tuán)撥歸朱德、彭德懷統(tǒng)一指揮。毛澤東就如何對(duì)待這部分友軍,在十月四日致電朱德、彭德懷、任弼時(shí)等,叮囑道:“我們對(duì)于國(guó)民黨交給我們指揮之部隊(duì),應(yīng)采取愛(ài)護(hù)協(xié)助態(tài)度,不使他們擔(dān)任最危險(xiǎn)的任務(wù),不使他們給養(yǎng)物資缺乏。對(duì)作戰(zhàn)應(yīng)使主要打幾個(gè)小勝仗,對(duì)動(dòng)員民眾應(yīng)詳告以政策、方法,對(duì)他們多取商量,表示殷勤愛(ài)護(hù)之意,力戒輕視、忽視、譏笑、漠不關(guān)心及把他們置于危險(xiǎn)地位等錯(cuò)誤態(tài)度。”[54]毛澤東要求他們對(duì)全軍指戰(zhàn)員進(jìn)行教育,徹底執(zhí)行這一方針。在東線,當(dāng)娘子關(guān)告急時(shí),八路軍第一二九師也救出了被日軍包圍的友軍曾萬(wàn)鐘部一千多人。
忻口戰(zhàn)役是抗戰(zhàn)初期華北戰(zhàn)場(chǎng)上作戰(zhàn)規(guī)模最大、戰(zhàn)斗最激烈的一次戰(zhàn)役,將南下的日軍主力擋住了二十一天。這次戰(zhàn)役,也是抗戰(zhàn)初期國(guó)共兩黨領(lǐng)導(dǎo)的軍隊(duì)密切配合作戰(zhàn)最為成功的一次。由于國(guó)共雙方在這次戰(zhàn)役中誠(chéng)意合作,取得了較好的戰(zhàn)果。
十月中旬,日軍主力占領(lǐng)石家莊后沿正太鐵路西進(jìn),包抄忻口的后方。二十八日,娘子關(guān)失守。三十一日,閻錫山下令放棄忻口。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華北戰(zhàn)場(chǎng)的抗日戰(zhàn)爭(zhēng)進(jìn)入一個(gè)新的階段。
正確的領(lǐng)導(dǎo),在于能有預(yù)見(jiàn)。毛澤東自己在中共七大的結(jié)論中生動(dòng)地說(shuō)過(guò):“坐在指揮臺(tái)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見(jiàn),就不能叫領(lǐng)導(dǎo)。坐在指揮臺(tái)上,只看見(jiàn)地平線上已經(jīng)出現(xiàn)的大量的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領(lǐng)導(dǎo)。只有當(dāng)著還沒(méi)有出現(xiàn)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shí)候,當(dāng)桅桿頂剛剛露出的時(shí)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fā)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并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lǐng)導(dǎo)。”[55]抗戰(zhàn)爆發(fā)以來(lái)的短短幾個(gè)月時(shí)間內(nèi),毛澤東顯示了他對(duì)未來(lái)事態(tài)的發(fā)展總能比別人先見(jiàn)一著,對(duì)各種錯(cuò)綜復(fù)雜的新問(wèn)題都能及時(shí)提出明確而切合實(shí)際的對(duì)策,這就表現(xiàn)出他卓越的領(lǐng)導(dǎo)才能。
注釋
[1]《中國(guó)共產(chǎn)黨為日軍進(jìn)攻盧溝橋通電》,《解放》第1卷第10期,解放周刊出版社1937年版。
[2]《蕭勁光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00頁(yè)。
[3]毛澤東致張?jiān)埔蓦姡?937年7月14日。
[4]毛澤東致張?jiān)埔蓦姡?937年7月15日。
[5]洛甫、毛澤東致葉劍英電,1937年7月9日。
[6]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賀龍、林彪、劉伯承、徐向前致葉劍英電,1937年7月14日。
[7]《新中華報(bào)》,1937年7月19日。
[8]《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152頁(yè)。
[9]《先總統(tǒng)蔣公全集》第1冊(cè),臺(tái)灣中國(guó)文化大學(xué)中華學(xué)術(shù)院編印,第1064頁(yè)。
[10]《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44頁(yè)。
[11]《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46、348頁(yè)。
[12]詹姆斯?貝特蘭:《華北前線》,新華出版社1986年7月版,第111頁(yè)。
[13]《聶榮臻回憶錄》(中),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38頁(yè)。
[14]洛甫、毛澤東致周恩來(lái)、博古、林伯渠電,1937年7月28日。
[15]洛甫、毛澤東致周恩來(lái)、博古、林伯渠電,1937年8月1日。
[16]洛甫、毛澤東致朱德、周恩來(lái)轉(zhuǎn)彭德懷、任弼時(shí)電,1937年8月1日。
[17]《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150頁(yè)。
[18]毛澤東致周恩來(lái)電,1937年8月1日。
[19]洛甫、毛澤東致周恩來(lái)、朱德、葉劍英電,1937年8月4日。
[20]洛甫、毛澤東致朱德、周恩來(lái)、博古、林彪、彭德懷、任弼時(shí)電,1937年8月5日。
[21]毛澤東致葉劍英、彭德懷、任弼時(shí)電,1937年8月4日。
[22]毛澤東、洛甫致周恩來(lái)、博古并告葉劍英電,1937年8月1日。
[23]洛甫、毛澤東致彭德懷、任弼時(shí)電,1937年8月8日。
[24]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會(huì)議上的發(fā)言記錄,1937年8月9日。
[25]《一個(gè)美國(guó)女記者在中國(guó)的冒險(xiǎn)(續(xù))》,《瞭望》,1985年第48期。
[26]《周恩來(lái)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195—196頁(yè)。
[27]《蕭勁光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02頁(yè)。
[28]毛澤東在洛川會(huì)議上的發(fā)言記錄,1937年8月24日。
[29]毛澤東在洛川會(huì)議上的報(bào)告,1937年8月22日。
[30]《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51頁(yè)。
[31]毛澤東在洛川會(huì)議上的報(bào)告記錄,1937年8月22日。
[32]《蕭勁光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04頁(yè)。
[33]毛澤東在洛川會(huì)議上的發(fā)言記錄,1937年8月24日。
[34]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召開(kāi)的座談會(huì)上的發(fā)言記錄,1937年8月27日。
[35]《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92頁(yè)。
[36]《任弼時(shí)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37頁(yè)。
[37]洛甫、毛澤東致博古、林伯渠、彭德懷、任弼時(shí)電,1937年8月18日。
[38]洛甫、毛澤東致周恩來(lái)、葉劍英電,1937年8月18日。
[39]毛澤東致張沖轉(zhuǎn)朱德、周恩來(lái)電,1937年8月17日。
[40]毛澤東致朱德、任弼時(shí)電,1937年9月16日。
[41]毛澤東致朱德、彭德懷、任弼時(shí)、林彪、聶榮臻、賀龍、關(guān)向應(yīng)、劉伯承、徐向前電,1937年9月17日。
[42]毛澤東致彭德懷電,1937年9月19日。
[43]《聶榮臻回憶錄》(中),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59頁(yè)。
[44]毛澤東致彭德懷電,1937年9月21日。
[45]毛澤東致彭德懷電,1937年9月21日。
[46]毛澤東致周恩來(lái)、劉少奇、楊尚昆電,1937年9月25日。
[47]《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18頁(yè)。
[48]《聶榮臻回憶錄》(中),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60頁(yè)。
[49]毛澤東致彭德懷電,1937年9月21日。
[50]毛澤東致周恩來(lái)、朱德、彭德懷、任弼時(shí)電,1937年9月29日。
[51]《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78—379、500頁(yè)。
[52]《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78—379、500頁(yè)。
[53]毛澤東致周恩來(lái)、朱德、彭德懷等電,1937年10月6日。
[54]毛澤東致朱德、彭德懷、任弼時(shí)的電報(bào),1937年10月4日。
[55]《毛澤東在七大的報(bào)告和講話集》,中央文獻(xiàn)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00、201頁(y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