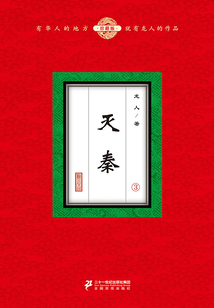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烽火秦疆
二世皇帝三年,流云齋齋主項梁聽居巢人范增之計,立楚懷王之孫為懷王,建都盱臺,項梁自封為武信君。
隨后幾個月,項梁率部與秦將章邯數度交戰,大獲全勝之下,漸生輕敵之心,最終在定陶一役戰死身亡。
消息傳出,懷王驚恐,從盱臺來到彭城,作出了一系列的任命,重用了一批并非流云齋所屬的人員,項羽不喜,此刻他已登上齋主之位,聲勢之大,一時無二,豈容他人與之爭鋒?遂在救援趙國的途中,設計殺了懷王任命的上將軍宋義,懷王無奈,就讓項羽做了上將軍,大權在手,威震楚國,項羽之名,聞傳諸侯。
自樊陰列兵會紅顏之后,由項羽統領的楚國軍隊在諸侯中漸成一枝獨秀,強大無比,他邀集十余路諸侯軍隊救援趙國,并在巨鹿一役大破秦軍,從此天下群雄,唯他馬首是瞻。
與此同時,劉邦率部西進,并與項羽約定,先攻入關中者,為關中王。
于是就在趙高壽辰愈發臨近的時日里,大秦王朝的形勢已是岌岌可危,戰局幾乎到了行將崩潰的邊緣。劉邦率部十萬,強攻武關,此關乃關中門戶,一旦突破,咸陽城將無憑可依,雙方在此激戰數日數夜,始終僵持不下。
而項羽一部屯兵漳河南岸,與章邯統率的四十萬大秦軍隊相峙不下,雙方互有攻防,大有斃敵于一役的決戰態勢,同時也為劉邦西進牽制了敵軍大部主力。
軍情嚴峻,戰局又是如此緊張,但咸陽城中,卻依舊是夜夜笙歌、醉生夢死的景象,胡亥與趙高更是置朝廷安危于不顧,君臣之間鉤心斗角,爾虞我詐,企圖在七月初二的這一天里抖擻精神,一舉壓服對方。
咸陽城中,看似平靜,卻到了一戰定生死的緊要關頭。只要是明眼人,似乎都已經看到了大秦王朝的末日。
山雨欲來風滿樓,這乃此刻咸陽的真實寫照。
七月初二,卦書云:大吉,諸事皆宜。
今天又是一個艷陽高照的日子,碧空萬里,不見白云,但在尋芳樓中,卻有一種異常沉悶的氣氛壓在韓信的心頭,因為他已明白,決定自己命運的時刻到了。
自與紀空手分手之后,他就開始設法通知照月三十六騎離開咸陽。這看上去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但在此時此地,由于相府內的戒備陡然森嚴起來,使得韓信只得借重格里的身份,尋了個借口才召來昌吉一見,等到這件事情辦妥之后,他現在唯一可做的,便唯有等待。
等待是一件折磨人精神的苦差事,不過幸好這種等待并不漫長,日上三竿之后,趙岳山匆匆趕來,一臉肅然,帶他走入了九宮殿中。
九宮殿依然一片陰沉,韓信每次跨入殿中的時候,都覺得自己的心情倍加壓抑,仿佛有趙高的地方,這種壓力就隨時存在著。不過他的鎮定功夫已遠勝從前,單從外表來看,是難以看破他內心情緒的緊張的。
大廳之上擺了兩排暗紅色的桌椅,除了格里、趙岳山、樂白等人之外,還有張盈等一干韓信未曾謀面的謀臣將領居坐其中,這些人面色嚴謹,神情肅穆,都將目光投在了中間那張鋪著錦白虎皮的太師椅上,靜靜地等候著趙高的來臨。
殿中閑雜人等各自退去,韓信在趙岳山的示意下,坐到了格里的身邊,同時感受到了樂白與張盈充滿敵意的目光巡視。
殿中氣氛緊張,卻靜寂異常,整個空間不聞人聲,靜至落針可聞。
半晌之后,一陣輕輕的咳嗽聲從殿后傳來,隨著一個輕輕的腳步聲,趙高終于出現在了眾人的視線之下。他的每一步踏出,輕盈中不失沉穩,循規蹈矩,臉上泛出一絲不經意的笑意,風采照人,目光若電,更有幾分不可一世的王者傲氣。
眾人肅然起立,待得趙高坐定,這才紛紛重新入座。
趙高眼芒掃視眾人一圈,這才微微一笑,有種說不出來的自信與威風震懾全場,緩緩說道:“各位辛苦了。一大早將各位從熱被窩里請來,想必各位也知曉了本相的意思。是的,沒錯,本相邀請各位,的確是為了今天晚上的這場大戲!”說到這里,他頓了一頓,看到眾人亢奮的神情,似乎甚為滿意,大廳中頓時涌出無限戰意和迫人的壓力。
他看了韓信一眼,繼續說道:“除了時信之外,在座的諸位跟隨本相拼戰多年,深知本相的為人作風,一定會在心中問起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何以本相會在如此大好形勢之下,遲遲不對胡亥動手的原因!”
這個原因韓信曾經聽格里說過,但趙高的話出,頓時讓眾人無不大驚:“這只因為胡亥本身便是一個武學高手,無論是明槍明刀,還是暗中行刺,都絕非易事,何況還有登龍圖的下落始終不明,若無十足的把握,本相不敢妄動。”
趙高所言,絕非危言聳聽,由不得眾人不信,倒是張盈淡淡一笑道,“但是趙相既然有心要動,當然是有了十分的把握,還請趙相將計劃一一道出,讓屬下們好著手準備。”
“本相忍耐多年,又豈會急于這一時的功夫?”趙高微笑道:“對于胡亥其人,本相曾經有過深入的研究,最初以為此人胸無大志,只是一個庸碌無為的酒色之徒,但是只要留心觀察,便不難看出他心中暗藏殺機,伺機待動。據本相所知,他暗中培植的勢力絲毫不弱,而且也準備在今天晚上與本相一決雌雄!”頓了一頓,隨即沉聲接著道,“所以今夜一戰,已是決戰,不容半點閃失!”
他的話中殺氣隱現,更有勢在必得的決心。當他的眼芒掃到趙岳山的身上時,趙岳山霍然站起。
“本相交代你辦的事情是否辦妥?”趙高在這個時候問起話來,未免突兀,但是眾人心中一凜,知道趙高必有用意。
趙岳山道:“事已辦妥,凡是在座諸君的家眷親屬共一百二十七人,全被屬下接到了一個安全隱秘的所在,保證萬無一失。”
此言一出,除韓信和張盈外,眾皆失色,他們素知趙高的手段,對這種利用人質進行挾持的行事作風并不驚奇,驚奇的是趙岳山的辦事效率,自己前腳一走,竟然后腳就接走了自己的家眷!可見趙岳山對此事早有布置,趙高此時說來,無非是讓眾人明白自己的處境,有進無退,誓死一拼。
趙高明白自己的話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微微一笑,道:“各位不必驚慌,本相此舉,只是為各位的家眷著想。試想一旦動起手來,以胡亥的為人,難免不會對各位的府上有所騷擾,唯有將各位的家眷集中一處,加以重兵保護,便可去了各位的后顧之憂。”
他笑了笑,接著道:“當然,如果有人敢背叛本相,壞了本相的大計,那么本相說不得也要讓他絕子絕孫,香火一脈從此不續!”
眾人無不倒吸了一口冷氣,心里透涼,仿佛人在千丈懸崖邊緣,已無退路可言。不過,他們都對趙高具有無上的信心,倒也不以為意。
張盈道:“趙相過慮了,這些人都是追隨趙相多年的屬下,忠心可鑒,斷無二心。”眾人紛紛表示附和之意。
韓信看出趙高與張盈一唱一和,旨在提高士氣,畢竟對手是大秦皇帝,權柄在手,趙高不得不有所忌憚。
格里首先站起身來道:“屬下所轄三千暗殺團弟子,已經整裝待命,只等趙相一聲令下,必當誓死效忠!”
趙高微一點頭,樂白等人一一站起,各自表明效忠之心。韓信一一聽來,始知這幫人中,既有負責皇宮守衛的帶兵尉閻樂,亦有負責城防事務的將軍,勢力之大,幾乎涉及咸陽城的每個角落。
趙高揮手讓眾人坐下,這才站將起來,踱步來到他們中間。他那形如竹竿卻隱帶風骨的身形傲立于眾人之上,隱有鶴立雞群的領袖風范,咳嗽一聲,緩緩說道:“此時此刻,能坐到本相九宮殿中的人,都將是本相非常器重的人才,所以今晚一戰是否成功,決定于各位是否能夠堅定不移地執行本相發出的每一道指令,你們的忠心毋庸置疑,關鍵還要看你們臨危處變的能力,本相相信你們一定能夠完成本相交給你們的每一個使命!”
他雖然細聲慢氣,但極有條理,首先將相府外圍的一切防務一一交代,閻樂及一干將領紛紛領命而去。韓信聽得如此周密的布置,不僅為趙高所擁有的壓倒性優勢而心驚,同時更為趙高縝密的心思而感到可怕。當他的目光每一次不期然地與趙高那犀利的眼芒相對時,他都有一種如坐針氈的感覺。
隨著時間一點一點地流逝,殿堂中除了趙高之外,就只剩下了張盈、樂白、格里、趙岳山以及韓信五人,人數雖然減少,但氣氛卻愈發緊張,因為每一個人都知道,趙高接下來的安排才是整個計劃的核心,事情的成敗與否,關鍵還在他們身上。
果不其然,趙高沉吟半晌,這才說道:“你們都是我最為器重的心腹,所謂養兵千日,用在一時,現在就是用到你們的時候了。”他不再自稱“本相”,而改用“我”字,言下自有籠絡之意,眾人無不抬頭仰視,凝神屏氣,生怕漏過趙高所言的一字一句。
“樂白的親衛營,著重于整個相府外的警戒,在今晚酉時之前,任何人許進不許出。酉時之后,全面戒嚴,不許有任何人出入府內,敢有違者,殺無赦!”趙高拍了拍樂白的肩頭,下手雖輕,卻帶出了一種無可匹御的殺氣,令人根本不敢存有抗拒之心。
“是!”樂白領命而去。
趙高待樂白的身影消失在殿外之后,這才轉頭望向格里道:“你的任務,是帶領你的戰士進駐相府,或明或暗,必須牢牢控制住府內的整個局勢。據我所知,在參加龍虎會的百名戰者之中,其中不乏有胡亥派出的高手混跡藏身,你著重于他們身上,一旦信號傳出,立時實施格殺,不得有誤!”
格里接過趙高遞出的一張名單,瀏覽一遍:“何為信號?”
趙高毫不猶豫地道:“擲杯為號!”
格里應聲而起。
趙高微微一笑,道:“雖然府內的一切局勢有利于我,但真正兇險之處,卻在登高廳。”
韓信一直沉默不語,直到這時,他才低聲發問道:“登高廳又在何處?”
趙高看了他一眼,道:“登高廳當然也在相府之內,不過在今天晚上,它卻是我專門宴請胡亥的所在。為了不引起胡亥的疑心,今夜出入登高廳的人,不僅非富即貴,而且不能私帶兵器入內。”
韓信心中暗驚:“紀少果然聰明,已經算到了趙高的心思。這么說來,趙高果真是想利用我來行刺胡亥。”他不動聲色,靜聽趙高下文,孰料趙高話鋒一轉,面對趙岳山道:“至于登高廳的布置,相信岳山已安排好了?”
“是,一切盡按趙相吩咐,萬事俱備。”趙岳山恭聲道。
“很好!”趙高滿意地點了點頭,與張盈相視一笑,道,“還有一件事情,我想了很久,總是不太踏實,只有有勞你去替我打理一下。”
他稱張盈并不直呼其名,而是只用一個“你”字,可見二人的關系不同尋常,韓信看在眼中,微微一怔,卻見張盈俏臉微紅,目光盯視趙高,似乎有一種說不出的情意。
“趙高與張盈難道是一對情人?如果不是,兩人的神情何以會如此曖昧?如若是,以趙高的性情,他又怎容得下張盈風流淫蕩的行事作風?”韓信不由大感惑然。
“趙相請講。”張盈微微低頭,避過趙高的眼芒道。
“我想請你替我監視一下后院廚房的那一幫人,神農廚藝,雖然傳世十代,家世清白,但是他們終究是外人。俗話語,小心能駛萬年船,我可不想在陰溝里面翻船。”趙高此言一出,嚇得韓信頓冒冷汗,不由得為紀空手擔起心來。
張盈領命道:“我一定照辦,不過為了預防萬一,我可以在酒菜上席之前,命其自嘗一筷,以防他們在酒菜中做手腳。”
趙高笑道:“你果然心細如發,好!就照此辦理,只要每一件事情都做到毫無漏洞,明年的今天,必定是胡亥的祭日!”
趙岳山與張盈看了韓信一眼,這才在趙高的示意下匆匆離去。偌大一個殿堂中,轉眼間便只剩下趙高與韓信二人相對,半晌無聲,一時靜寂。
在趙高的目光逼視下,韓信心中忐忑,整個人極不自然,好半天才聽趙高相問一句:“你在想什么?”
韓信微驚,趕忙答道:“屬下所想,只怕有污趙相之耳,是以不敢回答。”
趙高“哦”了一聲,頗感興趣地道:“但說無妨,我不怪罪于你便是。”
韓信這才答道:“屬下心想,不知趙相與張軍師是什么關系,何以你們二人的神情讓屬下一直看不分明?”
“哈哈哈……”趙高略怔一怔,驀然爆發出一陣大笑,半晌之后才戛然而止,注視著韓信道,“我一生從不輕易信人,對你亦不例外。就在這之前,我還一直在對是否對你加以重用表示懷疑,現在我卻確信,你應該是一個可以讓我信任的人。”
韓信似乎糊涂了,問道:“為什么?難道我心中的想法就能改變你對我的看法嗎?”
“是的。你心中所想正是你真實心境的寫照,因為但凡心懷叵測之徒,到了這種緊要關頭,他只會想到如何隱藏自己,如何伺機一擊,而絕對不會想到與他無關的事情。你能看出我與張盈之間的關系,這不僅證明了你觀察入微,同時也證明了你對我并無惡意。”趙高緩緩而道,眼中露出欣賞之意。當世之中,像韓信這般杰出的年輕后輩畢竟不多,趙高雖然閱人無數,但對韓信卻有一股發自內心的扶植之意。
韓信心中一驚,不由為趙高的推理感到欽服。事實上若非紀空手事先提醒,他或許在心情緊張之下,極有露出馬腳的可能。
此刻,韓信等著趙高說出他與張盈之間的關系,平心而論,他的確對此抱有濃厚的興趣,興之所致,并非全是作偽,可是趙高并沒有接著這個話題聊下去,而是輕品一口香茗道:“你的流星劍式已經具有一定的火候,再輔之以雄渾的內力,當世之中,確實算得上年輕一輩的頂尖人物。但是擁有這些尚且不足以讓你名揚天下,一個真正的高手,他還需要具備一往無前的勇氣與對勝利的渴望。現在正好有這樣一個成名的機會,不知你是否勇于面對?”
他的話平平無奇,卻給人精神的振奮,不知不覺地使聽者有一種熱血沸騰的亢奮。韓信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壓下自己激動的情緒,沉聲道:“我此次咸陽之行,不求財富,只求功名,能有成名之機,豈容錯失?還請趙相吩咐!”
“好!我就喜歡年輕人的這股沖勁!”趙高眼中頓時閃射出異樣的光彩,接著道,“我要你在今晚的登高廳上,刺殺胡亥!”
韓信臉顯震驚之色,他倒不是為趙高的話而震驚,而是對紀空手的判斷能力感到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害怕。如果讓紀空手得知他此時心中的真正想法,不知紀空手臉上會是一種什么樣的表情?
“你怕了?”趙高的眼芒如電般射入到韓信的眼眸中,似乎想從中看穿一點不明的玄機。
“不!”韓信斷然答道,“我早就在等著這樣的機會。”
趙高滿意地點了點頭,道:“你能如此想,說明你的確是一個難得一見的人才,也證明了我的識人目光并沒有錯。在我的門下,武功高過你的并非沒有,但真正能夠完成這次刺殺任務者,恐怕你是唯一的一個!”
韓信很想知道這其中的原因,是以詢問道:“為什么?對于趙相來說,我畢竟是一個外人。”
趙高搖頭道:“以前是,但從這一刻起,你已是我的親信。所謂用人不疑,我相信你對我的忠心。”頓了一頓,隨即接著道,“世人皆知,胡亥登上皇位,其功在我。但是正因如此,使我功高震主,所以胡亥一登上皇位,他最想除去的人,當然就是我。只是他一直礙于我的實力,遲遲不敢動手,但卻暗中培植了不少力量,就等待機會給我致命的一擊。”
韓信道:“我聽人說,胡亥喜好酒色,從不節制,是一個庸碌無為的昏君,想不到他會有如此心計。”
趙高道:“這才是他聰明的地方,若非如此,我又豈能容他活到今日?不過所幸我終于發現了他的陰謀,今夜一戰,猶是未晚。我要讓他知道,我趙高既然可以立他,也可以廢他,大秦的天下始終只能掌握在我趙高的手上!”
說到這里,他的臉上油然生出一股傲然之氣,不失入世閣豪閥的王者風范與一代權相的氣勢。縱是韓信如此大膽之人,亦在這股威勢之下黯然低頭,不敢仰視。
良久之后,趙高方才又道:“不過我依然失算了一著,就是胡亥不僅從始皇身上學到了龍御斬,而且功力之高,絕非是一般高手所能匹敵。只要他有劍在手,殺他并非易事。”
韓信問道:“今夜登高廳上,不是不可佩劍嗎?”他一問之下,方知所問極為幼稚,不由臉上微紅。
趙高看出了他極為不好意思,佯作不知道:“但是他是王者,豈有解劍之理?所以我千思萬慮,終于想到了利用龍虎會來對付他!”
韓信已聽過紀空手點評趙高陰謀,聽到這里,已是全然明白,他有意掩飾自己適才的無知之談,故作恍然大悟:“趙相莫非是想讓我在龍虎會上一舉奪魁,然后借機召見,給我刺殺胡亥之機?”
趙高微一點頭,道:“是的,唯有如此,你才能帶劍進入登高廳,而且不會讓胡亥有半點疑心。所以我說,只有你才能助我完成這次刺殺行動!”
韓信這才明白趙高器重自己的原因:一來是因為自己的劍法不錯,以有心算無心,或許可以敵過胡亥的龍御斬;二來自己面相極生,胡亥不會對自己過分注意,這樣無形中就增加了成功的機率。想通了這些事情之后,他這才知道趙高的心計之深,固然讓人害怕,但紀空手料事如神,卻又讓人佩服得五體投地,若非他深信冥冥之中必有天理,或許會改變自己的主意。
韓信收攝心神,很快進入了自己扮演的殺手角色,問道:“可是龍虎會上高手如云,縱然我能打敗所有敵手,想必亦是力竭,又怎能與胡亥一拼?”
趙高微微一笑,道:“這一點你不用擔心,我對此事早有安排。我可以保證你出現在登高廳的時候完全擁有你應有的戰斗力,而且還有同樣的幾個攻擊手為你策應。”
韓信笑道:“如果真是這樣,那么胡亥一定是必死無疑了,我對自己的劍法通常都很有信心!”
趙高也笑了,而且是得意地一笑:“是嗎?那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張盈與趙岳山并肩出了九宮殿,稍作安排一下,便帶領一干手下往后院而來。
膳房不大,卻隱于花園一側的竹林之中,一點不顯粗俗之氣,唯有隱隱傳來的刀剁砧板之聲與隨之而來的撲鼻香氣,構成了廚房獨有的氛圍。
在趙岳山的布置下,膳房的安全戒備愈發森嚴,除了少有的幾個人可以自由出入外,其他的人各就各位,一片忙碌。
負責膳房守衛的是帶刀侍衛莫生,這是一個盡忠職守的典型軍人,憑著戰功晉升官位,不善言辭,卻是個有本事的人物,趙岳山派他負責此地,自然是看重他的實力。是以,他此刻見到趙岳山與張盈之后,恭聲行禮,只說了一句話:“莫生給兩位請安。”
趙岳山“嗯”了一聲,并不還禮,而是擺手道:“免了吧,你忙你的,我帶張軍師四處走走。”
他踏入膳房之內,第一眼看到的便是一張大大的躺椅,一張茶幾,一杯香茗,然后才看到神農那張清癯的臉容。他總有一種錯覺,認為神農既然是天下第一名廚,理所當然也是天下第一胖子才對,可是當他見過神農之后,才知道這不過是自己的謬論而已。
“神農先生,我可又來看你來了。”趙岳山素知名人都有自我清高的毛病,是以臉上帶笑,舉止有禮。
“趙總管不必客氣,你一日總要來個數次,又何必在乎多來這一次呢?你能對趙相如此忠心,難怪趙相會對你如此看重呢!”神農起身相迎,見到張盈時,眼中陡然放光,裝出一副好色之徒的模樣。
張盈認識的男人無數,又豈會在乎這種目光,咯咯一笑,道:“說得好,趙相看重的人,武功本事尚在其次,關鍵還要看這個人是否忠心。說到忠心二字,放眼相府之內,唯有總管當居首席。”
趙岳山剛想謙遜幾句,忽然醒悟張盈乃是借此諷刺自己,不由狠狠瞪了她一眼,轉而問道:“神農先生的廚藝天下聞名,我也不想再加贊美了。只是今夜宴席之上,食客如云,高手無數,若是先生稍有大意,只怕難逃眾人的非議。”
神農先生傲然道:“廚藝之道,乃我九世家傳,平生不敢自吹,唯有于此道敢夸下海口,這一點但請總管放心。”
趙岳山拍掌笑道:“大師就是大師,所說之話句句與眾不同。”他巡視了一眼膳房內的物什,接著道,“一應所需是否都已齊備?從此刻起,相府之內已經封關戒嚴,不許任何人出入相府,你若欠缺一些材料,說給我聽,待我替你跑上一趟吧。”
神農先生道:“不敢勞煩總管,諸事俱備,只等開席,我已經早就安排妥當了。”
張盈任由神農先生與趙岳山二人閑聊,一雙俏目卻在四處打量,打量半天,始終不見異樣,稍覺放下心來。當她來到一排鍋灶之前,看著十幾道背影背對自己忙個不停時,突然心神一跳,覺得有一股力量吸引著她,循其望去,發現那是一道背影,感覺有點熟悉,可是一時之間,卻又想不起來在哪里見過。
她不由留心起來,對她來說,只要是曾經在其記憶中留下印象的東西,一般都不會輕易忘卻。
這是一道厚實的背影,在運動的韻律中充滿著動感,透過薄薄的衣衫,仿佛可以看到里面蘊含著青春活力的肌肉。不知為什么,當張盈悄然走近時,她的心中竟然泛起情動的漣漪。
這幾乎不可能發生的事情,竟然在她的身上驀然出現,這簡直讓她有些亢奮不已。自從她那段刻骨銘心的戀情最終遙遙無期后,她便對任何男人都失去了應有的興趣,甚至不能激起她對情欲的正常需求。雖然她日夜有男人相伴而眠,但她從來不認為這是情緣,更不用說付出感情了,她只將這種男人當作是一種戲弄的對象,玩弄別人,同時也玩弄自己,在醉生夢死中尋求心靈的慰藉。
但在這一刻,她面對這道背影時,竟然產生出一種對異性的渴求,甚至感到了自己身體正悄悄地發生異樣的改變。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收攝心神,終于在與那道背影相距五步時站定。
“我們一定是在哪里見過?”張盈冷然道,其語氣冷得有些做作。
這道背影依然不停地翻動著炒勺,聚精會神地對付著鍋中的菜肴,仿佛沒有聽到張盈的問話,倒是神農先生與趙岳山聞聲走了過來。
“莫非張軍師認得劣徒?”神農心中雖驚,但臉上卻不動聲色。
“也許。”張盈一雙美目凝視著這道背影,等到這道背影轉過身來,她微微失望地“哦”了一聲,卻對此人產生了更濃烈的興趣。
她可以肯定自己從來沒有見過這個男人,如果見過,她就絕對不會放過!她從那張略帶油煙的臉上看到了一種滿不在乎的氣質,似笑非笑,眼帶憂郁,雖然算不上俊美,卻有一種撩人心扉的男人魅力。隱約之中,她似乎又看到了昔日的戀人,目光在瞬間變得如霧般撲朔迷離。
是的,這人當然就是紀空手,也只有像紀空手這樣被補天石異力改造過的男人,才能夠吸引住張盈這等欲海嬌娃的目光。
“我想這位夫人一定是認錯人了。”紀空手微微一笑,他當然知道來者是張盈,但他卻不知張盈對他的熟悉感是來自其體內的補天石異力。當日他在船上用補天石異力將張盈的天顏術破去,其補天石異力尚滯留于張盈體內,故此兩氣相吸,使張盈對他有種特別的感覺。他知道自己的易容術很難被人識破,此刻與其在她的面前刻意掩飾,倒不如坦然相對,畢竟張盈閱人目力十分驚人,如果作偽,定難逃過她的視線。
張盈的俏臉一紅,趙岳山故意怒斥道:“小子無禮,張軍師雖然年紀不小,卻仍是未嫁之身,你怎么可以‘夫人’相稱?”
張盈眼中泛出一絲恨意,一閃即沒,冷哼一聲:“不知者無罪,我可沒有計較,又何必勞煩趙總管操心?喂!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她這后面的一句話顯然是問紀空手,倒把趙岳山晾到了一邊。
紀空手不慌不忙地道:“小人姓丁,名紀,師從神農先生已有數年時間了。”他以丁衡之姓為姓,以自己之姓為名,表示不忘丁衡提攜之意。
張盈嘴上念叨了一遍,突然發問:“你剛才炒的是一道什么菜?”
“油爆花生。”紀空手道。
“怎么壽宴之上會有這種菜?”張盈微一皺眉道。
“此菜雖然平常,亦是市井常見之物,但要將它做成一道上席菜肴,又豈是容易之事?油爆花生,講究的是色澤金黃,香酥可口,清脆生香,口感適中。小小的一道菜肴,卻有十九道工序,若非廚道中人,又怎知內中艱辛?”紀空手娓娓道來,絲毫不顯呆滯,說話舉止之中,隱現大廚風范,便是神農聽了,亦是連連點頭,暗自嘆服紀空手的記憶力與悟性。
張盈依然不動聲色地道:“油爆花生會有十九道工序,何不說來聽聽?”她絲毫不覺厭煩,一一相詢。
這是她一貫的行事作風。她總認為,一個奸細,往往都注意到一些大的枝節,卻會忽略一些微不可察的細節,唯有從細節上入手,才能發現奸細的破綻。但若你從一些大事問起,這些問題幾經奸細琢磨,已是天衣無縫,更能自圓其說,你是很難從中找出破綻的。
紀空手微微一笑,胸有成竹地道:“第一道工序,在于選料。雖是一碟花生米,卻必須是產自關中沙地的紅皮花生,個大心圓,顆顆均勻,這樣方能入菜;第二道工序,將選料出來的花生在深寒井水中浸泡一個時辰,然后濾水備用;第三道工序,則是選油……”他一一說來,談到油溫、控火、下鍋時機等等事宜,一氣呵成,宛如行云流水。說到最后時,他才頓了頓,道:“翻炒時需用滾云勺,這樣才能讓花生受熱均勻,炒至第三十七勺時,起鍋離火,濾油裝盤,不可有一點停頓時間,否則花生必然焦黑。但若提前起鍋,花生便帶一絲生味,算不上是炒貨上品。”
張盈微微點頭,似乎非常滿意紀空手的回答,神農見狀,一顆心頓時放了下來。
但是張盈正要轉身之際,陡然眼芒生寒,厲聲問道:“你剛才一口氣說了三百六十九個字,卻氣息悠長,不見呆滯,可見內功不弱,以你這樣的身手居然安心來做廚子,若無不良居心,又作何解釋?”
此話一出,趙岳山與神農俱都失色,張盈身后的一幫隨從更是拔刀逼上,形勢危急,刻不容緩,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張軍師能看出小人的身手,眼力果然高明。不過神農門下,要想找出一個不會武功的人,實在太難,不信請問神農先生。”紀空手鎮定自若,不慌不忙地答道。
神農先生趕忙道:“這是我家傳的內功心法,凡我門下,入門必修,只是為了發揚廚藝,絕無與人爭勝之心。”
張盈奇怪道:“內功心法難道還與廚藝有關?”
神農先生道:“廚藝一道,講究繁多,若無內力,單是掌鍋顛勺便極難掌握,又怎能談得上廚藝高明呢?此事還請張軍師與趙總管明鑒!”
張盈不再說話,所謂隔行如隔山,她對此道一無所知,也就不好亂加妄斷,而且她對紀空手確有一種莫名的好感,便抱著“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態度放過了他。
等到張盈與趙岳山離開膳房,紀空手這才松了一口大氣,叫了聲:“好險!”發現自己的內衣俱已濕透。
“紀少這招意形留神真乃易容的最高境界,如此險中求勝,今夜盜取登龍圖,我們必定成功!”神農笑了笑,拍了拍紀空手的肩頭道。
“那我們可得好生計劃一下才是,今夜的相府,無異于龍潭虎穴,只要我們稍有不慎,恐怕就會全軍覆滅!”紀空手目光一閃,顯然意識到了任務的艱巨。
“你不必擔心,今夜的行動我已經計劃好了,趙岳山剛才通知了我,今夜凡是上到登高廳的每一道菜肴,必須要試菜之后方可上席,我們完全可以利用這個機會,摸清廳中的形勢,再伺機下手。只要刺殺得了趙高,登龍圖便不難到手。”神農看了看四周的動靜,悄然說道。他的臉上沉穩無比,似乎對事態的發展已經胸有成竹。
紀空手臉上不見動靜,心中卻暗吃一驚,與神農敷衍幾句,見到守衛前來,各自散開。
時間在等待中一點一點地過去,隨著夕陽西下,漸漸消失,暗沉的夜色終于降臨。今夜雖無星月,但在相府內已是燈火通明,亮如白晝,處處笙歌響起,車水馬龍,熱鬧一片,以一場壽宴為名的大決戰終于徐徐拉開了帷幕。
七月初二,夜,咸陽城中趙高相府。
將近酉時,相府之外的廣場上,車馬列隊而立,足有千駕之多,人聲鼎沸,凡是咸陽城中有頭有臉的人物全都到來,更有些人知道二世皇帝胡亥要親來道賀,都想目睹帝君龍顏,無不趨之而來,整個氣氛顯得異常熱鬧。
相府內外點起了萬盞大紅燈籠,燈籠之上寫有“壽”字,愈發突出了喜慶的氛圍。過道園林都有千姿百態的各色燈飾,更加增添了不少輝煌的氣派。
但是熱鬧之余,卻不失有度,在樂白與格里的統領下,暗殺團武士與親衛營的戰士俱已到位,形成了非常嚴密的戒備態勢。膽小之人見之,已是戰戰兢兢,有心人見之,不免在心中有所揣度,但更多的人卻不以為意,認為相府守衛,自當如此,一切盡在情理之中。
由大門而入,賓客雖然魚貫不絕,但一切接待均是井井有條,絲毫不顯亂跡。來賓各按自己的身份,由專人引領,分別進入了一主二輔的三座大廳。
當中一廳面積最小,但設置最為豪華,與兩邊輔廳相距數十丈遠,卻高高在上,只可由上俯瞰,輔廳中的人卻根本看不到主廳動靜,廳上有匾,匾名“登高廳”。既有登高而望之意,又可作“登高一呼,四方響應”之解,由此可看出趙高的狼子野心。
登高廳所設宴席只有寥寥數桌,雖顯空曠,但桌與桌之間的間距有度,顯示著每一桌賓客身份地位的差別。若非王侯將相一類的人物,只怕是沒有資格居坐其中的。
沿登高廳向兩邊而建的,正是兩座輔廳,輔廳面積極大,各設五百席,可容下數千賓客。三廳之間,有一塊偌大的空場,搭置木臺,成為了龍虎會的演武場。三方賓客俱可在喝酒作樂之余,欣賞到高手之間演繹而出的龍爭虎斗。
韓信在臺下的一方席上入坐,手抱一枝梅,閉目養神,絲毫不為外界動靜所驚擾。他并不擔心自己是否能奪得魁首,登上登高廳。因為趙高既然有言在先,想必一切都已安排妥當,他倒是一心想看看紀空手何以能在大庭廣眾之下,從胡亥的身上盜走登龍圖。
他雖然對紀空手一向很有信心,但看到眼前這種場面,不由得為紀空手擔起心來,畢竟這是在相府府內,稍有閃失,的確是無路可逃,無處遁跡。
格里瞅了個空暇時間,悄悄來到他的身邊,道:“你不必緊張,此事雖然事關重大,但若趙相沒有把握,他也絕對不會貿然動手。”
他與韓信極是投緣,料其新手上陣,難免緊張,是以特來囑咐幾句,韓信知他心意,微微一笑:“多謝將軍關心,時某心中有數。”
格里見他神態如常,頓時放下心來,拍拍他的肩道:“若想成名,成敗在此一舉,不動則已,一動必要義無反顧,永不言退。”
“是。”韓信心中一凜,肅然道,這是格里殺人的經驗之談,的確是刺殺精華,韓信怎敢不聽?
格里巡視了一下四周的人群,其中不乏有躍躍欲試的戰士,陡然間看到東面角落處的一條人影,心中一驚,“咦”了一聲道:“怎么此君也到了相府?”
韓信循聲望去,只見那人一身玄衣打扮,身材健碩有力,懷抱一桿長槍,在夜色映襯下仿若一個幽靈般挺立于那角落中。雖然看不清其面目,但觀其輪廓,已有一股襲人的寒意油然而生,令人不寒而栗。
韓信剛要發問,倏覺那人抬頭望來,一道如電的寒芒透過虛空,竟與自己的目光在空中相對,雖是一觸即分,但是韓信只覺胸口一悶,仿佛感到有一股大力擊中胸膛一般。
“此人姓扶,名滄海,乃南海長槍世家的傳人。南海長槍世家一向少有人在江湖走動,他今日前來,已經是與長槍世家往日的行事作風大大不同。”格里似乎對江湖逸聞如數家珍,娓娓道來。
“他莫非亦是胡亥的手下?”韓信悄聲問道。
“不可能,胡亥安排的高手已全在我們掌握之中,他們也絕對不會來爭這份名頭,倒是這扶滄海的槍法不弱,若他有心奪魁,只怕對你不利。”格里不由擔起心來。
“若是如此,倒也再好不過。”韓信豪氣頓生,大有與扶滄海一決高低之意。
格里搖頭道:“趙相對你早有安排,豈能再容節外生枝?何況今日相府之內戒備如此森嚴,此人竟能避過眾多耳目,闖入府內,單憑這份膽色與勇氣,已足以讓人不可妄生小視之心!”
韓信正待說話,忽見扶滄海從人群中走出,大步行來,他的步伐堅定有力,眼芒透出,直逼韓信面門。隨著他的人每向前移動一分,帶出的壓力便隨之增強一分,韓信昂首而視,不動聲色,心中卻感到一座山岳緩緩移來,給人以咄咄逼人的壓服之勢。
扶滄海走到與韓信相距三尺處方才站定,臉如嚴霜,眼中神光若電,半晌才道:“我巡視全場武者,今夜的龍虎會上能與我一戰者,唯君而已。”
他言下并無太大的惡意,反倒對韓信多了幾分推崇的意思。韓信一怔之下,微微笑道:“不敢,扶兄英氣勃發,未出手時已氣勢在先,這等威勢,豈是時信所能比肩的?”
“時信?長街擊殺樂五六的時信?”扶滄海眼芒一閃,追問一句。
“僥幸得手,怎敢言勝?樂五六死在我的手下,全是輕敵所致,若非如此,只怕死的人就會是我了。”韓信淡然笑道。
扶滄海沉吟半晌方道:“樂五六的身手我早有所耳聞,你過謙了。如果我目力不差,縱是樂五六全力以赴,也未必是你的百招之敵。”他突然間傲然笑道,“幸會,幸會,有強手親臨,總算讓扶某不虛此行。”
他說完此話,又悄然退回自己剛才所站的那個角落,來去突兀,瀟灑至極,頓讓韓信嘆服不已。特別是他面對格里這等高手時猶似不見,這份傲氣,實是狂得可以。
“看來你與扶滄海必有一戰,他指名點你,只怕你難以回避。”格里臉上露出一絲憂郁之色,輕嘆一聲道。
“難得遇上如此英雄人物,我亦不想錯失這個機會。”韓信眼眸中頓閃異彩,戰意勃發下,整個人多出了一股必勝的氣勢。
格里欲勸又止,只得匆匆離去。雖說韓信與扶滄海之戰勝負未料,鹿死誰手猶未可知,但兩人若是交手,終需百招之后方能罷休,到時即使韓信勝了,也必定已是強弩之末,又怎能再擔負起刺殺胡亥的使命?
這種結局絕對不是趙高愿意看到的,所以格里無論如何,都不能讓扶滄海與韓信交手。而要扶滄海接受這個建議,通常的辦法,只有格里親自與扶滄海一戰,迫他離開相府。
格里的行事作風就像是一陣風,只要主意拿定,立時實行。于是一炷香的時間不到,他已約上了扶滄海,悄然離開人群,來到了花園之中。
扶滄海人到花園,便已看到了花園之中人影幢幢,潛藏了不少高手。他皺了皺眉,卻絲毫不懼,緩緩地將長槍取在手中。
格里看出了扶滄海眼中的疑慮,輕笑一聲道:“我絕沒有以多欺少的意思,之所以約你一戰,只是不想讓你與時信在今夜交手。”隨即打了個手勢,竟然指揮屬下全部退出了花園。殊不知,這個決定帶給他的將是滅頂之災。
“為什么?”扶滄海沒有料到格里會是如此自信,但他更想知道,格里為何要攔阻他與韓信在龍虎會上的爭魁之戰。
“如果你能勝得了我的霸王鈸,過了今夜,你就自然會知道原因。但是現在,我卻無可奉告。”格里笑了笑,南海長槍世家雖然名揚天下,但他卻絲毫不懼,他完全有擊敗扶滄海的自信,否則也不會貿然挑戰了。
“霸王鈸,這是格里的兵器,莫非你就是入世閣中暗殺團統領格里?”扶滄海倒吸了一口冷氣,心中暗驚,他絕對沒有料到站在時信身邊的將軍竟是入世閣的三大高手之一。
“你現在知道,并不算遲,只要你答應離開相府,我留給你的還是一條生路。”格里很滿意扶滄海的反應,更不愿貿然與南海長槍世家為敵,所以提出了一個折中的方案。
“不,你錯了,你可知道,我來到相府是何目的嗎?”扶滄海臉上突然露出了一絲不易察覺的笑意。
格里道:“來參加龍虎會的人,都想奪魁,借此爭得一份功名,你難道不是嗎?”
“當然不是,南海長槍世家屹立江湖數百年,你可曾聽到過有一人身居官位?”扶滄海淡淡一笑,臉上仿佛多出了對功名利祿的厭倦。
“這倒不曾聽過。”格里想了想道。
扶滄海道:“我來相府,一是欲會會天下英雄,二來則是為了幫朋友的一個忙。英雄可以不會,但忙卻不能不幫,所以我不能走,咱們唯有一戰!”
格里眼中閃過一抹詫異之色,道:“你的朋友是誰?”
“你很快就會知道。”扶滄海冷冷一笑,陡然間長槍一振,大聲喝道,“就讓我的長槍會一會你的霸王鈸吧!”
他雙腿錯步,長槍已然破空,槍鋒閃耀虛空,發出嗡嗡之音,一股懾人的殺氣頓時彌漫空中。
他初時給格里的印象,雖然狂傲,卻不失有禮,聽到自己的名號,似有怯意,但這一刻卻像變成了另外的一個人般,非常沉著冷靜,眼芒射處,無一不是隨時可以發動攻擊的突破口,根本沒有半點輕敵或是怯陣的表現。
他的雙手握住槍身,穩定如山,卻意態輕閑,隨意擺出的架勢,如山梁般橫亙,的確具有震撼人心的高手風范。
格里心中暗自喝彩一聲,不敢大意,將手伸向背后,再伸出時,只見一只大如鐵扇的鋼鈸躍然空中,鈸邊寒芒盡現,竟是一件可攻可守的殺人利器。
他的眼神變得如刀鋒般銳利,洞察著對方長槍逼迫而出的氣勢走向,而自己的霸王鈸卻一點一點地伸向虛空……
花園之中靜若無聲,清風徐來,到了他們相距的空間,仿佛撞上了一面墻,再也滲透不進。如此強橫的氣勢,使得雙方都不敢有半點疏忽,更不敢貿然出手。
幽暗的花香覆蓋了整個園林,淡香襲人,沁人心脾,但是無論是格里,還是扶滄海,似乎都沒有聞到這如處子體香般的幽香,撲鼻而入的,是那股沉沉的肅殺氣息。
這是無聲的對峙,在如此緊張的氣氛中仿佛透出了一個信息,那就是不動則已,一動必是石破天驚!
格里感受著對方迫來的如潮壓力,不得不為自己的一時輕敵暗自叫苦。他根本沒有想到扶滄海的內力會如此雄渾,一時大意,讓對方在氣勢上壓了自己一頭,不過他畢竟身經百戰,臨場經驗豐富,而且實力不弱,表面上絲毫看不出落于下風的跡象,卻在暗中催逼勁力,企圖在對峙中扳回劣勢。
他的本意是想速戰速決,心系龍虎會和韓信,使得他無心戀戰。按他的實力,假若與扶滄海同時拔出兵器,在氣勢上不分軒輊,他就處于主動,但是到了此刻,他只能氣度沉凝,嚴陣以待,根本沒有出手的機會。
他明白自己此刻的處境,不由心中一急:“倘若扶滄海一直不動,我豈非便要陪他站上一夜?”
但是扶滄海絕對沒有再等待下去的意思,他忽地身子向前微俯,如獵豹般陡然沖前。
人動,槍卻未動,就仿佛長槍懸凝空中一般,等到他踏出兩步時,勁力陡然從掌中爆發,長槍甫動,如惡龍般飆射而出。
如此怪異的出槍手段,實乃格里生平僅見,但他卻知道這樣的出槍,借力強大的慣性可以使速度增加逾倍,刻不容緩之際,他唯有架鈸格擋。
“當……”的一聲,槍鈸一觸即分,發出一聲輕響,但兩人同時感到手臂一麻,不由得重新估量對方的實力。
扶滄海回槍退步,槍勢更烈,手腕一振之下,長槍化作漫天槍雨,如暴風驟雨般卷向格里的身體。
格里雖處守勢,卻絲毫不亂心神,指撥霸王鈸,竟如風車般全力旋轉,一時“砰砰……”之聲不絕于耳,頓時化去扶滄海的如潮攻勢。
“高手就是高手,臨危不亂,不過你再接我這十七式滄海槍法試試!”扶滄海戰意勃發,大喝一聲,人如狂飆直進。
他占得先機,欲一鼓作氣挫敗對方,何況面對的又是格里這等高手,一旦讓對方轉守為攻,自己便難以扳回勝勢,是以他一招出手,招招不讓,槍勢如大江之水,連綿不絕,盡顯長槍攻掠的威力。
格里一見之下,心中再也不存僥幸,心知高手交戰,只要一旦失勢,唯有在嚴防之下等待對方出現破綻,倘若貿然攻擊,往往是畫虎不成反類犬,徒增敗筆。
于是他全力退防,霸王鈸飛旋如風,遮擋得滴水不漏,鈸動風生,獵獵直響,卷起花草殘枝,愈滾愈大,猶如滾雪球一般,任憑對方的長槍舞動穿越,竟然不散。
扶滄海看得心驚,久攻不下,不由怒喝:“第十七式,滄海怒潮!”話音一落,長槍速度陡然放緩,一點一點地透入虛空,勁力四溢,潮聲隱起,猶如海潮怒嘯而來。
格里心中一凜,頓覺一股強大無匹的勁氣隨著槍鋒的挺進,成階梯式的浪潮一級一級不斷加強,由四面向自己圍殺而來。觸目之下,但覺扶滄海在精奧的步法配合下,正圍繞著自己做出旋轉式的攻擊,處處俱是飛旋的人影。
他不由心中一緊,同時暗自竊喜,因為他看出了這是扶滄海竭盡平生所學的一招精華,只要自己能夠擋住這絕妙的一殺,勝負已可立判。
他當然有化解此招的辦法,事實上他在盡力防守的同時,已經作好了反攻的準備,唯一要做的,就是等待機會。
而現在就是一個機會,以格里的眼力,當然不會放過,是以他突然在這一刻變得異常冷靜,雙目厲芒綻射,凝注著長槍在每段空間與每個時段里衍生的變化與進度。
“呼……”當扶滄海的長槍如毒蛇吐信般刺破他的勁氣防線時,格里再不猶豫,一退之下,就在對方槍勢欲盡未盡之時,陡然出手了。
“轟……”爆響驚起,格里提聚的功力驀然沿著霸王鈸飛旋暴射,向四方迸裂。一時間那凝聚的草球散裂開來,疾風襲卷,花草如漫天星雨般飆射開來。
誰也想不到這飛旋的草球也是一種攻擊的武器,花草疾射,形如暗器,仿佛形成了千百個攻擊點。而最讓扶滄海感到心驚的,還不是這些,就在草球爆裂的剎那,他感到在草球的中心有一股凌厲無匹的殺氣飛襲而來。
殺氣,刀的殺氣,格里以霸王鈸成名,所以誰也沒有想到他也會使刀,而且還是用刀的高手,這才是格里真正致命的一殺!
凜冽的殺氣如針刺般直侵肌膚,眉毛倒豎,卻不能使扶滄海的眼珠轉動一下。他在瞬息之間感受著這突然的一變,并且必須要在最短的時間內作出判斷和相應的變化。
刀是彎刀,呈弧形而來,刀氣更帶著一股強大無匹的回旋之力,任何人面對此刀,都不可能真正做到無動于衷。
扶滄海也不能,不過他幸好也留了一手,所以他并非毫無回旋的余地,因為他的滄海槍法雖然名為十七式,但真正的一式殺招,就隱藏在這第十七式之后。
南海長槍世家能夠屹立江湖數百年不倒,這固然與它地處邊疆有關,實則是因為每隔數年,這個世家中都會涌現出一位杰出的弟子,對祖傳的槍法套路作出精心的改良或者重新設計。每經一人,其槍法的破綻便減少一分,漸漸達到攻守平衡的完美境地。到了上一代人的時候,長槍世家出了個扶三槍,為了檢驗這套槍法的實用性,竟然現身江湖,公然與當時最負盛名的劍客飛散人決戰于吳楚故地。雖然最終無人知道這一戰的結果,但扶三槍回來之后,認定槍法攻勢有余,防守不足,是以閉關七年,終于創出了這滄海槍法的最后一招——意守滄海!
只因這一招只守不攻,與滄海槍法十七式的全攻精髓格格不入,是以扶家子弟并沒有將它納入滄海槍法之列。但這一招一旦與之配套,攻守有度,渾然天成,又的確是這套槍法的后續之招。
此招創成數十年,今日方在扶滄海的手上展露出來,怪不得連格里這等行家高手都沒有預知此事。
“轟……”槍鋒破空,終于與彎刀碰撞一起,爆發出一股猛烈的狂風,草樹連根拔起,向四方飛瀉。
兩條人影俱覺渾身一震,身形不由自主地向后跌飛。格里心驚之下,霸王鈸陡然出手,發出了一記意想不到的攻招。
鈸鋒森寒,如圓盤飛旋,嗚嗚聲響,懾人心魄。勁氣隨著霸王鈸運行的軌跡向前罩射,頓時將扶滄海的整個人影籠罩。
扶滄海心驚這陡生的變化,再也無力作出應變之招,他不得不承認,自己低估了格里的實力,根本就沒有想到格里竟能在身體失控的情況下猶能施出這厲害的殺招。
高手之爭,虛實變幻莫測,一切全靠預判能力來搶占先機。扶滄海沒有算到格里的彎刀,但他有意守滄海應急;可是他又沒有算到格里除了彎刀之外,真正的殺人兵器是霸王鈸,這一次,他似乎死定了。
格里也是這樣認為的,所以他身體向后跌飛,氣血翻涌的同時,臉上已經露出了一絲笑意,他相信扶滄海絕對逃不過自己這致命的一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