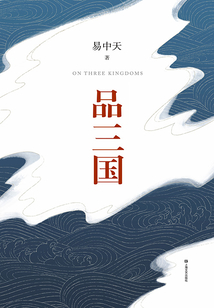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179評論第1章 開場白:大江東去
這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這是一段撲朔迷離的歷史,這是一些引人入勝的故事,這是一個津津樂道的話題。正史記錄,野史傳說,戲劇編排,小說演義。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評點,不同作品有不同的描述。是非真假眾說紛紜,成敗得失疑竇叢生。三國,究竟應該是怎樣的面目呢?
所謂“三國”,通常是指從漢獻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到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共九十年這段歷史。把這段歷史稱為“三國”,在名目上多多少少是有些問題。因為曹丕稱帝,是在公元220年;劉備稱帝,是在公元221年;孫權稱帝,是在公元222年。這個時候,魏、蜀、吳三國,才算是正兒八經地建立起來了。按理說,三國史,應該從這時開始,到三家歸晉止,那才是名正言順的“三國”。但是,縱覽古今,幾乎沒有這么講的。這么講,曹操、關羽、周瑜,還有魯肅等等,就都不能出場了。青梅煮酒、三顧茅廬、赤壁之戰、敗走麥城這些故事,也都講不成了。能行嗎?
實際上,無論是正史(比如《三國志》),還是小說(比如《三國演義》),差不多都會從董卓之亂甚至更早一些說起。這才真正是歷史的態度。因為曹、劉、孫這三大勢力或三大集團,是在東漢末年的軍閥混戰中發展壯大起來的;魏、蜀、吳三足鼎立的局面,也早在他們建國之前就已基本形成。看歷史,必須歷史地看。沒有前因,就沒有后果。只看“名”,不看“實”,咬文嚼字,死摳字眼,那不叫“嚴謹”,只能叫“鉆牛角尖”。
那么,這九十年間是個什么世道呢?
也就兩個字:亂世。展開來說,就是烽火連天,餓殍遍野,戰事頻仍,民不聊生。或者借用魯迅先生的話說,就是“夢里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然而,亂世出英雄。越是滄海橫流,越能顯出英雄本色。因此,這又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一個充滿陽剛之氣、既有英雄氣概又有浪漫情懷的時代。不知多少風流人物在這里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不知多少蓋世英雄在這里大顯身手叱咤風云,正所謂“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
列舉這些熟悉的姓名,那將是一個長長的名單。雄才大略的曹操,鞠躬盡瘁的諸葛亮,英武瀟灑的周瑜,堅忍不拔的劉備,他們都是這個時代的英雄,也都是我們民族的英雄,因為他們都想把分裂變成統一,把亂世變成治世,求得社會的和諧、天下的太平。當然,他們也都無一例外地認為,這個歷史使命應該由他們自己,或者說由他們那個集團來承擔,決不肯拱手讓給他人。因此,他們之間有矛盾,有沖突,有摩擦,有戰爭,甚至你死我活殺氣騰騰,結果是“一將功成萬骨枯”,說起來真是讓人感嘆不已,悲喜交加!
這在當時,大約也是沒有辦法的事;而歷史,也只能在悲劇性的“二律背反”中前進。一方面,是戰爭只能用戰爭來結束;另一方面,則是為了結束戰爭,人民必須先飽受戰爭的苦難。因此,當我們贊美和欣賞那些亂世英雄的時候,不要忘記那時人民所承受的痛苦。
逐鹿中原的結果是一家獨大,龍爭虎斗的結果是天下一統。這就是西晉。西晉的情況其實更加不堪,這里先不說它,且說三國。三國的一個特點是時間短。魏、蜀、吳三國的存在,不過半個多世紀;加上“前三國”時期,也不過九十年。這樣短暫的時間,在我們民族的歷史上,真不過“彈指一揮間”。人們甚至來不及認真反思和細細品味,眼睛一眨,就已老母雞變鴨。歷史往往是由勝利者來書寫的,民間修史則難免見仁見智,或者偏聽偏信。因此,魏、蜀、吳三國剛一滅亡,史書的記載就眾說紛紜,學者的見解也莫衷一是。比如諸葛亮的出山,就有“三顧茅廬”和“登門自薦”兩種說法;而赤壁那場大火,也有黃蓋詐降縱火和曹操燒船自退兩種記載。三國,是一段精彩紛呈又讓人眼花繚亂的歷史。
三國歷史的戲劇性使它成為文學藝術家垂青的對象。在民間,它也是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知道劉備的,肯定比知道劉秀的多;知道曹操的,也肯定要超過知道王莽的。這不能不歸功于文學藝術作品,尤其是《三國演義》的影響。文學藝術作品的感染力是超過史學著作的,文學藝術作品又是需要想象和虛構的。充滿想象和虛構的文學藝術作品以史為據,為線索、為題材,虛虛實實,半真半假,更為這段原本就撲朔迷離的歷史平添了許多曖昧。
就說周瑜。
提起這位江東名將,人們首先想到的,往往是“三氣周瑜”的故事,是“既生瑜,何生亮”,以及“周郎妙計安天下,賠了夫人又折兵”等等。可惜那是小說,不是歷史。歷史上的諸葛亮并不曾氣過周瑜。就算氣過,怕也氣不死。為什么呢?因為周瑜的氣量是很大的。《三國志》對他的評價是“性度恢廓”,也就是性情開朗,氣度寬宏。同時代人對他的評價也很高。劉備說他“器量廣大”,蔣干說他“雅量高致”。順便說一句,蔣干這個人,也是被冤枉了的。他是到過周營,但那是赤壁之戰一年以后,當然沒有上當受騙盜什么書。蔣干的臉上也沒有白鼻子,反倒是個帥哥。《江表傳》的說法是,“干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為對”,看來是個才貌雙全的漂亮人物。
周瑜也一樣,也是一個漂亮至極的英雄。他的“帥”,在當時可謂家喻戶曉。《三國志》說他“長壯有姿貌”,還說“吳中皆呼為周郎”。郎,就是青年男子。呼人為郎,帶有贊美的意思。所以,“周郎”就是“周帥哥”。同時被呼為“孫郎”的孫策,則是“孫帥哥”。當然,一個人的“帥”,不僅僅是外貌,更重要的是內在的氣質。周瑜恰恰是一個氣質高貴、氣度恢弘的人。他人品好,修養高,會打仗,懂藝術,尤其精通音樂。即便酒過三巡,醺醺然之中,也能聽出樂隊的演奏是否準確。如果不準,他就會回過頭去看,當時的說法是“曲有誤,周郎顧”。因此,我甚至懷疑他指揮軍隊也像指揮樂隊,能把戰爭變成藝術,把仗打得十分漂亮,就像藝術品一樣。
周瑜的仗打得確實漂亮。赤壁之戰中,他是孫劉聯軍的前線總指揮。蘇東坡的《念奴嬌·赤壁懷古》說:“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羽扇,就是羽毛做的扇子。綸巾,就是青絲做的頭巾。羽扇綸巾在當時是儒雅的象征。本來,貴族和官員是應該戴冠的。高高的冠,寬寬的衣,峨冠博帶,即所謂“漢官威儀”。但是到了東漢末年,不戴冠而戴巾,卻成為名士的時髦。如果身為將帥而羽扇綸巾,那就是儒將風采了。于是我們就不難想象出當時的場景:曹操的軍隊列陣于長江,戰艦相連,軍旗獵獵,江東之人,魂飛魄散,膽戰心驚。然而周瑜卻安之若素,從容不迫。他戴綸巾,搖羽扇,運籌帷幄,指揮若定,終于克敵制勝,以少勝多。這真是何等的驚心動魄!這個時候的周瑜,真可謂少年英雄,意氣風發,光彩照人!
當然,戰爭不是藝術,不可能那么瀟灑,那么儒雅,那么風流倜儻,更不可能談笑風生之間,不可一世的“強虜”就“灰飛煙滅”了。這個時候的周瑜,迎娶小喬已經十年,也并非“小喬初嫁了”。蘇東坡那么說,無非是要著力刻畫周瑜的英雄形象罷了。文學作品是不能當作歷史來看的,但要說歷史上的周瑜英武儒雅,卻大體不差。周瑜二十四歲就被孫策任命為“建威中郎將”,馳騁疆場,建功立業。也就在這一年,孫策和周瑜分別迎娶橋公之女大橋和小橋[1]為妻,這就是蘇東坡所謂“小喬初嫁了”。可見周瑜這個人,是官場、戰場、情場,場場得意。對于一個男人來說,難道還有比這更讓人羨慕的嗎?這樣一個春風得意的人,怎么還會嫉妒別人,又怎么會因為嫉妒別人而被氣死呢?我們嫉妒他還差不多。
沒錯,周瑜和劉備集團是有過明爭暗斗,也曾經建議孫權軟禁劉備、分化關張,這事我們以后還會說到。但那是其集團政治利益所使然,與心胸和氣量無關。而且,周瑜忌憚的是劉、關、張,不是諸葛亮。老實說,那時周瑜還真沒把諸葛亮當作頭號勁敵,怎么會去暗算他?反倒是原本高風亮節的諸葛亮,卻因為編造出來的“三氣周瑜”,被寫成了“奸刁險詐的小人”(胡適先生語),想想這真是何苦!
于是我們發現,歷史距離我們,有時候竟是那樣的遙遠。
實際上,許多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都有三種面目,三種形象。一種是正史上記載的面目,我們稱之為“歷史形象”。這是史學家主張的樣子。這里需要說明一下,就是“歷史形象”不等于“歷史真相”。歷史有沒有“真相”?有。能不能弄清楚?難。至少,弄清楚三國的歷史真相,很難。因為我們已經找不到當時的原始檔案,也不能起古人于地下,親口問一問。就算能問,他們也未必肯說實話。這就只能依靠歷史上的記載,而且主要是“正史”。但即便是“正史”,也有靠不住的地方、靠不住的時候。史學大師呂思勉先生的《三國史話》,就多次提到《三國志》、《后漢書》等等記載未必可靠。何況劉備的那個蜀漢,還沒有官修史書。《三國志》中的有關記載,竟是“耳聞目見”加“道聽途說”。這樣一來,我們又只能寄希望于歷史學家的考證。然而歷史學家的看法也不一致。比如蜀漢政權“國不置史,注記無官”一事,就被唐代史學家劉知幾認為是污蔑不實之詞,謂之“厚誣諸葛”。這可真是越來越說不清。因此,我們只能把“歷史形象”定位為史書上記載的,或者歷史學家主張的形象。而且還得說清楚,即便這個形象,也并非只有一種,也是有爭議的。
第二種是文藝作品包括小說和戲劇中的面目,我們稱之為“文學形象”。這是文學家藝術家主張的樣子,比如《三國演義》和各種“三國戲”。
還有一種是老百姓主張的樣子,是一般民眾心中的面目,我們稱之為“民間形象”,比如各種民間傳說和民間習俗、民間信仰,也包括我們每個人自己心目中的形象。其實,我們每個人的心目中,也都有一個歷史人物形象的。因此,一部歷史劇拍出來,總會有觀眾議論“像不像”的問題。其實,這些歷史人物,誰都沒有見過,卻可以議論“像不像”,可見每個人心里都有一本“賬”。
文學形象和民間形象的形成,也有一個歷史過程。大體上是越到后代,就越不靠譜,主觀臆想和個人好惡的成分就越多。當然,有了科學的歷史觀以后,又另當別論。但我們前面說過,文學藝術作品的感染力是超過史學著作的。街頭巷尾的口口相傳,其力量同樣不可小看。民間人士不是歷史學家,不需要“治學嚴謹”,也不必對誰負責,自然“想唱就唱”。這原本也沒什么。但是,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同樣,一種形象,如果說的人多了,就有可能從“假象”變成“真相”。
就說諸葛亮。
諸葛亮這個人,至少從晉代開始,就是許多人追捧的對象,可謂魅力四射,粉絲如云。當時有一位郭沖先生,大約是諸葛亮的鐵桿粉絲,感覺大家對諸葛亮的崇拜還不夠,于是“條亮五事隱沒不聞于世者”,其中第三件事就是空城計。這五件事,都被裴松之在為《三國志》作注的時候駁回。駁空城計的證據是:諸葛亮屯兵陽平的時候,司馬懿官居荊州都督,駐節宛城,根本就不可能出現在陽平戰場,哪來的什么空城計?
不過這個故事實在太好聽了,于是《三國演義》便大講特講,三國戲也大演特演,所謂“失空斬”(失街亭、空城計、斬馬謖),歷來就是久演不衰的折子戲。但這個故事不是事實,也不合邏輯。第一,司馬懿不敢進攻,無非是害怕城中有埋伏。那么,派一隊偵察兵進去看看,行不行?第二,司馬懿“果見孔明坐于城樓之上,笑容可掬”,距離應該不算太遠,那么,派一個神箭手把諸葛亮射下城樓,來他個“擒賊先擒王”,行不行?第三,按照郭沖的說法,當時司馬懿的軍隊有二十萬人,諸葛亮只有一萬人;按照《三國演義》的說法,當時司馬懿的軍隊有十五萬人,諸葛亮只有二千五百人。總之是敵眾我寡。那么,圍他三天,圍而不打,行不行?何至于掉頭就走呢?所以裴松之作注時,就斷定郭沖所言不實。裴松之說:“就如沖言,宣帝(司馬懿)既舉二十萬眾,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設防持重,何至便走乎?”
所以,空城計是靠不住的。其他如火燒新野、草船借箭,也都是無中生有。火燒博望是有的,但那把火是劉備所放(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偽遁,惇等追之,為伏兵所破),沒聽說有諸葛亮什么事。火燒赤壁也是有的,但那是周瑜部將黃蓋的主意和功勞,也沒諸葛亮什么事。借東風就更可笑。諸葛亮“沐浴齋戒,身披道衣,跣足散發”,登壇祭風,簡直就是裝神弄鬼,所以魯迅先生說《三國演義》“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這里說的“妖”,不是妖精或妖怪,是“妖人”,即巫師或神漢一類。
諸葛亮當然不是“妖人”。不但不是“妖人”,還是“帥哥”。陳壽的《上〈諸葛亮集〉表》說他“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漢代的八尺,相當于現在的五尺五寸,也就是一米八四。諸葛亮出山的時候,年齡則是二十六歲。二十六歲的年齡,一米八四的個子,而且“容貌甚偉”,大家可以想想是什么形象。至少,不可能是一身道袍,一臉長須的。羽扇綸巾大概是事實,因為那是當時的時尚,也就不是諸葛亮的專利。所謂“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說的是周瑜,不是諸葛亮。就算有“借東風”這事,也該是周瑜去“借”(民間傳說便有說周瑜借東風的),要不然杜牧怎么說“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其實諸葛亮在赤壁之戰期間的主要功績,是促成了孫劉的聯盟;他對劉備集團的主要貢獻,則是確立了聯吳抗曹、三分天下的政治策略,并身體力行。實際上諸葛亮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未必是杰出的軍事家。他的軍事成就是有爭議的,他的軍事才能也不像后世傳說的那么玄乎。歷史學家繆鉞先生就曾在《三國志選》的“前言”中指出:“諸葛亮征南中事,當時傳說不免有夸大溢美之處,譬如對于孟獲的七擒七縱,是不合情理的,所謂‘南人不復反’,也是不合事實的。”諸葛亮也不像文學作品和民間傳說中說的那樣迭出險招。愛出險招的是郭嘉。而諸葛亮的特點,無論是史家的評論,還是他的自我評論,都是“謹慎”。陳壽說他“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于將略”,應該說是實事求是的評價。也就是說,諸葛亮是蕭何,不是張良和韓信。
但是,到了《三國演義》里面,諸葛亮就集蕭何、張良和韓信于一身,不但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而且神機妙算未卜先知。任何人,只要按照他的“錦囊妙計”行事,就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劉備集團的大將如關羽、張飛、趙云輩,有如他手中的提線木偶,理解也執行,不理解也執行。這當然不是事實,但有原因。什么原因呢?我們以后再說。
其實,“錦囊妙計”的故事是有的,可惜是發生在曹操身上。這事記載在《三國志·張遼傳》里,時間則是在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我們以后再說。“空城計”的故事大約也是有的,曹操、文聘、趙云可能都使過。不過這事有爭議,我們也只好以后再說。但是,即便沒有爭議,大家也不會講,因為民間不喜歡曹操。
民間對于三國,也是很關注的,其熱情決不亞于史學家。我們知道,中國四大古典名著中,《紅樓夢》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最高,有“閑談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也枉然”的說法。但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細民所嗜,則仍在《三國》、《水滸》。”也就是說,老百姓喜歡的還是《三國》和《水滸》。事實上對中國社會影響最大的,不是《紅樓》,而是《三國》和《水滸》。比如屠宰業奉張飛為祖師爺,編織業奉劉備為祖師爺,強盜奉宋江為祖師爺,小偷奉時遷為祖師爺,沒聽說過哪個行業奉《紅樓夢》人物比如賈寶玉、王熙鳳為祖師爺的。所以,三國人物的民間形象,也很值得研究。
就說關羽。
關羽確實有令人崇敬之處,那就是特重情義。他被曹操俘虜后,曹操對他“禮之甚厚”,關羽自己也說“吾極知曹公待我厚”,但他仍然不肯背叛劉備,最后的選擇是“立效以報曹公乃去”。結果曹操對他更為敬重(曹公義之),竟然任其重返敵營(奔先主于袁軍)。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出,關羽固然是義薄云天,曹操也堪稱俠肝義膽,至少是尊重俠肝義膽的。可惜人們都只記住了關羽的“情”,忘記了曹操的“義”,這不公平。
民間崇拜關羽雖然有道理,但有些信仰和習俗也很奇怪。比方說剃頭匠奉關羽為祖師爺,就匪夷所思。關羽并沒有當過剃頭匠呀!再說東漢時也不剃頭。想來想去,也就是他們手上都有一把刀。不過關老爺手上的刀是殺頭的,不是剃頭的。清代有一剃頭鋪門前掛一對聯云:“磨礪以須,問天下頭顱幾許;及鋒而試,看老夫手段如何”,倒很像關羽的口氣。
另一件奇怪的事是把關羽當作財神。關羽是身經百戰的將軍,當戰神還有道理,怎么會是財神呢?這當然也有道理,我們也以后再說。不過,我看總有一天,關羽會變成愛神,供奉到婚姻介紹所去,因為他對愛情的追求是很執著的。據《三國志·關羽傳》裴松之注引《蜀記》和《華陽國志》,關羽曾經愛上了一個女人,一再向曹操表示要娶其為妻。這話說多了以后,曹操便“疑其有異色,先遣迎看”。一看,果然國色天香,結果“因自留之”,害得關羽很是郁悶(羽心不自安)。此事如果屬實,曹操就太不地道了。
現在我們知道,三國這段歷史,其實有三種形象:歷史形象、文學形象和民間形象。那么,我們應該怎么看?
首先還是要弄清楚“歷史形象”,這就要讀正史,比如《三國志》。《三國志》的作者是陳壽。陳壽是四川南充人,他在西晉統一后五年(公元285年)就完成了《三國志》,時間隔得不久,治學態度又嚴謹,比較靠得住。不過,正因為陳壽治學態度嚴謹,許多當時的材料都棄而不用,《三國志》就比較簡略。于是又有裴松之的注。裴松之是山西聞喜縣人,生活在南朝劉宋時代。他作注的時候,距離陳壽完成《三國志》大約一百三十年。裴注的特點,是補充了大量材料,包括陳壽舍棄的和陳壽沒見到的,并加以辨析。無法考證和辨析的就存而不論。可見裴松之的治學態度也是很嚴謹的,所以裴注也比較靠得住。所謂“正說”,依據就是這兩個:陳壽的“志”,裴松之的“注”。其他的史書,當然也可以參考,但如果發生沖突,那就還是“先入為主”,以“壽志裴注”為據的好。
不過,“文學形象”和“民間形象”也并非就沒有意義或沒有道理。事實上,很多人是把三國尤其是《三國演義》當教科書來看的。正如孫犁先生所說:“謀士以其為智囊,將帥視之為戰策”,清代統治者還把《三國演義》作為“內部文件”發給親貴。錢鍾書先生的《管錐編》也談到好幾起后人學“空城計”的事實,甚至認為“空城計”是“不欺售欺”的典型范例。錢先生說:“夫無兵備而坦然示人以不設兵備,是不欺也;示人實況以使人不信其為實況,‘示弱’適以‘見強’是欺也。”毛宗崗父子的批語(簡稱毛批)也很有道理:“唯小心人不做大膽事,亦唯小心人能做大膽事。……孔明若非小心于平日,必不敢大膽于一時。仲達不疑其大膽于一時,正為信其小心于平日耳。”不過魏禧的說法更有意思:“若遇今日山賊,直入城門,捉將孔明去矣。”可見即便是民間形象和文學形象,甚至即便是張冠李戴、移花接木、無中生有,也能給人教益。因為一種形象能夠形成,能夠流傳,自然有它的道理。我們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把這些道理講出來。
這就又有三件事要做。一是要“還原”,就是告訴大家歷史的本來面目是怎么樣的。二是要“比較”,就是看看這三種形象究竟有什么不同。三是要“分析”,就是弄清楚歷史形象為什么會變成文學形象和民間形象。我們希望通過這三項工作,來為大家品讀三國。
這當然并不容易。
其實,正如歷史有三種形象,歷史也有三種讀法。一種是站在古人的立場上看歷史,這就是錢穆先生所謂“歷史意見”;一種是站在今天的立場上看歷史,這就是錢穆先生所謂“時代意見”;還有一種站在自己的立場上看歷史,這就是“個人意見”。任何人講歷史,都不可能不涉及這三種意見。畢竟,“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再輝煌的事件和人物,都可能只留下一些模糊的印象,任人評說。張昇的詞說:“多少六朝興廢事,盡入漁樵閑話。”其實“盡入漁樵閑話”的,又豈止是“六朝興廢事”?那是可以包括一切歷史的。正所謂“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接下來,我們將笑談三分,品讀三國。那么,從何說起呢?我想,還是從那個歷史形象、文學形象、民間形象最復雜,分歧最多,爭論最大的人說起,就讓他引領我們走進那段原本就很復雜而又波瀾壯闊的歷史吧!
[1]經核查,“大喬小喬”是宋代人蘇東坡說的,而晉人陳壽《三國志·周瑜傳》中橋工的兩個女兒,的確寫作“大橋小橋”。古人寫作沒有今人規范,所以陳壽沒有錯,蘇東坡也算不得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