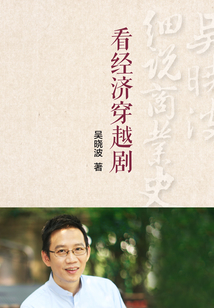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 2評論第1章 經(jīng)濟穿越劇
企業(yè)家到底是一頭怎樣的“豬”?
企業(yè)家被看成是“谷倉前空場上的一頭豬”,它能夠搜索出其他動物看不到的谷物的屑粒。
“企業(yè)家”這個詞最早出現(xiàn)于16世紀(jì)初的法語。1815年,法國哲學(xué)家薩伊在《政治經(jīng)濟學(xué)概論》中嘗試對企業(yè)家進行定義:“將所有生產(chǎn)資料集中在一起,并對他所利用的全部資本、所支付的工資價值、利息和租金,以及屬于他自己的利潤進行重新安排。”
在其后的100多年里,薩伊的定義被一再地引用。到了1942年,在哈佛大學(xué)任教的奧地利經(jīng)濟學(xué)家約瑟夫·熊彼特又在薩伊的定義上添了精巧的一筆。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中,他提出企業(yè)家的工作就是“創(chuàng)造性破壞”。熊彼特斷言,如果不進行創(chuàng)新和變革,就不會再成長,企業(yè)家必須讓資源在破壞中獲得新的移動。
芝加哥大學(xué)的經(jīng)濟學(xué)家伊斯雷爾·柯茨納便把企業(yè)家看成是“谷倉前空場上的一頭豬”。他說,這頭豬是一個“機會的偵察員”,它能夠搜索出其他動物看不到的谷物的屑粒。
當(dāng)然,也有人拿企業(yè)家與其他的職業(yè)人相比較。美國風(fēng)險投資家戴維·西爾弗在《企業(yè)家——美國的新英雄》一書中便把企業(yè)家與藝術(shù)家進行了一次有趣的對比:“企業(yè)家與藝術(shù)家有許多共同之處。他們都是問題解決者。藝術(shù)家通過畫布而企業(yè)家通過自己的公司來表達解決問題的方式。這兩種人都是個人主義者,他們異常敏感,富有想象力,熱情洋溢,復(fù)雜,充滿活力而且富有創(chuàng)造性。他們另一個相似的地方是,他們都不期望從他們的努力中獲得樂趣。”
企業(yè)家的能力被描述為“把社會的需要轉(zhuǎn)變?yōu)槠髽I(yè)的盈利機會”。日本索尼公司的創(chuàng)始人盛田昭夫常喜歡用鞋子推銷員的故事講述企業(yè)家的發(fā)現(xiàn)和創(chuàng)造精神:
兩個鞋子推銷員來到非洲的一個未曾開發(fā)的小島部落,發(fā)現(xiàn)當(dāng)?shù)氐耐林疾淮┬R粋€推銷員向總部發(fā)了這樣一封電報:“這里的人都不穿鞋,沒有一點銷售前景。”而另一個推銷員則發(fā)回了完全不同的電報:“這兒沒有一個人穿鞋,我們可以占領(lǐng)整個市場。請將所有的存貨通通運過來。”
沒有一個故事比它更能生動地展現(xiàn)企業(yè)家發(fā)現(xiàn)機遇和創(chuàng)造需求的能力。而另一個同樣頗為有趣的問題是,如果是一個哲學(xué)家和推銷員一起去小島又會發(fā)生什么事情?也許下面的假設(shè)是可能發(fā)生的:
哲學(xué)家將花一個月思考為什么土著人不用穿鞋;第二個月他將論證把鞋子推銷給土著人的必要性;當(dāng)推銷員用鞋子換走一船一船的寶石和礦物的時候,哲學(xué)家又將證明這是對等和道德的,還是一種掠奪的行為。
這樣的對比盡管十分空泛,但卻耐人尋味。無論怎樣的定義、描述或比較,企業(yè)家都至少擁有如下的特質(zhì):
他對資源的集中、移動,或者破壞,都是為了讓自己能夠獲得額外的那一部分;他改造世界的前提,是這種行為必須能夠為自己贏取超額的利潤;他只做確定的、承擔(dān)有限責(zé)任的、可以被量化衡定的工作。
企業(yè)家總是那么實際,他們不對現(xiàn)實以外的任何東西存留幻象,他們往往能不受誘惑地透過事物表層而直達問題的核心,而這幾乎是職業(yè)的本能。
1970年代美國最傳奇的企業(yè)家,工人出身的李·艾柯卡在危難之際出任克萊斯勒汽車公司總裁,他孤身到工會與憤怒的、要求增加薪水的工人們談判。當(dāng)有人質(zhì)問他,作為勞苦工人的后裔,他為什么不滿足大家要求多放幾個子兒的微薄條件?艾柯卡簡單地告訴他們:“我決定著你們的命運,我每小時17美元資助全公司所有的工人上班,但在每小時20美元時,我不會雇傭一個人。因此,你們最好達成一致意見。”
延用伊斯雷爾·柯茨納式的比喻,李·艾柯卡不僅是一頭善于發(fā)現(xiàn)機會的“豬”,而且還有著其他的特征:冷血、量化、促進生產(chǎn)力的提高。
我為什么愿意穿越回宋朝?
與唐漢明清相比,宋代就是一個不太強大但有幸福感的朝代。
有雜志給我發(fā)問卷:“如果你能穿越,最喜歡回到哪個朝代?”我想了一下說,“宋朝吧。”
為什么是宋代呢?那不是一個老打敗仗、老出投降派、老沒出息的朝代嗎?連錢穆老先生都說,“唐漢宋明清5個朝代里,宋是最貧最弱的一環(huán),專從政治制度上看來,也是最沒有建樹的一環(huán)。”其實我想說的是,強大就值得向往嗎?在我看來,與唐漢明清相比,宋代就是一個不太強大但有幸福感的朝代。宋代開國100多年后,當(dāng)時的人們開始比較本朝與其他朝代,我們現(xiàn)在聽不到他們討論的聲音,不過估計也與現(xiàn)在一樣,感嘆“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這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有一位大學(xué)問家叫程伊川,說得比較具體,他總結(jié)“本朝超越古今者五事”:一是“百年無內(nèi)亂”;二是“四圣百年”——開國之后的四位皇帝都比較開明;三是“受命之日,市不易肆”——改朝換代的時候兵不血刃,沒有驚擾民間;四是“百年未嘗誅殺大臣”——00多年里沒有誅殺過一位大臣;五是“至誠以待夷狄”——對周邊蠻族采取懷柔政策。由此可見,宋代確實是別開生面。宋代的皇帝對知識分子很尊重,100年沒有殺過一人。看著實在討厭了,就流放,流放了一段時間,突然想念了,再召回來。文人之間也吵架,但都不會往死里整。王安石搞變法的時候,司馬光在大殿上跟他吵,王安石就把他趕到洛陽去。司馬光去了洛陽后就埋頭編《資治通鑒》,編累了,就寫一封公開信罵罵王安石。王看到了,也寫公開信回罵。
宋代對商人很寬松。在漢朝的時候,商人要穿特別顏色的衣服,不能坐有蓋子的馬車;到了唐朝,《唐律》仍然規(guī)定“工商雜類不預(yù)士伍”、“禁工商不得乘馬”,而且商品交易只準(zhǔn)在政府規(guī)定的“官市”中進行;到了宋朝,這些規(guī)定都不見了,商人子弟可以考科舉當(dāng)官,文人們都不太在意自己的商人家庭背景。朱熹就很得意地回憶說,他的外祖父是一個開酒店、做零售的商人,當(dāng)年可有錢了,“其邸肆生業(yè)幾有郡城之半,因號半州”。政府對集市貿(mào)易的控制也完全地開放了,老百姓可以在家門口開店經(jīng)商,各位日后看電視劇,看到老百姓隨地擺攤做生意的場景,那都是宋以后的景象。如果電視劇演的是漢唐故事,你大可以寫微博去嘲笑一下編劇同學(xué)。
宋代的文明水平達到前所未見的高度。中國古代的“四大發(fā)明”,除了造紙術(shù)之外,其余三項——指南針、火藥、活字印刷術(shù)均出現(xiàn)于宋代。臺灣學(xué)者許倬云的研究發(fā)現(xiàn),“宋元時代,中國的科學(xué)水平到達極盛,即使與同時代的世界其他地區(qū)相比,中國也居領(lǐng)先地位”。宋代的數(shù)學(xué)、天文學(xué)、冶煉和造船技術(shù),以及火兵器的運用,都在世界上處于一流水準(zhǔn)。
宋代的城市規(guī)模之大、城市人口比例之高,超出了之前乃至之后的很多朝代。兩宋的首都汴梁和臨安,據(jù)稱都有百萬人口。當(dāng)時的歐洲,最大的城市不過15萬人。
正因為有如此繁華,所以馬可·波羅寫的那本游記,讓歐洲人羨慕了幾百年。法國學(xué)者謝和耐斷定,“在宋代時期尤其是在13世紀(jì),透出了中國的近代曙光。”南宋滅亡之后,蒙古人統(tǒng)治了中原98年,之后又有明清兩朝,其高壓專制程度遠遠大于宋代,更糟糕的是,實行閉關(guān)鎖國政策,中國人的格局從此越來越小,文明創(chuàng)新力也幾乎喪失殆盡。
簡單說到這里,你知道我為什么愿意穿越回宋朝了吧——跟漢朝比,宋朝無內(nèi)亂;跟唐朝比,宋朝更繁華舒適;跟明清比,宋朝更開放平和;跟當(dāng)代比,宋朝沒有空調(diào)、汽車和青霉素,不過也沒有含三聚氰胺的牛奶。其實,人生如草,活的就是從容兩字。
1978年城市化率緣何不如南宋?
在超過800年的時間里,中國的城市人口比例不是增加,而是下降了。
先告訴大家一個數(shù)據(jù),你聽到之后也許會非常吃驚:中國在南宋時期的城市化率為22%,而到改革開放的1978年時,城市化率僅為18%。
也就是說,在超過800年的時間里,中國的城市人口比例不是增加,而是下降了。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中國由世界第一強國轉(zhuǎn)為“東亞病夫”的全過程。
中國的城市興毀基本上都是政治的結(jié)果。自古以來,中國建城就是以政治軍事為主要功能,城池是侯國的都城,是獨立的地方政治中心。史料顯示,西周建立之后,分封了1000多個諸侯國。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shù)字,即便一個諸侯國只有一座城池,也起碼要有上千座大大小小的城鎮(zhèn)。
到了春秋末期、戰(zhàn)國初期,一些城市的規(guī)模已經(jīng)非常之大,在當(dāng)時的世界上無出其右。據(jù)考證,面積在6平方公里之上的城市起碼就有15座,其中,燕下都的面積達32平方公里,靈壽和臨淄分別為18和16平方公里。臨淄有人口7萬戶,按平均每戶5人計算,是一個擁有35萬人口的超大型城市,與同一時期的西方世界相比,中國的城市規(guī)模顯然要大幾倍,在希臘城邦臻于極盛的伯里克利(約公元前495年至公元前429年)執(zhí)政時期,雅典城的人口為15萬人。根據(jù)學(xué)者的計算,春秋末期的人口總數(shù)為3200萬人,而城市居民人數(shù)就多達509萬人,城市人口比重為15.9%。據(jù)此可以得出一個令人驚奇的結(jié)論:早在戰(zhàn)國時期,中國的城市化已然相當(dāng)高了。
到了宋代,城市的繁榮達到頂峰,北宋首都汴梁(今開封)和南宋首都臨安(今杭州)的人口都超過100萬,同時期的歐洲人簡直無法想象這個數(shù)字。據(jù)羅茲曼的計算,一直到1500年前后,歐洲最大的4個城市是米蘭、巴黎、威尼斯和那不勒斯,人口只有10萬至15萬。
進入明代之后,“水稻革命”和“棉花革命”讓中國的人口繁衍速度大增,尤其以江南地區(qū)的增長最快,原有的中心都市無力接納,于是地理條件較好的農(nóng)村向市鎮(zhèn)演化。而人口增加的同時,土地卻越來越緊張,漫溢出來的人口就順著棉業(yè)的發(fā)展而從事家庭紡織勞作,在這些農(nóng)戶的周邊又自然地出現(xiàn)了大型交易集市。這些新型市鎮(zhèn)與傳統(tǒng)市鎮(zhèn)的最大不同之處是,它們興起的功能不是為農(nóng)村消費服務(wù),而是為農(nóng)村生產(chǎn)服務(wù),參與貿(mào)易的不是“以物易物”的小農(nóng)戶,而是大商販和巨額資金,他們的利益所得,來自于規(guī)模化經(jīng)營和遠途販運。
史家將這一轉(zhuǎn)變歸納為中國城市化的“離心現(xiàn)象”——在其他國家,城市人口比重愈來愈高,也愈來愈集中,小城市變大,大城市變得更大;但是在中國,宋代以后城市人口的集中程度逐次減弱,大中型城郡停止擴充,明清兩代的幾個大都市,從人口到城區(qū)規(guī)模都比兩宋和元代時縮小許多,人口反而向農(nóng)村靠攏,形成江南地區(qū)的眾多市鎮(zhèn)。
自明初到清末的300余年間,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陷入停滯,城市總?cè)丝谥^對數(shù)幾乎沒有增長,但是全國總?cè)丝趧t在不斷增加——從明代初期的7000萬人,至清代乾隆年間已將近3億,城市人口比重日趨降低,這種趨勢到19世紀(jì)中葉達到谷底。
這種人口和經(jīng)濟重心向農(nóng)村下放的現(xiàn)象,最為真實地表明,中國社會的平鋪化和碎片化態(tài)勢。它既是人口增長和產(chǎn)業(yè)經(jīng)濟發(fā)展的客觀結(jié)果,同時也是中央集權(quán)制度的必然引導(dǎo)。
在城市離心化的大趨勢下,進而出現(xiàn)了“油水分離”的社會景象:政治權(quán)力集中于城市,為政府所全面控制。城市從此成為權(quán)錢交易中心和奢侈消費中心,而非生產(chǎn)制造中心。經(jīng)濟力量集中于數(shù)以萬計的市鎮(zhèn),為民間勢力所掌握,大量手工業(yè)分散于更多的村莊,這使得資本、人才和資源的集聚效應(yīng)根本無法發(fā)揮。
《南京條約》:衰落的結(jié)果還是原因?
西方學(xué)者將戰(zhàn)爭看成是中國衰落的結(jié)果,它讓中國“擺脫”了閉關(guān)鎖國的狀態(tài)。
每一個人生,每一個國家,都活在一些歷史的記憶中。2012年,在歐洲,最熱鬧的文化活動是紀(jì)念狄更斯誕生200周年,而經(jīng)濟界的頭等話題則是歐元誕生10周年。在中國,可拿來紀(jì)念的事件也不少,比如鄧小平南巡20周年,中美恢復(fù)邦交40周年,還有就是,清政府簽署《南京條約》170周年。
《南京條約》的簽署意味著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的結(jié)束,以及一個新時代的開始。1842年8月,清政府在與英國軍隊的交戰(zhàn)中屢戰(zhàn)屢敗,接連失去廈門、寧波、上海等重要城市,被迫簽下喪權(quán)辱國的《南京條約》。條約內(nèi)容包括:賠款2100萬銀元,割讓香港島,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為通商口岸,以及中方必須與英國協(xié)商英商進出口貨物需繳納的關(guān)稅。
這份條約如同一枚炮彈,在沉重而銹跡斑斑的國門上轟開了一個血腥的缺口。這是中國歷史的一個轉(zhuǎn)折,是中國現(xiàn)代化的起點。在此前長達兩千年的時間里,中國人控制了東亞地區(qū)的政治和經(jīng)濟活動,當(dāng)歐洲人進入這一片領(lǐng)域的時候,他們并沒有特別的優(yōu)勢,中國人也只是把歐洲人視為必須容忍的競爭對手,而不是一個入侵者,這與世界其他地區(qū)發(fā)生的景象非常不同。
這種均衡一直到19世紀(jì)中期才被徹底擊破。根據(jù)安格斯·麥迪森的統(tǒng)計,從1700年到1820年的120年間,中國的人均GDP增長率為零;同期,美國為72%,歐洲為14%,日本為13%,全世界平均增長率為6%。這些數(shù)據(jù)如此殘酷地告訴我們,歷史的轉(zhuǎn)折為什么會發(fā)生。
很多人帶著復(fù)雜而惋惜的心情解讀這一影響世界走向的轉(zhuǎn)折。
后世的中西方學(xué)者對于鴉片戰(zhàn)爭的評價有微妙的差異。中國學(xué)者大多數(shù)將這場戰(zhàn)爭看成是徹頭徹尾的侵略戰(zhàn)爭,是導(dǎo)致中國衰落的罪魁禍?zhǔn)住6鞣綄W(xué)者則傾向于將戰(zhàn)爭看成是中國衰落的結(jié)果,而不是原因,正是這場戰(zhàn)爭讓中國“擺脫”了閉關(guān)鎖國的狀態(tài)。
卡爾·馬克思在1853年7月22日給《紐約每日論壇報》寫的文章中論述道:“這個暴動的發(fā)生,無疑得益于英國的大炮將一種名叫鴉片的催眠藥品強加給中國。在英國的武力面前,滿清王朝的權(quán)威倒下成為碎片;天朝永恒的迷信破碎了;與文明世界隔絕的野蠻和封閉被侵犯了,而開放則達成了。”
進入當(dāng)代之后,即便是一些非常同情中國的學(xué)者,也從經(jīng)濟史的角度提出了這場戰(zhàn)爭的“不可避免性”。彭慕蘭寫道,“仔細研究可知,鴉片是促進世界貿(mào)易、加速經(jīng)濟增長最重要的動力,對中國是如此,對歐洲、美洲也是如此。”
盡管,發(fā)生在史界的這些爭論一直沒有停歇,然而,我們也可以從中得出某些具有共識性的結(jié)論:
其一,在工業(yè)革命中,一個國家的財富水平和財富總量,與其工業(yè)化的時機、速度以及成功之間并不是簡單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技術(shù)革新構(gòu)成了工業(yè)化進程的核心。然而在清代中國,總體上缺少推動生產(chǎn)方式發(fā)生根本性變革的激勵機制。
其二,工業(yè)革命和西方式的資本主義是以一種非常突然的方式“空降”到東亞地區(qū)的,作為被接受方,中國乃至所有東亞各國在心理、制度上所遭到的打擊都是巨大而慘烈,甚至是毀滅性的。
至今,我們回望170年前的那場戰(zhàn)爭以及那份條約,似乎已經(jīng)非常遙遠。但是,在制度的意義上,它給予國人的警醒卻依舊存在。我們?nèi)匀豢梢蕴岢鲞@樣的問題:在我們這個經(jīng)濟總量已經(jīng)居于全球第二的國家,是否已經(jīng)建立了推動生產(chǎn)方式發(fā)生根本性變革的激勵機制?那些外來的“變革基因”是否已經(jīng)在我們的政治及社會傳統(tǒng)中得到了充分的消化和融合?
所有這些問題,在我看來,其實還仍然是問題。
穿越回100年前,你將看到怎樣的商業(yè)中國
在2014年回望1914年的中國,百年若隱若現(xiàn),我們看到是一個陌生卻又有點熟悉的國家。
這一年,混亂的中國政壇猛烈地搖晃了一下。在上一年舉行的眾議院選舉中,國民黨贏得壓倒性勝利,盛傳將出任內(nèi)閣總理的國民黨領(lǐng)袖宋教仁卻被暗殺了,很快,國民黨在江西宣布“二次革命”,袁世凱的北洋軍在戰(zhàn)爭中獲勝。
而在地球上發(fā)生的最重大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由于歐洲列強陷入混戰(zhàn),無暇東顧,亞洲列國竟在經(jīng)濟上成了最大的獲益國之一,日本乘機擴大勢力,而對于中國來說,中國民族企業(yè)家獲得了喘息和崛起的機會。中國的工業(yè)經(jīng)濟從這一年開始,進入到一個高速成長的軌道上,據(jù)美國經(jīng)濟史學(xué)者托馬斯·羅斯基的計算,從1912年到1927年之間的工業(yè)平均增長率高達15%,位于世界各國的領(lǐng)先地位。在百年企業(yè)史上,這樣的高速成長期只出現(xiàn)了三次,其余兩次分別是1950年代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和1978年之后的改革開放時期。
第二次工業(yè)化浪潮
開始于1914年的這一輪實業(yè)投資熱,被史家認為是中國第二次工業(yè)化浪潮,它將一直持續(xù)到1924年。與上一輪的洋務(wù)運動時期相比,它有明顯不同的特征。
洋務(wù)運動是一次自上而下、由處于衰落期的清政府發(fā)動的,它的主角是洋務(wù)派大臣以及附庸于他們的官商,其工業(yè)化的特點是對軍事工業(yè)的關(guān)注,優(yōu)先發(fā)展重工業(yè),以國營資本為主力,創(chuàng)辦大型企業(yè)為主軸,到后期則把重點投注到鐵路、礦務(wù)和鋼鐵等資源性領(lǐng)域。洋務(wù)運動奠定了中國近代重工業(yè)的基礎(chǔ)。
這一輪工業(yè)化則是一次民營資本集體崛起的盛宴,它的主角是以盈利為主要動力的新興企業(yè)家,他們投資的產(chǎn)業(yè)主要集中于民生領(lǐng)域,以提供消費類商品為主,面大量廣的中小企業(yè)是最有活力的主流力量。在這期間,中國完成了輕工業(yè)的布局。其中,上海是紡織、食品和機械制造的中心,在1912年到1924年,上海地區(qū)出現(xiàn)了202家機器工廠,主要是生產(chǎn)針織機、小型車床和馬達、農(nóng)產(chǎn)品加工設(shè)備等等,廣東地區(qū)則是煙草、造紙和火柴工業(yè)的集散地。
這些產(chǎn)業(yè)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進口替代型”,在過去的四十多年里,外國公司已經(jīng)在眾多民生領(lǐng)域進行了大量的投資并引發(fā)了消費的空間,民族資本正是在這一前提下,靠生產(chǎn)成本的低廉以及對本土市場的熟悉而逐步發(fā)展起來的。這一特征與1978年之后的中國民營公司的成長路徑驚人地類似。
榮家:面粉與棉紗
1914年6月,無錫的榮宗敬、榮德生兄弟在上海閘北的光復(fù)路上建起福新三廠。至此,沿蘇州河,一字排開了四家榮家面粉廠,其高聳的煙囪日日濃煙滾滾,機器的軋軋聲晝夜不絕,蘇州河里運麥裝面的船只更是川流不息,景象已是十分壯觀。隨著歐戰(zhàn)爆發(fā),歐洲工業(yè)停滯,面粉軍需卻暴增,中國面粉以價格低廉、產(chǎn)量可觀而一躍成為全球新出現(xiàn)的采購市場,榮家的“兵船”牌面粉遠銷到歐洲和南洋各國,因質(zhì)量穩(wěn)定,它成了中國面粉的“標(biāo)準(zhǔn)面”。
在面粉上陡成霸業(yè)的同時,榮家的棉紗工廠竟也同步急進。
1914年,榮宗敬在上海郊外的周家橋選址,開建申新紗廠,購英制紡機36臺,投產(chǎn)開工后,正趕上歐戰(zhàn)期間的需求饑渴,上海的棉紗價格大漲,從每件90余兩狂漲到200兩,出現(xiàn)了“一件棉紗賺一個元寶”的暴利景象,申新在開工后的三年里,棉紗產(chǎn)量從3584件增加到9811件,棉布產(chǎn)量從2.9萬匹增加到12.8萬匹,盈利更是驚人,三年增長十余倍。
榮家兄弟在這些年所取得的成就,是新一輪工業(yè)化浪潮的縮影。除了面粉、棉紗之外,幾乎所有的生產(chǎn)資料和消費品都在戰(zhàn)爭中需求大增,以有色金屬鎢為例,1913年每磅價格為7.42美元,到1916年就漲到25.33美元,用于軍備的皮革、羊毛以及英國軍人大量消費的紅茶等等,都是戰(zhàn)時緊俏品,中國成了原料的大供應(yīng)商。
銀元與票號
1914年2月,在張謇和梁士詒等人推動下,北京政府鑄造了民國統(tǒng)一的銀幣,這是中國走向幣制統(tǒng)一的第一步,這款銀元采用的是袁世凱的大人頭,因此被民間稱為是“袁大頭”。由于鑄造質(zhì)量好、含銀量較高,“袁大頭”在1949年之前一直是最受歡迎的硬通貨幣。
戰(zhàn)爭加速了各國的貨幣鑄造量,白銀需求大增,在1914年,每一盎司白銀為0.56美元,到1919年就上升到了1.12美元,作為一個傳統(tǒng)的“白銀帝國”,中國因此大受其利,據(jù)美國商業(yè)部的一份報告,1917年的7000萬中國銀元就足夠償付上一年所要付的一億元債款,這大大增強了中國貨幣在國際市場上的購買力。
在金融業(yè)復(fù)蘇及日漸融入全球化的同時,傳統(tǒng)的金融業(yè)態(tài)則面臨滅頂之災(zāi)。1914年10月,天津《大公報》刊出了一條轟動中國商界的大新聞,“天下票號之首”日升昌宣布破產(chǎn)。報道描述道:“彼巍巍燦爛之華屋,無不鐵扉雙鎖,黯淡無色;門前雙眼怒突之小獅,一似淚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前日北京所傳,倒閉之日升昌,其本店聳立其間,門前當(dāng)懸日升昌金字招牌,聞其主人已宣告破產(chǎn),由法院捕其來京矣。”
晉商沒落之后,中國的金融中心從平遙縣城的青石板大街南移至十里洋場的上海。穿馬褂的票號日漸式微,著西裝的銀行取而代之。
范旭東:告別“食土民族”
1914年冬天,31歲的青年人范旭東獨自一人到了天津塘沽。這里的海灘邊鹽蛇遍地,如冰雪一般,無邊無際。他目睹此景,顯得有點激動。日后他對伙伴說,“一個化學(xué)家,看到這樣豐富的資源,如果還沒有雄心,未免太沒有志氣了。”
范旭東早年被家人送到日本讀書,一個日本校長對他說:“俟君學(xué)成,中國早亡矣。”此言,刺激了他的一生。從京都帝國大學(xué)理學(xué)院應(yīng)用化學(xué)系畢業(yè)后,他隨即回國,立志于復(fù)興中國的鹽業(yè)。自秦漢以來,中央政府就對鹽、鐵實行專營,中國人雖然守著豐富的海洋資源,食用的鹽卻仍是土法制作的粗鹽,效率低,純度低,并且含有很多有害物質(zhì)。當(dāng)時,西方發(fā)達國家已明確規(guī)定,氯化鈉含量不足85%的鹽不許用來做飼料;而在中國許多地方仍用氯化鈉含量不足50%的鹽供人食用。因此,有西方人譏笑中國是“食土民族”。實際上,制作精鹽并不難,成本也不高,只是中國當(dāng)時缺少化工人才,無人涉足。精鹽市場,長期被英商和日商壟斷。
范旭東在天津創(chuàng)辦久大精鹽公司,股本5萬元。他在塘沽的漁村開始研制精鹽,很快令純度達到90%以上,久大以海灘曬鹽加工鹵水,用鋼板制平底鍋升溫蒸發(fā)結(jié)晶,生產(chǎn)出中國本國制造的第一批精鹽,范旭東親筆設(shè)計了一個五角形的商標(biāo),起名“海王星”。
抵制日貨運動
一戰(zhàn)開打后,日本乘機爭奪中國利益,1914年8月,它出兵占領(lǐng)德國在中國的勢力范圍——山東半島。這一事件成為當(dāng)年度最嚴重的涉華國際事件,從而引發(fā)了一場猛烈的抵制日貨運動。
從數(shù)據(jù)看上,日本商業(yè)勢力的涌入是十分猛烈的,在一戰(zhàn)前夕,日本商品占中國進口商品總額的15·5%,到1919年已經(jīng)猛然上升到29.9%,僅紗錠一項,就從11萬枚增加到33.2萬枚,上升三倍。自1917年開始,日本取代英國成為最大的貿(mào)易商,而且成為對華工業(yè)設(shè)備的主要銷售者。更讓中國人難堪的是,日本商品在傳統(tǒng)的“中國貨”上也取得了優(yōu)勢,日本茶葉、日本絲綢的國際貿(mào)易額相繼都超過了同類的中國商品,成為最大的出口國,甚至在中國市場上,日本貨也成了頗受歡迎的時髦商品。除了經(jīng)濟上的咄咄逼人之外,日本對中國領(lǐng)土和政治特權(quán)要求也一點沒有放松。
2015年1月,日本對袁世凱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條》,要求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quán)益,準(zhǔn)許日本修建自煙臺連接膠濟路的鐵路等諸多經(jīng)濟特權(quán)。這些條款立即遭到各界的強烈抗議。隨之,各地紛紛爆發(fā)了日貨抵制運動。抗議集會此起彼伏。商人拒賣日貨,人人要用國貨。從此,抵制日貨成為中國社會的常態(tài),中國將日本牢牢地定位為頭號政治和經(jīng)濟敵人。
20年前的那個“吳英”
從鄭樂芬到吳英,如果不從制度的角度來進行思考,那么,拯救必?zé)o從談起,悲劇將繼續(xù)發(fā)生。
2012年1月18日,吳英非法集資詐騙案二審判決,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維持對被告的死刑判決。在過去的幾周內(nèi),輿論界及法律界出現(xiàn)了一股為吳英求情的熱潮。
吳英案之所以引起如此反響,表明她已經(jīng)化作一個“符號”,成為人們呼吁金融產(chǎn)業(yè)開放的導(dǎo)火線。這里,講述一個20年前、已經(jīng)被剝奪了生命的“吳英”。
隨著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迅猛發(fā)展,民間對資本的需求空前高漲,然而國營的金融機構(gòu)完全無法提供任何服務(wù)。在1984年,溫州蒼南出現(xiàn)了建國之后的第一家民間錢莊——方興錢莊。遺憾的是,它的招牌僅僅掛出一天,就被當(dāng)?shù)氐霓r(nóng)業(yè)銀行以違反國家規(guī)定為由摘除了。從此,民間金融在毫無制度約束的前提下,轉(zhuǎn)入地下。從1985年之后,溫州九縣兩區(qū)30萬人卷入民間借貸活動,涉及發(fā)生額達12億元之巨。由于無法可依、地方政府不知管控,便很快轉(zhuǎn)化為惡性的高利貸事件,當(dāng)?shù)厝朔Q“抬會”。到1986年春夏,資金鏈突然斷裂,各地相繼爆出會主潛逃的消息,抬會體系瞬間雪崩。短短3個月中,溫州全市有63人自殺,200人潛逃,近1000人被非法關(guān)押,8萬多戶家庭破產(chǎn)。
這是1949年迄今,最為惡劣的金融破產(chǎn)事件,地方政府開始抓捕和通緝那些知名的會主,以殺一儆百的方式來平息民憤。一位33歲、名叫鄭樂芬的婦女被當(dāng)成罪大惡極的首犯,判決死刑。
鄭樂芬是永嘉的一個家庭婦女。據(jù)熟悉的人回憶,鄭為人熱情大方,沒讀過幾年書,結(jié)婚后就在家里做點針頭線腦的小生意。當(dāng)抬會風(fēng)暴刮起的時候,頭腦靈活、人緣頗佳的鄭樂芬很自然地成了當(dāng)?shù)氐囊粋€小會主。后來發(fā)現(xiàn),溫州抬會的會主八成以上是由像鄭樂芬這樣的文化程度不高甚至是文盲的農(nóng)村婦女擔(dān)當(dāng)?shù)摹@一事實在后來的20多年仍然如此。
鄭后來在供詞中描述當(dāng)時的情景說,“錢收進來,先在墻兩頭放著,到了晚上一間房子已全部堆滿錢,只有封門派民兵舉刺刀看門。人們喊著要入會,把大疊的錢扔進來。”鄭樂芬所主持的抬會規(guī)模,在當(dāng)時屬于中等,她共發(fā)展了427人入會,收入會款6200萬元,支付會員會款6010萬元。
令人驚奇的事情是,鄭樂芬一直要拖到5年后的1991年9月才被正式處決,在這段時間里,浙江法律界對死刑判決進行了激烈的爭論。
鄭樂芬的辯護律師認為,抬會本身是一個騙局,鄭氏主觀上是以非法占有會員的錢財為目的,應(yīng)定性為詐騙罪,以此論刑,鄭氏罪不當(dāng)死。
而法院是以投機倒把的罪名判定死刑的。從法院提供的證據(jù)來看,鄭樂芬并無詐騙錢財?shù)男袨椋c會員訂立合約,雙方對抬會的經(jīng)營方式都是明知和認同的。因此,法院認為,被告之罪重點是侵犯了國家金融管理制度,應(yīng)定投機倒把罪,根據(jù)情節(jié),可處極刑。
就在鄭樂芬被處決的那年,在距離溫州600公里之外的金華東陽,10歲的鄉(xiāng)下姑娘吳英正背著書包行走在去小學(xué)的土路上。她不會料到的是,20年后,她將步鄭樂芬之后塵,成為另一起民間金融事件的犧牲品。
從鄭樂芬到吳英,如果不從制度的角度來進行思考,那么,拯救必?zé)o從談起,悲劇將繼續(xù)發(fā)生。
1月25日,著名大律師、八旬老人張思之發(fā)表了一份致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的公開信。在信中,張思之重點表達了兩個觀點:其一,吳英所集資金大多流入當(dāng)?shù)貙嶓w領(lǐng)域,屬合法經(jīng)營范疇,故無詐騙之行為;其二,“縱觀金融市場呈現(xiàn)的復(fù)雜現(xiàn)狀,解決之道在于開放市場,建立自由、合理的金融制度,斷無依恃死刑維系金融壟斷的道理”。
這兩條分別從法律和制度層面對吳英案做出了剖析,尤其是第二條,當(dāng)是案件紛議之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