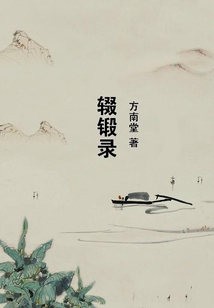
輟鍛錄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有詩人之詩,有學人之詩,有才人之詩。
才人之詩,崇論閎議,馳騁縱橫,富贍標鮮,得之頃刻。然角勝於當場,則驚奇仰異;咀含於閒暇,則時過境非。譬之佛家,吞針咒水,怪變萬端,終屬小乘,不證如來大道。
學人之詩,博聞強識,好學深思,功力雖深,天分有限,未嘗不聲應律而舞合節,究之其勝人處,即其遜人處。譬之佛家,律門戒子,守死威儀,終是鈍根長老,安能一性圓明!
詩人之詩,心地空明,有絕人之智慧;意度高遠,無物類之牽纏。詩書名物,別有領會;山川花鳥,關我性情。信手拈來,言近旨遠,筆短意長,聆之聲希,咀之味永。此禪宗之心印,風雅之正傳也。
故作詩未辨美惡,當先辨是非。有出入經史,上下古今,不可謂之詩者;有尋常數語,了無深意,不可不謂之詩者。會乎此,可與入詩人之域矣。
詩必言律。律也者,非語句承接,義意貫串之謂也。凡體裁之輕重,章法之短長,波瀾之廣狹,句法之曲直,音節之高下,詞藻之濃淡,於此一篇略不相稱,便是不諧於律。故有時寧割文雅,收取俚直,欲其相稱也。杜子美云:“老支漸于詩律細”。嗚乎!難言之矣。
未有熟讀唐人詩數千百首而不能吟詩者,未有不讀唐人詩數千百首而能吟詩者。讀之既久,章法、句法,用意、用筆,音韻、神致,脫口便是,是謂大藥。藥之不效,是無詩種,無詩種者不必學詩。藥之必效,是謂佛性,凡有覺者皆具佛性,具佛性者即可學詩。
《三百篇》而下,由漢、魏以迄六朝,代有傳詩,而余獨以唐人為歸:“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古云:“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此說詩之妙諦也,而未足以盡詩之境。如杜子美“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白樂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韓退之《拘幽操》,孟東野《游子吟》,是非有得於天地萬物之理,古圣賢人之心,烏能至此?可知學問理解,非徒無礙於詩,作詩者無學問理解,終是俗人之談,不足供士大夫之一笑。然正有無理而妙者,如李君虞“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劉夢得“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李義山“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不重來”。語圓意足,信手拈來,無非妙趣。可知詩之天地,廣大含宏,包羅萬有,持一論以說詩,皆井蛙之見也。
作詩不能不用故實,眼前情事,有必須古事襯托而始出者。然用事之法最難,或側見,或反引,或暗用,吸精取液,於本事恰合,令讀者一見了然,是為食古而化。若本無用意處,徒取經史字面,鋪張滿紙,是侏儒自丑其短,而固高冠巍屐,綠衣紅裳,其惡狀愈可僧也。
“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毋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此司空文明送別之作也。僅二十字,情致綿渺,意韻悠長,令人咀含不盡。似此等詩,熟讀數十百篇,又何患不能換骨!
詩中點綴,亦不可少,過於枯寂,未免有妨風韻。然須典切大雅,稍涉濃縟,便爾甜俗可厭。吾最愛周繇《送人尉黔中》云:“公庭飛白鳥,官俸請丹砂”。亦何雅切可風也!
點綴與用事,自是兩路。用事所關在義意,點綴不過為顏色豐致而設耳。今人不知,遂以點綴為用事,故所得皆淺薄,無大深意。
今日晨起,讀元次山《舂陵行》,悲惻者久之。日運下趨,今人不獨學問不如古人,性情亦大懸絕。安得如結者百十輩,布滿天下耶?
唐人最善於脫胎,變化無跡,讀者惟覺其妙,莫測其源。如謝惠連《搗衣》云:“腰帶準疇昔,不知今是非。”張文昌《白纻詞》則云:“裁縫長短不能定,自持刀尺向姑前。”裴說《寄邊衣》云:“愁捻銀針信手縫,惆悵無人試寬窄。”非皆本於謝語乎?又金昌緒“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岑嘉州則脫而為“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至家三拜先生,則又從岑詩翻出云:“昨日草枯今日生,羈人又動故鄉情。夜來有夢登歸路,未到桐廬已及明。”或觸影生形,或當機別悟,唐人如此等類,不可枚舉。解得此法,《五經》、《廿一史》皆我詩心也。
李遐叔《吊古戰場文》:“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悁悁心目,寢寐見之。”陳陶則二十四字化而為十四字,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里人。”可謂猶龍之筆。
作詩最忌敷陳多於比興,詠嘆少於發揮,是即南北宗所由分也。
詩人體物入微,真能筆通造化。喬知之《長信宮樹》云:“馀花鳥弄盡,敗葉蟲書遍。”沈佺期《芳樹》云:“啼鳥弄花疏,游蜂飲香遍。”偶一歌詠,一則秋氣蕭條,一則春光明媚,即此可悟用字法。
詠物詩不宜多作,用意用筆俱從雕刻尖巧處著想,久之筆仗纖碎,求一二高視闊步之語,昭彰跌宕之文,不可得矣。
詠物題極難,初唐如李巨山多至數百首,但有賦體,絕無比興,癡肥重濁,止增厭惡。惟子美詠物絕佳,如詠鷹詠馬諸作,有寫生家所不到。貞元、大歷諸名家,詠物絕少。唯李君虞《早燕》云:“梁空繞復息,檐寒窺欲遍”,直是追魂攝魄之訓。馀無所見。元和以後,下逮晚唐,詠物詩極多,縱極巧妙,總不免描眉畫角,小家舉止,不獨求如杜之詠馬詠鷹不可得見,即求如李之《早燕》大方而自然者,亦難之難矣。
白樂天歌行,平鋪直敘而不嫌其拖踏者,氣勝也;張文昌樂府,急管繁弦而不覺其跼蹐者,趣勝也。
古人有一二語獨臻絕勝,不惟後之作者不能仿佛,即其全集中亦不復再見,是蓋一時興會所致,不能強得也。然是皆寫景則然,若言情述事,非苦思不得,果能到思路斷絕處,自有奇語。
人情真至處,最難描寫,然深思研慮,自然得之。如司空文明“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李君虞“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皆人情所時有,不能苦思,遂道不出。陳元孝云:“詩有兩字訣:曰曲,曰出。”觀此二聯,益知元孝之言不謬。
“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太液滄波遠,長楊高樹秋”,如此寫景,豈晚唐人所得夢見?
高適、李頎不獨七古見長,大段氣體高厚,即今體亦復見骨格堅老,氣韻沉雄。余最愛李頎一篇云:“青青蘭艾本殊香,察見泉魚固不祥。濟水至清河自濁,周公大圣接輿狂。千年魑魅逢華表,九日茱萸作佩囊。善惡死生齊一貫,衹應斗酒任蒼蒼。”眼中胸中何等寬闊,可謂見得到說得出。
作詩以意為主,而句不精煉,妙意不達也;煉句以達為主,而音不合節,雖達非詩也。然則音韻之於詩亦重矣哉!今人不知,誤以高響為音韻,其失之更遠。
音韻之說,消息甚微,雖千言萬語,不能道破,惟熟讀唐人詩,久而自得。
《赴奉先縣五百字》,當時時歌誦,不獨起伏關鍵,意度波瀾,煌煌大篇,可以為法,即其中琢句之工,用字之妙,無一不是規矩,而音韻尤古淡雅正,自然天籟也。
唐詩至元和間,天地精華,盡為發泄,或平,或奇,或高深,或雄直,旗鼓相當,各成壁壘,令讀者心忙意亂,莫之適從。就中惟昌谷集不知其妙處所在,良由余之性所不近也。
能令百世而下,讀其詩可想其人,無論其詩之發於誠與偽,而其詩已足觀矣。
儲光羲《田家雜詠》云:“見人乃恭敬,曾不問賢愚。雖若不能言,心中亦難誣。”非浮沉玩世用拙保身之士乎?錢起《罷章陵令山居》第二首云:“丘壑趣如此,暮年始棲偃。賴遇無心雲,不笑歸來晚”。非備嘗世味甘心泉石之士乎?至韋蘇州、元次山詩,不必考其本末,辨其誠偽,一望而信其為悱然忠厚、淡泊近道之君子也。韓退之、呂溫詩,不必論其時世,究其言行,一望而知其為熱中躁進、好事取為之人也。其不可掩如此。
詩有語意相同而工拙大相遠者,如賈長江“走月逆行雲”,亦可為形容刻劃之至矣。試與韋蘇州“喬木生夏涼,流雲吐華月”較之,真不堪與之作奴。
賀黃公云:“東坡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此言論畫,猶得失參半,論詩則深入三昧。”旨哉斯言,是可與入道者也。
體裁惟七律最難,須五十六字無一牽湊,平近而不庸熟,清老而不俚直,高響而不叫號,排宕而不輕佻,尤忌刪去兩字便可作五言詩讀。欲除諸病,惟熟讀少陵及大歷諸名家,則得之矣。
晚唐自應首推李、杜,義山之沉郁奇譎,樊川之縱橫傲岸,求之全唐中,亦不多見,而氣體不如大歷諸公者,時代限之也。次則溫飛卿、許丁卯,次則馬虞臣、鄭都官,五律猶有可觀,外此則邾、莒之下矣。
溫飛卿五律甚好;七律惟《蘇武廟》、《五丈原》可與義山、樊川比肩。五七古、排律,則外強中乾耳。
立題最是要緊事,總當以簡為主,所以留詩地也。使作詩義意必先見於題,則一題足矣,何必作詩?然今人之題,動必數行,蓋古人以詩詠題,今人以題合詩也。
詩中不宜有細注腳。一題既立,流連往復,無非題中情事,何必更注?若云時事之有關系者,不便直書題中,亦不應明注詩下;且時事之有關系者,目前人所共知,異代史傳可考,又何必注?若尋常情事,無關重輕,而於題有合者,非注不明;既云於題有合,自應一目了然,又何須注?若云於題無甚關合,注解正所以補題,此即牽強湊泊之謂也,烏足云詩?
用事選料,當取諸唐以前,唐以後故典,萬不可不入詩,尤忌以宋、元人詩作典故用。
康熙己卯、庚辰以後,一時作者,古詩多學韓、蘇,近體多學西昆,空疏者則學陸務觀,浸淫濡染,三十年其風不變。究之徒有其貌,古人精神所在,正未嘗窺測及之。然風雅道喪,猶未極也。近有作者,謂《六經》、《史》、《漢》皆糟粕陳言,鄙三唐名家為熟爛習套,別有師傳,另成語句,取宋、元人小說部書世所不流傳者,用為枕中秘寶,采其事實,摭其詞華,遷就勉強以用之,詩成多不可解。令其自為疏說,則皆逐句成文,無一意貫三語者,無一氣貫三語者。乃僴然自以為博奧奇古,此真大道之波旬,萬難醫藥者也。但愿天地多生明眼人,不為其所迷惑,使流毒不遠,是厚幸矣。
古人於事之不能已於言者,則托之歌詩;於歌詩不能達吾意者,則喻以古事。於是用事遂有正用、側用、虛用、實用之妙。如子美《荊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云:“萬歲持之護天子,得君亂絲為君理。”此側用法也。劉禹錫《葡萄歌》云:“為君持一斗,往取涼州牧。”此虛用法也。李頎《送劉十》云:“聞道謝安掩口笑,知君不免為蒼生。”此實用也。李端《尋太白道士》云:“出游居鶴上,避禍入羊中。”此正用也。細心體認,得其一端,已足名家,學之不已,何患不抗行古人耶!
孟東野集不必讀,不可不看。如《列女操》、《塘下行》、《去婦詞》、《贈文應道月》、《贈鄭魴》、《送豆盧策歸別墅》、《游子吟》、《送韓愈從軍》諸篇,運思刻,取逕窄,用筆別,修詞潔,不一到眼,何由知詩中有如此境界耶?
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者,非奇險怪誕之謂也,或至理名言,或真情實景,應手稱心,得未曾有,便可震驚一世。子美集中,在在皆是,固無論矣。他如王昌齡“奸雄乃得志”一篇云:“一人計不用,萬里空蕭條。”千古而下讀之,覺皇甫酈之論董卓,張曲江之判祿山,李湘之策龐勛,古來恨事,歷歷在目。尋常十字,計關宗社,非驚人語乎?李太白之“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以史中敘事法用之於詩,但覺安祥妥適,非驚人語乎?劉禹錫之“風吹落葉填宮井,火入荒陵化寶衣”,李商隱之“於今腐草無螢火,終古垂楊有暮鴉”,不過寫景句耳,而生前侈縱,死後荒涼,一一托出,又復光彩動人,非驚人語乎?韋應物之“欲持一瓢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高簡妙遠,太音聲希,所謂舍利子是諸法空相,非驚人語乎?若李長吉,必藉瑰辭險語以驚人,此魔道伎倆,正仙佛所不取也。
要之作詩至今日,萬不能出古人范圍,別尋天地。唯有多讀書,镕煉淘汰於有唐諸家,或情事關會,或景物流連,有所欲言,取精多而用物宏,脫口而出,自成局段,入理入情,可泣可歌也。若舍此而欲入風雅之門,則非吾之所得知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