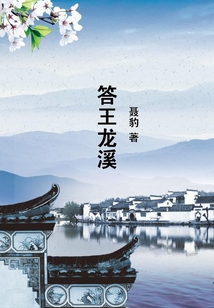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來書云:顏子不遠復,正是德性之知,孔門致知之學,所謂復以自知不學不慮之良知也。子貢務于多學,以億而中,與顏子正相反,顏子沒而圣學亡。子貢學術易于湊泊,積習漸染,至千百年而未已也。先師憂憫后人,將此兩字信手拈出以承千圣絕學,誠不得已之苦心。世之儒者,反哄然指以為異而非之,夜光之珠,視者××,亦無怪其然也。
克己復禮,三月不違,是顏子不遠于復,竭才之功也。復以自知,蓋言天地之剛,復全于我,而非群陰之所能亂。卻是自家做得主宰定,故曰自知猶自主也。子貢以多識億中為學,誠與顏子相反,至領一貫之訓,而聞性于天道,當亦有見于具足之體,反而筑室,獨居三年,其中之所存亦苦矣,要未可以易視之也。先師良知之教,本于孟子。孟子言孩提之童,不學不慮,知愛知敬,蓋言其中有物以主之,愛敬則主之所發也。今不從事于所主,以充滿乎本體之量,而欲坐享其不學不慮之成,難矣!
來書云:仁者與物同體,息為化生之元,入圣之微機也。夫氣體之充而塞乎天地者也,氣之靈為良知。孟子論日夜所息,平旦虛明之氣即是靈氣。造化無停機,才止息耶,即有生息之義。靜專動直,靈之馭氣也,靜翕動辟,氣之攝靈也。是以大生廣生,動靜之間,惟一息耳。邵子亦謂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醫家以手足痿痹為不仁,蓋言靈氣有所不貫也。又以呼吸定息為接天地之根,蓋言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也。人能從此一息保合愛養,不為旦晝之所梏亡,終日一息也。日至月至,日月一息也。三月不違,三月一息也。九年不反,九年一息也。推而至于百千萬年,百千萬年一息也。是為至誠無息之學。
仁是生理,亦是生氣,理與氣一也。但終當有別。告子曰:生之謂性。亦是認氣為性,而不知系于所養之善否。杞柳、湍水、食色之喻,亦以當下為具足。勿求于心,勿求于氣之論,亦以不犯做手為妙悟。孟子曰:茍得其養,無物不長,茍失其養,無物不消。是從學問上驗消長,非以天地見成之息,冒認為己有而息之也。仁者與物同體,亦惟體仁者而后能與物同之。馭氣攝靈與定息以接天地之根諸說,恐是養生家所秘,與吾儒之息未可強而同。而要以收斂為主,則一而已。一動一靜,為天地人之至妙,邵子是從易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看得來,無以繼善成性、顯仁藏用、盛得大業、生生不已,而終之以陰陽不測之神,即邵子至妙至妙之嘆。陰陽迭運,動靜相生,循環無端,而天地日月水火土石人鬼禽獸草木皆從生滅摩蕩中成象成形,而莫知誰之所使,故曰至妙至妙者也。如曰氣之靈為良知,即謂氣之理為良知亦可。氣有升降,便有動靜,而謂良知無未發之時,豈別有說乎?
來書云:性為人之生理,息則其生生之機也。佛氏以見性為宗,吾儒之學亦以見性為宗。致良知,見性之宗也。性定則息定,而氣自生生,故曰是集義所生者也,盡性以至于命也。若曰息則氣定,則氣命于性,而歸于虛寂,則將入于禪定,非致知之旨矣。
息有二義:生滅之謂也。攻取之氣息,則湛一之氣復,此氣化升降之機,無與于學問也。子之所謂息者,蓋主得其所養則氣命于性,配義與道,塞乎天地,生生之機也。傳曰:虛者氣之府,寂者生之機。今以虛寂為禪定,謂非致知之旨,則異矣。佛氏以虛寂為性,亦以覺為性,又有皇覺、正覺、圓覺、覺明、明覺之異,佛學養覺而嗇于用時,儒用覺而失所養,此又是其大異處。
來書云:息之一字,范圍三教之宗。老氏謂之谷神玄牝,其息深深。蒙莊氏謂之六月息,釋氏謂之反息還虛,吾儒則謂之向晦入晏息,邵子謂之復媾之幾,天地之呼吸也。是息,先天地而生,后天地而存,人能明此一息,是為天地氤氳,萬物化生,一息通于今古。平旦之氣,有不足言者矣。
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澤中有雷,君子以向晦入晏息。蓋亦康衢,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謠。消息盈虛,天行也,君子尚消息盈虛,亦只是隨時之義。申申夭夭,休休蕩蕩,便是夫子息境。若是精神向里收斂,亦便是時時息,更無晝旦之別。其以息為范圍三教之宗,而攙和二氏及養生家之言以神其說,疑××之×也。
來書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道誼未嘗不利,未嘗無功,但有計謀之心,則為有所為而為,即入于功利。先師所謂一心在根上培灌,不作枝葉花實之想,但得此根生意不息,不怕無枝葉花實,此是對癥之藥,所當時時勤服者也。
物上求正,隨在致此良知,周乎物而不過云云,恐不免有功利心。君子以成德為行與德修罔覺,更無些子功利意,卻別是一乾坤也。無妄六二之象曰:不耕獲,未富也。言耕而獲,便是功利,惟耕而不計獲者,方是一心在根上培灌,不作枝葉花實之想。其間特毫厘之差,不知尊兄以何者為根,亦以何者為枝葉花實。格物是致知之功,隨在致此良知,周乎物而不過,謂是為培灌根乎?亦只是培灌枝葉花實,便是培貫根也?鄙人之見,竊謂心體是根,事為是枝葉,事為之得其當處是花實。致虛守寂以養乎未發之中,而于感應之變化聽其自然,人力無所與也,卻是一心在根上培灌,不作枝葉花實之想。
來書云:吾人今日正當潛龍之學,不易乎世,不成乎名。故君子立心為己,莫先于淡,淡是入德之基。吾人潛不久,淡不下,只是世情心未忘。此是最初發軔第一步不可以不深省也。
君子黯然之學,便是潛龍之學。潛則含晦章美,專于內養以成其德,不見其有外,見之美,泊乎其淡也。潛故淡耳,非有心于淡也。故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謂是為發軔第一步是也。但前此既謂良知者,千圣之絕學,范圍三教之宗,又謂息之一字,范圍三教之宗,又謂千古圣學,只在幾上用功,又以無前后、內外為千圣斬關第一義,又以乾知大始為渾沌初開第一竅,又謂千古道脈,只在虞廷道心之微,茲又以發軔第一步歸之潛與淡,不知是一了百當耶?抑自有前后內外之可言也?
龍溪云:寂之一字,千古圣學之宗,感生于寂,寂不離感。舍寂而緣感,謂之逐物,離感而守寂,謂之泥虛。夫寂者,未發之中,先天之學也,未發之功只在發上用,先天之功只在后天上用。明道云:“此是日用本領工夫,卻于已發處觀之。”康節《先天吟》云:若識先天無個字,后天須用著工夫。可謂得其旨矣。
夫未發之功只在發上用,先天之功只在后天上用,至引程邵語以附會之,只緣尊兄站得地步高,故敢如此立說。乃程邵之意,實非兄之意也。程子曰:未發之中,本體自然敬以持之,使此氣息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自然中節。此是日用本領工夫。其曰卻于已發處觀之者,蓋所以察識其端倪,以致夫擴充之功,一有不中,則心之為道或幾乎息矣。中是察識底標的,擴充底圣胎。故曰:不如且只道敬。又曰:敬而無失便是中。邵子詩意謂識得先天是個至虛至無之體,則奉天時行,無所作為以塞之,便是后天工夫。不然,何別有一首云:一片先天是太虛,當其無事見真腴,直從宇泰收功后,始信人間有丈夫。無事真腴,宇泰收功,將屬之先天乎?后天乎?果在發上用乎?抑自有未發之功乎?寂之一字,兄信之深矣。故曰寂是未發之中,先天之學。夫有未發之中,便有發而中節之和,有先天之學,便有奉天時行之用。感生于寂,歸寂以通感,已無復可疑。前既以多學億中之助為后天之知,后天之功,亦只是去其學億之病,惟復以奉天時行為功也。如以奉天時行為功,則學在推崇先天至矣。前所引程邵之言,無亦斷章太過乎?
龍溪云:先天是心,后天是意,至善是心之本體。心體本正,才正心便有正心之病,才要正心便屬意了。故曰:欲正其心先誠其意。猶云舍了誠意,更無正心工夫可用也。
其曰心體本正,才要正心,便有正心之病,此慈湖之言,便是慈湖之學,不有孔孟之公案乎?曰洗心,曰存心,曰養心,而二氏亦有修心、明心之語。自古圣賢未聞以此為心病者。才說正心便屬意,猶俗論云:才說止至善便屬物,才說戒懼便屬睹聞。不知正是正個甚的,止是止個甚的,戒懼是戒懼個甚的。傳謂有所忿嚏則不得其正,明意之不可有也。心不在焉,則視聽言動皆失其職,明心之不可不正也。
龍溪云:良知是寂然之體,物是所感之意,用則其寂感所乘之機也。知之與物而復先后可分,故曰致知在格物。致知工夫在格物上用,猶云明德工夫在親民上用,離了親民更無明德之學也。
來云良知是寂然之體,是以良知為主腦,而以寂感為兩股,故曰用則寂感所乘之機也。疑與經傳之意太別。“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此程子之言也。“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此朱子之言也。今曰良知是寂然之體,不知寂然上又有一體也?“致知工夫在格物上用,明德工夫在親民上用”,先師曾有是言,特欲發明萬物一體之學,與大學本意微有間。
龍溪云:良知是天然之則,格者,正也,物即事也。格物云者,致此良知之天則于事事物物也,物得其則謂之格,非于天則之外別有一段格物之功也。
來云:“”信若是,則工夫在致知,不在格物矣。況致之一字,亦非推此及彼之意,即致廣大之致也。充滿乎本體之量而不以一毫意欲自蔽,則自此而發者自然中節。如孩提之愛敬,又何待于推乎?
龍溪云:既如公以兵器喻學,心猶銃炮,硝磺之內蘊,未發之寂也。而其所蘊之真否,須于所發之激射察之,以益求其所蘊之真,固未嘗狃于激射而忘其有事于硝磺也。引線之火,即觸硝磺而達于激射之機也。然非所發之激射,則其所蘊之硝磺亦我從而致其察矣。
龍溪云:前謂未發之功只在發上用者,非為矯強矜飾于喜怒之來,以制之于外也。皆是天則,即所謂未發之中也。中節云者,循其天則而不過也。養于未發之豫,先天之學是矣。后天而奉天時者,乘天時行,人力不得而與。曰奉曰乘,正是養之之功。若外此而別求所養之豫,即是遺物而遠于人情,非在塵出塵作用,與圣門復性之旨為有聞(當為“間”)矣。
古之所謂豫者,蓋言事有前定,非臨時補湊。蓋“有物先天地”,言先有此物而后有天地也。“無形本寂寥”,言其至虛至無也。“能為萬象主”,言萬物統體一太極也。“不逐四時凋”,言其不垢不凈、不生不死,真常得性也。
龍溪云:未應非先,已應非后,即寂而感行焉,即感而寂存焉,正是合本體之工夫。無時不感,無時不歸于寂也。若以此為見成而未及學問之功,不知學問之功,又將何如用也?寂非內而感非外。蓋因世儒以寂為內,感為外,故言此以見寂感無內外之學。非故以寂為外,以感為內,而于內外之間,別有一片地界可安頓也。良知之前無未發者,良知即是未發之中,若復求未發,則所謂沉空也。良知之外無已發者,致此良知即是發而中節之和,若別有已發,即所謂依識也。語意似亦了然。
妄意尊見,諺謂夜半吃魚兒,無頭無尾。甚者謂物亦無內外,以蓋其波。未應非先,已應非后,本是言心體,尊兄必以說工夫。
龍溪云:愚則謂良知在人,本無污壞,雖昏蔽之極,茍能一念自反,即得本心。譬之日月之明,偶為云霧所翳,謂之晦耳,云霧一開,明體即見,原未嘗有所傷也。此原是人人見在具足,不犯做手本領工夫。
“良知在人,本無污壞,雖昏蔽之極,茍能一念自反,即得本心。”是則有是理,特言之太易耳。夫以昭昭之多而概廣大無窮之體,能免望洋之嘆、管窺之譏乎?來謂“日月之明,偶為不犯做手本領工夫。”云云,此又是論道理。非困心衡慮,百倍其功而能庶幾于仁智者鮮矣。若謂一念自反,為進為之端,則可也。
龍溪云:乾知大始,大始之知,混沌初開之竅,萬物所資以始,知之為義本明,不須更訓主字。
如公等只以一知字盡天地古今之變,又恐過于易簡者也。
龍溪云:公謂“”,似于先師致知之旨,或有所未盡契也。良知即未發之中,原是不睹不聞,原是莫見莫顯。明物察倫,性體之覺,由仁義行,覺之自然也。自然之覺即是虛即是寂,即是無形與聲,即是虛明不動之體,即為易之蘊。
龍溪云:良知者,自然之覺,微而顯,隱而見,所謂幾也。良知之實體為誠,良知之妙用為神,幾則通乎體用而寂感一貫。
龍溪云:先師良知之說,仿于孟子不學不慮,乃所為自然之良知也。自然之良,即是愛敬之主,即是寂,即是虛,吾人今日致知之學,不能入微,未免攙入意見知識,無以充其自然之良,則誠有所不免,若謂自然之良未足以盡學,復求有物以主之,且謂覺無未發,亦不可以寂言,將使人并其自然之覺而疑之。
前既以誠為良知之實體,實體便是主物。必實體呈露而后可以言自然之良,而后有不學不慮之成。茲不求自然之良于實體之充,則所謂良者,卒成一個野狐精,其與自然之覺遠矣。既曰覺,便是發,感于物而后有覺。惟擴充仁體,則四端發見始有火燃泉達之機。
龍溪云:空空原是道體。
今謂鄙夫的空空與圣人同,即王汝止謂滿街的是圣人之說,徒以長傲而侮圣也。
龍溪云:良知者,心之靈也,理一而已,性則理之凝聚,心則凝聚之主宰,意則主宰之發動,知則明覺之體,而物則其感應之用也。寂是心之本體,不可以時言,時有動靜,寂則無分于動靜。自然之知,即是未發之中。
尊兄所傳,恐皆夜半密語,而傳習錄云云,想是為眾僧說法,非上乘所屑也。
龍溪云:仁是生理,即其化生之元,理與氣未嘗離也。人之息與天理之息原是一體。
故知幾之學,養心要矣。不得其養,而曰我之息即天地之息,謂之冒認非過也。
龍溪云:以未發為本領工夫者,致知也,發處察識端倪以致夫擴充之功者,格物也。
龍溪云:未發不與已發相對
中是性,和是情,中立而和出焉,體用一源也。
龍溪云:何思何慮,猶云思慮而未嘗有所思慮也。何思何慮正是工夫,非以效言也。
龍溪云:格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謂是為由中之學是也。但尊兄之意猶自看得歸于正三字在物上。
龍溪云:先師教人嘗曰:“至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蓋緣學者根器不同,故用功有難易。有從心體上立基者,有從意根上立基者。從心體上立基,心便是個至善無惡的心,意便是至善無惡的意,便是致了至善無惡的知,格了至善無惡的物。從意根上立基,意是個有善有惡的意,知便是有善有惡的知,物便是有善有惡的物,而心亦不能無不善之雜矣。故須格其心之不正以歸于正。
龍溪云:物是物有本末之物,不誠則無物,故曰精氣為物,是從虛無靈覺凝聚出來的,豈容輕得?
鄙以致虛守寂、充滿乎虛靈之體為致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為格物,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正與明明德于天下相照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