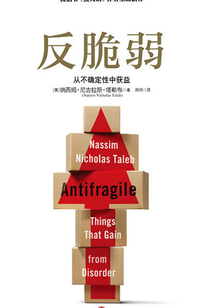最新章節
- 第74章 后記
- 第73章 結語
- 第72章 給職業戴上倫理光環(2)
- 第71章 給職業戴上倫理光環(1)
- 第70章 切身利害:反脆弱性和犧牲他人的可選擇性(5)
- 第69章 切身利害:反脆弱性和犧牲他人的可選擇性(4)
第1章 前言(1)
如何愛上風
風會熄滅蠟燭,卻能使火越燒越旺。
對隨機性、不確定性和混沌也是一樣:你要利用它們,而不是躲避它們。你要成為火,渴望得到風的吹拂。這總結了我對隨機性和不確定性的明確態度。
我們不只是希望從不確定性中存活下來,或僅僅是戰勝不確定性。除了從不確定性中存活下來,我們更希望像羅馬斯多葛學派的某一分支,擁有最后的決定權。我們的使命是馴化、主宰,甚至征服那些看不見的、不透明的和難以解釋的事物。
那么,該怎么做呢?
反脆弱性
有些事情能從沖擊中受益,當暴露在波動性、隨機性、混亂和壓力、風險和不確定性下時,它們反而能茁壯成長和壯大。不過,盡管這一現象無處不在,我們還是沒有一個詞能夠用來形容脆弱性的對立面。所以,不妨叫它反脆弱性(antifragile)吧。
反脆弱性超越了復原力或強韌性。復原力能讓事物抵抗沖擊,保持原狀;反脆弱性則讓事物變得更好。它具有任何與時俱進事物的特質:進化、文化、觀念、革命、政治制度、技術創新、文化和經濟的成功、企業的生存、美食食譜(比如,雞湯或加入一滴干邑葡萄酒的韃靼牛排),還有城市、文化、法律制度的興起、赤道雨林的生長和細菌耐藥性的增長等。反脆弱性決定了有生命的有機體或復雜體(比如人體)與無生命的機械體(比如辦公桌上的訂書機)之間的區別。
反脆弱性偏好隨機性和不確定性,這意味著——這一點非常關鍵——它也偏好錯誤,準確地說是某一類錯誤。反脆弱性有一個奇特的屬性,它能幫助我們應對未知的事情,解決我們不了解的問題,而且非常有效。讓我說得更直白些:由于有了反脆弱性,我們做的要比我們想象的更好。我寧愿做愚鈍但具有反脆弱性的人,也不做極其聰明但脆弱的人。
我們很容易看到周圍有一些偏好壓力和波動性的事物,如經濟系統、你的身體、你的營養(糖尿病和阿爾茨海默病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于飲食缺乏隨機性,缺乏偶爾挨餓帶來的壓力)、你的心靈,甚至還有極具反脆弱性的金融合約——它們本質上就是要從市場的波動中獲益。
反脆弱性使我們更好地理解了脆弱性。正如不減少疾病我們就無法改善健康,不減少損失我們就無法增加財富,反脆弱性和脆弱性是同一波譜上的不同波段。
非預測性
掌握反脆弱性的機制后,我們就可以在充滿不確定性的商業、政治、醫學和整個生活中(未知因素占主導地位的地方,隨機性、不可預測性、不透明性或不完全理解性占主導的情況下)做出非預測性決策,建立一個系統和廣泛的指導。
弄清楚什么是脆弱的,比預測對其造成傷害的某個事件是否會發生要容易得多,脆弱性是可以衡量的,但風險卻是無法衡量的(在賭場外,或者在自稱“風險管理專家”的人的頭腦之外)。這為我所說的“黑天鵝”問題提供了一個解決方案,因為我們原本就不可能計算出重要的罕見事件的風險,也無法預測其何時會發生。但事物對波動性所致危害的敏感性是可觀察的,這比對造成危害的事件進行預測更容易。因此,我們建議顛覆我們目前的預測、預言和風險管理方法。
在每一個領域或應用方面,我們都提出了通過降低脆弱性或利用反脆弱性,從脆弱走向反脆弱性的規則。而且,我們幾乎總能使用一個簡單的不對稱測試來檢測反脆弱性和脆弱性:從隨機事件(或一定沖擊)中獲得的有利結果大于不利結果的就是反脆弱的,反之則是脆弱的。
剝奪反脆弱性
最重要的是,如果反脆弱性是所有幸存下來的自然(和復雜)系統的特征,那么剝奪這些系統的波動性、隨機性和壓力源反而會傷害它們。它們將會變弱、死亡或崩潰。我們一直在通過壓制隨機性和波動性來削弱經濟、我們的健康、政治生活、教育,甚至幾乎所有的東西……正如在床上躺一個月(最好是手上有一本未刪節版的《戰爭與和平》或者《黑道家族》全部86集的碟片)會導致肌肉萎縮,復雜系統在被剝奪壓力源的情況下會被削弱,甚至被扼殺。現代的結構化社會大多正以自上而下的政策和機制(被稱為“蘇聯–哈佛派謬見”)傷害著我們:它們的所作所為實際上侵犯了系統的反脆弱性。
這是現代化的悲劇,正如極為焦慮、過度保護子女的父母。那些試圖幫助我們的人往往會對我們造成最大的傷害。
如果說一切自上而下的東西都會使我們變得脆弱,并且阻礙反脆弱性和成長,那么一切自下而上的事物在適量的壓力和混亂下反而能夠蓬勃發展。發現(或創新,或技術進步)的過程本身就取決于能增進反脆弱性的自由探索和積極的冒險,而非正規的教育。
以犧牲他人的利益為代價獲利
社會最大的脆弱性制造者和最大的危機制造者,正是那些置身事外,不承擔后果的人。一些人以犧牲他人利益為代價實現反脆弱性,也就是說,他們從波動性、變化和混亂中實現有利結果(或獲得收益),而將他人暴露于損失或傷害的不利因素下。這種以別人的脆弱為代價而取得自己的反脆弱性的行為是很隱蔽的——由于蘇聯–哈佛派知識分子圈無視反脆弱性,因而此類不對稱性(到目前為止)很少有人能夠識別,更別提傳授了。
此外,我們發現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由于日益復雜的現代制度和政治事務,這些“危及他人的重大風險”很容易被隱瞞。過去,甘冒風險的人才會位高權重,他們必須為自己的不當行為承受損失,而英雄則是那些為了他人的利益承受損失的人,如今,情況卻完全相反。我們正目睹一群反面“英雄”人物的涌現,他們多為政府官員、銀行家,或者只知道借他人名氣自抬身價,參加達沃斯會議的成員,以及權力過大的學者。這群人不會承受真正的損失,也不受問責制的約束。他們將整個系統玩弄于股掌之上,而公民卻要為其埋單。
歷史上從未有過如此多的非冒險者,也就是施加重大控制力而個人卻不承擔風險的人。
他們忘記了一條最主要的道德法則:你不應該為了獲得反脆弱性,而犧牲別人的脆弱。
“黑天鵝”問題的解決方案
我想快樂地生活在一個我不了解的世界里。
“黑天鵝”事件是造成廣泛、嚴重后果的,不可預知的、不定期發生的大規模事件。對某些觀察者來說,他完全沒有預料到它們的發生,這種人通常被稱為“火雞”,因為他們對這些事件完全沒有預期,并會受到這些事件的傷害。我已經說過,歷史其實大部分源于“黑天鵝”事件,但我們關心的卻是如何微調我們對普通事件的了解,因此我們不斷地開發模型、理論或表述方式,可是,這些東西不可能跟蹤“黑天鵝”事件,或者衡量這些沖擊的發生概率。
“黑天鵝”事件綁架了我們的思維,讓我們感到自己“差不多”或“幾乎”預測到了它們,因為它們都是可以進行回溯性解釋的。由于存在可預測性錯覺,我們沒有意識到這些“黑天鵝”事件對生活的影響。現實生活遠比我們記憶中的生活更加錯綜復雜——我們的頭腦傾向于將歷史以更平穩和更線性的狀態呈現出來,這導致我們低估了隨機性。一旦我們看到隨機事件時,就會心生畏懼并反應過度。在逃避這種恐懼以及對秩序的渴求中,一些人類建立的系統往往會打亂事物的隱性邏輯,或者打亂不那么明顯的邏輯,結果導致“黑天鵝”事件的發生,而且幾乎得不到任何收益。當你尋求秩序,你得到的不過是表面的秩序;而當你擁抱隨機性,你卻能把握秩序、掌控局面。
復雜系統內部充滿著難以察覺的相互依賴關系和非線性反應。“非線性”是指當你把藥品的劑量增為兩倍,或將工廠的員工數量增為兩倍時,所得效果并非初始效果的兩倍,而是要么更多,要么更少。在費城待兩個星期的愉快指數并不會是待一個星期的兩倍——對此我深有體會。把反應繪制成圖的話,并不會呈現為一條直線(“線性”),而是一條曲線。在這種環境下,簡單的因果關系錯位了;通過觀察單個部分是很難看清整個局勢的走向的。
人造的復雜系統往往會引發失控的連鎖反應,它會減少甚至消除可預測性,并導致特大事件。因此,現代世界的技術性知識可能會不斷地增加,但矛盾的是,它也會使事情變得更加不可預測。現在,由于人為因素的增加,以及我們逐漸地遠離了先祖和自然的模式,加上林林總總的設計復雜性削弱了強韌性,以至于“黑天鵝”的影響在進一步增加。此外,我們成為一種新型疾病的受害者,即新事物狂熱癥,它使我們建立起面對“黑天鵝”事件時會表現得極其脆弱的系統,卻自以為實現了所謂的“進步”。
“黑天鵝”問題有一個惱人方面,實際上也是一個很核心的并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的問題,即罕見事件的發生概率根本是不可計算的。我們對百年一遇洪水的了解遠低于5年一遇的洪災,其模型的誤差在涉及小概率事件時會成倍增長。事件越罕見,越難以追蹤,我們對其發生頻率的了解就越少。然而,事件越罕見,參與預測、建模和在會議上用花哨的演示文件陳述其計算方程式的“科學家”們卻顯得越有信心。
得益于反脆弱性,大自然是管理罕見事件的最好專家,也是管理“黑天鵝”事件的高手;幾十億年來,它成功地演變進化到今天,而無須任何由常春藤盟校培養出來的,并由某個研究委員會任命的主任給出命令和控制指令。不僅僅是“黑天鵝”事件的解決方案,了解反脆弱性還會使我們從理智上不那么害怕接受一個事實:“黑天鵝”事件對歷史、技術、知識以及所有事情的發展都有存在的必要。
僅有強韌性還不足夠
大自然不只是“安全”的,它還能積極地進行破壞和更替、選擇和重組。每當隨機事件發生時,僅僅做到“強韌性”顯然還不夠好。從長遠來看,哪怕只有一點點瑕疵的東西也會被無情的歲月所摧毀,但我們的地球卻已經運轉了大約40億年了,很顯然,僅僅依靠強韌性是完全無法辦到的:你得需要多完美的強韌性才能阻止一個裂縫最終引發整個系統的崩潰。鑒于不可能存在這樣完美的強韌性,我們需要一個能夠不斷利用(而非逃避)隨機事件、不可預測的沖擊、壓力和波動實現自我再生的機制。
從長遠來看,反脆弱性往往能從預測誤差中受益。如果按照這個理念下結論,那么很多從隨機性中受益的事物如今應該主宰世界了,而受隨機性傷害的事物就應該消失。嗯,其實現實也確實如此。我們一直有這樣的錯覺,認為這個世界的運轉有賴于規劃設計、大學研究和政府機構的資金支持,但是我們有顯著的——非常顯著——證據表明,這只是一個錯覺,我稱為“教鳥兒如何飛行”。技術是反脆弱性的結果,是冒險者們通過自由探索和反復試錯產生的,但這些籍籍無名的小人物的設計過程卻大多不為人所知。許多東西都是由工程師和能工巧匠們發明的,不過,歷史卻是由學者撰寫的;我希望我們能修正對增長、創新以及諸如此類事情的歷史詮釋。
(某些)事物的可預測性
脆弱性是相當容易衡量的,但風險卻很難衡量,尤其是與罕見事件相關的風險。[1]
我說過我們可以估算甚至衡量脆弱性和反脆弱性,但我們無法計算風險以及沖擊和罕見事件的發生概率,無論我們有多么復雜成熟的模型。如今,我們實行的風險管理僅僅是對未來發生事件的研究,只有一些經濟學家和其他狂人才會做出有違經驗事實的斷言,稱能夠“衡量”這些罕見事件未來的發生概率,當然也會有愚蠢的人聽信他們,而無視經驗事實與此類斷言的歷史準確率。但是,脆弱性和反脆弱性是一個物體、一個茶幾、一個公司、一個行業、一個國家、一個政治制度當前屬性的一部分。我們可以識別和看到脆弱性,甚至在很多情況下還可以測量它,或至少能以較小的誤差測量相對脆弱性,而對風險的測量相比較而言(到目前為止)則并不可靠。你沒有任何可靠的依據說某個遙遠的事件或沖擊的發生概率比另一個事件更高(除非你喜歡自我欺騙),但你能很有信心地說,當某一事件發生時,某一個物體或結構比另一個物體或結構更脆弱。你很容易做出判斷,在溫度突然變化的情況下,你的祖母要比你更脆弱;發生政變時,一些軍事獨裁國家要比瑞士更脆弱;危機來臨時,銀行比其他部門更脆弱;或者發生地震時,一些建造結構不牢固的現代建筑要比古老的查特雷斯大教堂更脆弱。關鍵的是,你甚至可以預測哪一個人會存活更長的時間。
我無意討論風險(這涉及預測,又很局限),我主張使用脆弱性的概念,它不帶有預測性,并且與風險不同,它是一個有趣的詞,可以描述一個與其完全相反的不受局限的概念:反脆弱性。
衡量反脆弱性有一個類似煉金石的方法或一個簡化的規則,它使我們能夠跨領域(從個人健康到社會建設)地識別反脆弱性。
在實際生活中,我們已在不知不覺中探究反脆弱性了,并有意識地抗拒它,特別是在知性世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