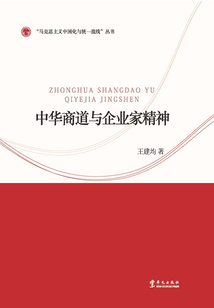最新章節(jié)
書友吧第1章 導言
在現(xiàn)代經(jīng)濟發(fā)展中,企業(yè)家精神重要嗎?如果企業(yè)家精神重要,那么,什么是企業(yè)家精神?企業(yè)家精神又是從何而來的呢?這個問題實際上追問的是企業(yè)家精神的源泉問題,或者說是企業(yè)家精神的文化基因問題。在此基礎上,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培育當今中國的企業(yè)家精神?對此,我們所要探討的“中華商道與企業(yè)家精神”這一主題,就是要力圖解決這些問題。
企業(yè)家精神具有極端的重要性
我們知道,現(xiàn)代經(jīng)濟的發(fā)展,企業(yè)家精神具有極端的重要性,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我們不能設想,沒有喬布斯的蘋果公司;同樣,我們也無法想象,沒有任正非的華為公司。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如果我們從財富的角度簡單進行一下比較,可能會更加震撼。2017年,蘋果公司銷售收入達到了2292億美元[1],在178個國家中位居第45位[2];2018年,蘋果公司更進一步,其銷售收入創(chuàng)造新的紀錄,達到了2660億美元[3],在178個國家中位居第43位[4]。現(xiàn)在,讓我們看一下華為公司。2017年,華為公司的銷售收入達到了894億美元[5],在178個國家中位居第64位[6];2018年,華為公司同樣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其銷售收入跨越千億美元大關,達到1051.91億美元[7]。如果把華為同國內(nèi)26個省會城市進行比較,同樣令人震撼。2017年華為的銷售收入是6063.21億人民幣,以GDP計算,位居省會城市的第15位[8]。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僅華為一家企業(yè)就提供19萬個就業(yè)崗位;2017年,向國家繳納稅收710億元人民幣[9]。這可是真金白銀的財富創(chuàng)造。
正因為如此,早在2014年的北京APEC會議(亞太經(jīng)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就指出,市場的活力來自人,特別是來自企業(yè)家,來自企業(yè)家精神[10]。2016年,銀行保險監(jiān)督管理委員會主席曾在《人民日報》以“企業(yè)家的作用無可替代”為題撰文[11]。可見,我們對企業(yè)家精神的認識相當深刻。
這里有必要追問一下,對于現(xiàn)代經(jīng)濟,為什么企業(yè)家精神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呢?這要從市場經(jīng)濟的效率來進行分析。我們說市場經(jīng)濟之所以有效率,就在于市場能夠通過價格、供求和競爭等機制有效地配置資源,從而更有效地創(chuàng)造財富。這就是亞當·斯密所說的“看不見的手”的力量。但實際上真正配置資源的,并非“看不見的手”,而是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yè),而企業(yè)的靈魂是企業(yè)家。因此,我們說市場配置資源,實際上就是企業(yè)配置資源,而企業(yè)配置資源,實際上就是企業(yè)家配置資源。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現(xiàn)代經(jīng)濟就是企業(yè)家經(jīng)濟。這就是企業(yè)家、企業(yè)家精神之所以是推動經(jīng)濟發(fā)展的重要力量、甚至是決定性力量的原因所在。
但是,在今天,我們不僅要從觀念上深刻認識到企業(yè)家精神的重要性,更要從現(xiàn)實上認識到弘揚企業(yè)家精神的緊迫性。這是因為,中國現(xiàn)在進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要實現(xiàn)經(jīng)濟轉(zhuǎn)型升級和高質(zhì)量發(fā)展,構(gòu)建新發(fā)展格局,突破資源環(huán)境約束、人力成本約束以及技術創(chuàng)新約束,提升企業(yè)發(fā)展的核心競爭力,急需企業(yè)家精神。面對百年未有之變局,特別是面對美國對中國經(jīng)濟毫無底線的瘋狂打壓和脫鉤政策,我們急需企業(yè)家精神。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更是急需企業(yè)家精神。那么,什么是企業(yè)家精神呢?如何培育中國當代的企業(yè)家精神呢?或者說企業(yè)家精神是從何而來的呢?
何謂企業(yè)家精神
要知曉什么是企業(yè)家精神,首先要明確什么是企業(yè)家。所謂企業(yè)家,就是組織和管理生產(chǎn)要素的人。一般認為,企業(yè)家這一概念源自理查德·埃利。19世紀末,經(jīng)濟學家理查德·埃利在《政治經(jīng)濟學導論》一書中指出,企業(yè)家一詞借用的是法語,指的是組織和管理生產(chǎn)要素者。自此之后,包括凱恩斯、熊彼特,都開始使用企業(yè)家這個詞。但是,早在中世紀末,人們就開始使用企業(yè)家一詞了。在當時,企業(yè)家是法國貸款術語,被用來形容一名戰(zhàn)場指揮官。后來,它的意思逐漸擴展到商業(yè)領域。同時,它也被用來指稱某個公共音樂機構(gòu)的主管或管理者[12]。當然,從實際角度看,當商業(yè)從農(nóng)業(yè)和手工業(yè)中分離出來,出現(xiàn)了專門從事商品交換活動的從業(yè)人員,形成了第三次社會大分工以后,就產(chǎn)生了企業(yè)家。雖然這時候沒有企業(yè)家之名,但是有企業(yè)家之實。歷史地看,古巴比倫是遠古企業(yè)家的搖籃。彰顯古巴比倫商業(yè)文明的《漢謨拉比法典》,曾深刻影響了后來的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商業(yè)及其經(jīng)濟慣例。不僅如此,一些商貿(mào)經(jīng)營的知識也是由東方傳入古希臘和古羅馬的,特別是在帝國末期,從事貿(mào)易的主要就是東方居民[13]。所以,不僅僅在科學技術方面,古希臘、古羅馬對古代東方借鑒頗多,就是在工商業(yè)及其技能方面,古希臘、古羅馬文明中的絕大部分都有東方的淵源[14]。
在中國,遠在神農(nóng)氏和舜帝時期,中國商業(yè)活動及商業(yè)文明就已經(jīng)有所發(fā)展了。而商朝因善于經(jīng)商而聞名天下,以至于后來就把凡是從事商業(yè)交換的人和行業(yè)稱為商人和商業(yè)。商族、商人、商品、商業(yè),都和古時的商朝有關[15]。進入春秋戰(zhàn)國時期,經(jīng)濟發(fā)展,自由商人崛起,中國實際上已經(jīng)是一個具有市場經(jīng)濟體系雛形的社會了。[16]當時,儒家思想脫穎而出,深刻影響了中國的商業(yè)倫理,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中華儒商商道和儒商精神,對今天的企業(yè)家和企業(yè)家精神仍然具有深刻影響。
那么,什么是企業(yè)家精神呢?實際上,對于什么是企業(yè)家精神,并沒有形成一個共識。企業(yè)家精神這一概念最早是由富蘭克·H·奈特(1885—1972)正式提出來的,本意是指企業(yè)家的才能才華。[17]但隨著生產(chǎn)力的不斷提高,社會經(jīng)濟飛速發(fā)展,對企業(yè)家精神這一概念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入,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來界定企業(yè)家精神,企業(yè)家精神也被賦予了越來越多的含義。
早期的經(jīng)濟學家讓·巴蒂斯特·薩伊(1767—1832)是從價值的角度來分析企業(yè)家精神的。他指出,企業(yè)的目的是創(chuàng)造價值,企業(yè)家是價值創(chuàng)造的帶頭者。基于此,薩伊認為,企業(yè)家精神就是通過對經(jīng)濟資源的更合理調(diào)配以實現(xiàn)價值的創(chuàng)造。這樣,薩伊認為,企業(yè)家精神就是將經(jīng)濟資源從生產(chǎn)率較低、產(chǎn)量較小的領域轉(zhuǎn)移到生產(chǎn)率較高、產(chǎn)量較大領域的能力。[18]著名經(jīng)濟學家阿爾弗雷德·馬歇爾(1842—1924)則從市場平衡的角度來認識企業(yè)家精神。他認為,由于價格自發(fā)調(diào)節(jié)導致了市場的不均衡性,而企業(yè)家的任務,就是消除這種不均衡性。所以,阿爾弗雷德·馬歇爾認為,企業(yè)家精神是消除市場不均衡性的特殊力量。[19]著名經(jīng)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1883—1950)通過分析企業(yè)家的特性,指出創(chuàng)新精神是企業(yè)家精神的本質(zhì)特征。[20]基于創(chuàng)新精神,熊彼特進一步指出,企業(yè)家精神是一種善于發(fā)現(xiàn)創(chuàng)新和整合的能力,以及將這種能力付諸企業(yè)實踐行動的集合能力,即做別人沒做過的事,或是以別人沒用過的方式做事的組合。所以,他又進一步將這種行動的組合定義為開發(fā)新產(chǎn)品、開辟新的市場、尋求新的供給來源、實現(xiàn)新的組織形式等一系列活動。[21]其后,基于市場機會把握能力,彼得·德魯克(1909—2005)認為,企業(yè)家精神是善于發(fā)現(xiàn)并且把握市場機會,用來實現(xiàn)自身目標以及滿足社會需要的能力。彼得·德魯克認為,企業(yè)家精神是尋求機會而不是引發(fā)變化,它是對已經(jīng)存在的機會的把握。[22]這種觀點是以企業(yè)的發(fā)展為出發(fā)點,以把握市場機會為核心,認為企業(yè)家精神,就是貫穿于從創(chuàng)業(yè)到發(fā)展壯大的整個企業(yè)歷程中對于機會把握的能力。盡管,對于企業(yè)家精神的認識如此多元,且還在深化之中,但是,有一個共識是,企業(yè)家精神是不能脫離企業(yè)家的生長環(huán)境的,特別是文化環(huán)境。另外,為了分析方便,這里還是要就企業(yè)家精神的內(nèi)涵作一個概括,即企業(yè)家精神是企業(yè)經(jīng)營管理者在從事企業(yè)生產(chǎn)經(jīng)營活動過程中所產(chǎn)生的思想觀念、精神素質(zhì)以及行為方式的總和。簡而言之,企業(yè)家精神就是企業(yè)家在領導企業(yè)不斷發(fā)展壯大的過程中所形成的所有精神特質(zhì)的總和。從內(nèi)容上看,企業(yè)家精神主要包括創(chuàng)新精神、敬業(yè)精神、競爭精神、合作精神、冒險精神,以及隨時代不斷變化發(fā)展所形成的其他精神。其中,創(chuàng)新精神是企業(yè)家精神的本質(zhì)特征。
那么,這里我們要繼續(xù)追問的是企業(yè)家精神從何而來的問題。其實,上面已經(jīng)說過,企業(yè)家精神是不能脫離企業(yè)家生長環(huán)境的,特別是文化環(huán)境。下面我們就此問題作進一步的分析。
企業(yè)家精神從何而來
著名歷史學家威爾·杜蘭特和阿里爾·杜蘭特在《歷史的教訓》一書中指出:“不是種族塑造了文明,而是文明塑造了民族;地理、經(jīng)濟和政治環(huán)境造就了文化,而文化又創(chuàng)造了人類形態(tài)。”[23]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人是文化的產(chǎn)物。與之相應的是,文化必將塑造經(jīng)濟及其作為經(jīng)濟主體的企業(yè)家及其企業(yè)家精神。因為,按照道格拉斯·C·諾斯(1920—2015)的看法,對于企業(yè)家而言,“我們的文化傳統(tǒng),我們的信仰體系,這一切都是根本的制約因素,我們必須仍然考慮這些制約因素。這也就是說,我們必須非常敏感地注意到這一點:你過去是怎樣走過來的,你的過渡是怎樣進行的。我們必須非常了解這一切。這樣,才能很清楚未來面對的制約因素,選擇我們有哪些機會。”[24]而且,“如果一個國家不知道自己過去從何而來,不知道自己面臨的現(xiàn)實制約、傳統(tǒng)影響以及文化慣性,就不可能知道未來的發(fā)展方向”。[25]所以,文化傳統(tǒng)是影響企業(yè)家及其企業(yè)家精神的重要因素。
事實上,不論從歷史上還是從現(xiàn)實上來看,不同的文化傳統(tǒng)孕育了不同的企業(yè)家精神。以色列文化傳統(tǒng)孕育了以色列企業(yè)家的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精神;阿拉伯文化傳統(tǒng)孕育了阿拉伯企業(yè)家的誠信品格;而以中華儒商傳統(tǒng)為主的中華商道,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孕育了富有特色的中華儒商文化傳統(tǒng)。今天,以中華儒商文化傳統(tǒng)為主的中華商道,應當也必然是培育當代中國企業(yè)家精神的源頭活水。
實際上,對于企業(yè)家、企業(yè)家精神的文化根源問題,尤其是關于中國企業(yè)家和企業(yè)家精神的培育問題,現(xiàn)代管理之父德魯克的認識更為深刻,也更具有現(xiàn)實針對性。他一針見血、態(tài)度鮮明地指出:“中國發(fā)展的核心問題,是要培養(yǎng)一批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但是,管理者不同于技術和資本,不可能依賴進口。他們應該是中國自己培養(yǎng)的管理者,他們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國家和人民,并深深植根于中國的文化、社會和環(huán)境中。只有中國人才能建設中國。”[26]所以,中國的企業(yè)家、企業(yè)家精神應該也只能來自產(chǎn)生它的文化基因,這就是以中華儒商文化傳統(tǒng)為主的中華商道。
當然,更為重要的問題是,以中華儒商文化傳統(tǒng)為主的中華商道,能否給予我們今天的企業(yè)家所需要的營養(yǎng)呢,這里就必須要提到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得主阿瑪?shù)賮啞ど?933—)的一個重要觀點。他認為,對經(jīng)濟問題的最根本追問是,人應當怎樣生活的問題。他指出:“就其基本性質(zhì)和特征而言,任何經(jīng)濟問題歸根到底都是一個價值問題,而對任何價值的追問,最終都要追究到蘇格拉底式的問題——人應當怎樣生活?作為價值的經(jīng)濟問題必須和人類的生活目的相關。”[27]人應當怎樣生活?它進一步追問的是,作為人何謂正確,或者是,人應當如何正確地生活。這正是日本著名企業(yè)家、思想家、哲學家、慈善家稻盛和夫(1932—)做人做事的基準和前提。[28]
稻盛和夫認為,在做人、做事時,必須追問這樣一個問題,“作為人何謂正確”,要把做人應當遵循的普遍真理作為人生的原理原則。[29]而對于人應當怎樣正確地生活?人應當遵循怎樣的普遍真理?它的答案,恰恰就在儒家經(jīng)典思想中。對此,稻盛和夫在《企業(yè)家精神》一書中對該問題作出了明確回答。他指出:“所謂的中國古代經(jīng)典,就是作為人應有的正確活法,也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在企業(yè)經(jīng)營中,必須重視的道理和行為規(guī)范。”他還特別指出,當今的一些日本企業(yè)家,就是因為丟失了以德為本的經(jīng)營道理和規(guī)范,稍有成績就自我陶醉,忘掉謙虛,言行傲慢,放縱私欲,以致沒落和滅亡。同時,他還深刻地指出,不只是日本存在這樣的問題,發(fā)達國家以及今天成功人士輩出、催生了眾多中國夢的中國也面臨這個問題。所以,他強調(diào),重新學習中國古代圣賢的智慧,以德為本,創(chuàng)立和諧企業(yè),對于我們所有人都是必要的。[30]
應當說,稻盛和夫?qū)θ寮宜枷氲恼J識是非常精當、準確的。儒家思想的核心就一個字,“仁”,即“仁者愛人、以人為本”。這是儒家的核心價值,也是儒家的根本原則。用孟子的話來說就是,“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31]這是說,“仁”包括三層含義,即對親人的愛,對大眾的愛,對萬物的愛。可以說是愛滿天下[32],是真正的博愛。對于儒家而言,愛大眾,造福大眾,“天人合一”,讓大眾生活得更美好,是最高的道德。所以,孔子強調(diào),“博施于民而能濟眾”者[33],不僅僅是仁者,而且是圣人。一個人正確的活法,就是以人為本,讓大眾生活得更好。而以人為本是中華文化的根本精神和品格,是中華文化的一個主要特征。[34]
因此,要培育新時代中國的企業(yè)家、企業(yè)家精神,必須深入到中華商道之中,要追問中華商道的本質(zhì),理解中華商道的內(nèi)涵,追尋中華商道的歷史發(fā)展,剖析中華商道的現(xiàn)代意義,傳承和弘揚中華商道的核心價值觀。在此基礎上,以中華商道為根基,客觀比較中西方商業(yè)文化(文明),積極學習借鑒包括西方在內(nèi)的商業(yè)文化(文明)的積極成果,只有如此,才能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企業(yè)家和企業(yè)家精神的偉力。當然,我們在強調(diào)企業(yè)家精神的文化基因時,不僅不排斥西方文化以及其他文化的積極因素,而且必須努力學習借鑒一切有利于中華商道的現(xiàn)代商業(yè)文明的積極成果。這是今天傳承和弘揚中華商道的應有之義。
另外,既然企業(yè)家精神源于文化基因,為了更好地對這些內(nèi)容展開分析和討論,就需要深化對文化結(jié)構(gòu)和文化功能的認識,進而深化對商業(yè)文化(文明)和企業(yè)文化結(jié)構(gòu)的認識。而對這個問題的深入分析,有助于我們深入認識中華商道的本質(zhì),也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學習借鑒西方商業(yè)文化(文明)。
對文化的深入分析是關鍵
深化對中華商道的認識,培養(yǎng)新時代企業(yè)家精神,關鍵是要深入認識文化的結(jié)構(gòu)和功能。在此基礎上,還要清晰地把握商業(yè)文化和企業(yè)文化的結(jié)構(gòu)和功能。這樣,才能深入分析中華商道和企業(yè)家精神的關系問題。這實際上就是本書對中華商道與企業(yè)家精神這一核心問題進行探討所使用的分析框架。
眾所周知,文化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文化是指人類在社會實踐過程中所獲得的物質(zhì)、精神的生產(chǎn)能力和創(chuàng)造的物質(zhì)、精神財富的總和;狹義的文化是指精神生產(chǎn)能力和精神產(chǎn)品,包括一切社會意識形式,自然科學、技術科學、社會意識形態(tài)。[35]在這里,我們是從廣義角度來分析文化的。
據(jù)此,就文化的結(jié)構(gòu)看,文化包含物質(zhì)(技術)文化、制度(組織)文化和精神(價值)文化,它們共同構(gòu)成一個有機的整體。[36]其中物質(zhì)文化是基礎,處于結(jié)構(gòu)的表層;制度文化是保障,處于結(jié)構(gòu)的中層;精神文化是核心,處于結(jié)構(gòu)的核心。簡單地看,三者的關系是:精神文化主要體現(xiàn)為核心價值觀,核心是以人性需要為本,即以人為本,或是以人為中心,也就是我們今天強調(diào)的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理念,這是物質(zhì)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根據(jù);物質(zhì)文化以生產(chǎn)工具為基礎,主要體現(xiàn)為一定技術水平下的產(chǎn)品和服務,以符合人性的需要為目的,是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基礎和體現(xiàn),本質(zhì)上要體現(xiàn)以人為本的核心價值觀;制度文化主要體現(xiàn)為以法制為基礎的組織和行為制度規(guī)范,以保護人的權利和利益為目的,是物質(zhì)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保障,本質(zhì)上是對以人為本核心價值觀的規(guī)定。正是在此意義上,人本的精神文化是商業(yè)文化的核心,是物質(zhì)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根據(jù);而物質(zhì)文化和制度文化是對人本精神文化的反映和保障。在一定時期的發(fā)展階段,它們?nèi)邞斒潜舜藚f(xié)調(diào)一致的。否則,這種商業(yè)文化是難以適應和推進經(jīng)濟社會的發(fā)展要求的。
這里,我們還可以從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學的視角來認識這三者的關系。在《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指出:“人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chǎn)中發(fā)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zhì)生產(chǎn)力的一定發(fā)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chǎn)關系。這些生產(chǎn)關系的總和構(gòu)成社會的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xiàn)實基礎。物質(zhì)生活的生產(chǎn)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zhì)生產(chǎn)力發(fā)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xiàn)存生產(chǎn)關系或財產(chǎn)關系(這只是生產(chǎn)關系的法律用語)發(fā)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形式變成生產(chǎn)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jīng)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fā)生變革。”[37]這就是說,物質(zhì)文化是以生產(chǎn)工具為基礎構(gòu)成了經(jīng)濟基礎,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是以法制為基礎的制度規(guī)范和以價值觀為基礎的意識形態(tài)共同組成的上層建筑。同樣的,在一定時期的一定發(fā)展階段,經(jīng)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是應當相互協(xié)調(diào)一致的。否則,就會阻礙經(jīng)濟社會的發(fā)展。
當然,物質(zhì)文化中的科技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推動生產(chǎn)工具創(chuàng)新改進,由此在生產(chǎn)出更先進、更符合人性需要的產(chǎn)品和服務時,必然會引發(fā)相應制度文化的變遷,以適應和保障新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而精神文化是否會產(chǎn)生相應變化,關鍵在于精神文化的內(nèi)核,也就是核心價值觀的人本性質(zhì)。換言之,以人為本是根本;若說核心價值觀發(fā)生變化,只能是更符合人性發(fā)展的需要,特別是符合人自由全面發(fā)展的要求。但是,人本精神的內(nèi)核隨著時代發(fā)展,將會有新的闡發(fā)和弘揚。它的內(nèi)核不應改變,也不能改變。如,“仁”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念,其內(nèi)核是,“仁者愛人,以人為本”,這同文化精神層面的要求是一致的。但是,對于“仁”來說,孔子曰成仁,孟子曰取義。孔子的仁,強調(diào)視人如己;孟子的仁,強調(diào)社會責任。宋明理學時期,朱熹的仁,強調(diào)新民;而明朝心學時期,王陽明的仁,強調(diào)仁民;新時代的今天,我們則強調(diào)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理念。時代在變,但“仁”的內(nèi)核卻始終如一。正因為如此,學者們指出,以人為本是中華文化的根本精神和品格[38],它將隨著科技進步更加凸顯,并非改變。更重要的是,文化的綿延,就在于文化的核心價值觀的延續(xù)不斷。“仁”的核心價值觀在中國數(shù)千年未變,所以,中國文化也就數(shù)千年綿延不斷。[39]
從這個意義上說,“仁”也必然是中華商道的本質(zhì)。對此,篤信中華商道的稻盛和夫也明確指出,商也,乃仁。[40]如果簡潔一點,以人為本其實就是人本、人道,那么,人本、人道就是商道,中華商道的本質(zhì)就是人本、人道。這樣,我們可以說,儒商就是以儒家核心價值觀指導企業(yè)經(jīng)營的企業(yè)家,即以儒家“仁、義、禮、智、信”為核心價值觀指導企業(yè)經(jīng)營的企業(yè)家。“仁”為根本理念,“義、禮、智、信”是“仁”的充分體現(xiàn)和展開,目的在于以人為本,追求和服務于人類對更美好生活的需求。以人為本的中華商道具有豐富的內(nèi)容。如“仁者愛人、以人為本”的商道精神,“以義取利、見利思義”的義利精神,“非誠賈不得食于賈”[41]的誠信精神,經(jīng)世濟民的家國天下情懷,互惠互利的商業(yè)智慧,貴群尚和的集體精神,等等。簡言之,中華商道蘊涵的人本觀、義利觀、誠信觀、創(chuàng)新觀、集體觀、家國觀,賦予了中國商業(yè)文明獨特的精神氣質(zhì)。
當然,就儒商的概念而言,是有一個歷史發(fā)展的過程的。儒商在春秋、戰(zhàn)國之際雖已出現(xiàn),但是,當時有儒商之實,并無儒商之名。那時令人稱道的商人被稱為“誠賈”“良商”。明嘉靖、萬歷之際,已經(jīng)出現(xiàn)并流行“儒賈”說,到清順治、康熙時才出現(xiàn)“儒商”說。歷史發(fā)展到近代,以張謇為代表的儒商傾其一生的心血實業(yè)救國,推動了近代儒商的新發(fā)展。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展,在中華大地上儒商再次崛起,蔚然成風,成為推動經(jīng)濟社會進步的偉大力量。
另外,這里有必要就商人和企業(yè)家作一個簡要說明。商人或企業(yè)家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商人或企業(yè)家是指商業(yè)流通領域的經(jīng)營者。在西方工業(yè)革命之前的歷史發(fā)展中,所謂的商人或企業(yè)家,主要就是這種狹義上的商人或企業(yè)家。廣義的商人或企業(yè)家是指工商業(yè)一切領域的經(jīng)營者,尤其是指工業(yè)領域或者說是實業(yè)領域的經(jīng)營者。在中國,到19世紀末,特別是20世紀20年代的時候,人們所強調(diào)的實業(yè)救國,主要指的就是生產(chǎn)領域或工業(yè)領域。今天,人們同樣是從廣義的角度來指稱企業(yè)家的。當然,也更重視所謂實業(yè)領域的企業(yè)家。
當前,新技術革命如火如荼,以人為本的核心價值觀,或者說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理念,既是新技術革命的根本目的,也是新技術革命的根本動力。新技術革命更加凸顯了人本價值觀的意義。對此,美國學者哈克在《新商業(yè)文明:從利潤到價值》一書中指出,工業(yè)時代是以企業(yè)和股東利益最大化為目的的,這種價值觀及其經(jīng)濟增長模式已經(jīng)走上了絕路。他認為,20世紀商業(yè)理念以攫取最大利益為目的,將成本轉(zhuǎn)嫁到普通民眾、社會、社區(qū)、環(huán)境和后代身上,是不公平的,其后果是不可逆轉(zhuǎn)的。如2008年的金融危機就是將次貸危機的巨額成本轉(zhuǎn)嫁給公眾、社會、后代了。[42]而21世紀的新商業(yè)文明立足于新技術革命,利潤追求讓位于價值創(chuàng)造,目的在于改善大眾、社區(qū)、社會和后代的生活狀況,實現(xiàn)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要求。[43]新技術革命需要與之相應的新商業(yè)文明,而新商業(yè)文明的本質(zhì)正是以人為本。新商業(yè)文明更加了凸顯人本這一核心價值觀。
總而言之,文化是物質(zhì)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位一體的有機整體。其中以人為本的精神文化是核心。明確了文化的結(jié)構(gòu)及其核心,還需要進一步來了解商業(yè)文化(文明)。顯然,與文化的結(jié)構(gòu)一樣,商業(yè)文化(文明)的結(jié)構(gòu)也是如此,分為商業(yè)物質(zhì)文化、商業(yè)制度文化、商業(yè)精神文化。商業(yè)文化(文明)的結(jié)構(gòu)及其關系也和文化的結(jié)構(gòu)及其關系是相同的。同樣地,企業(yè)文化的結(jié)構(gòu)也是如此,分為企業(yè)物質(zhì)文化、企業(yè)制度文化和企業(yè)精神文化。而企業(yè)文化的結(jié)構(gòu)及其關系同文化的結(jié)構(gòu)及其關系也是相同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商業(yè)文化(文明)和企業(yè)文化具有一致性,可以當作是同一事物。因此,下面我們在分析文化的功能時,直接分析商業(yè)文化(文明)的功能,而不再分析文化的功能和企業(yè)文化的功能。
就商業(yè)文化(文明)的功能來看,相對于商業(yè)文化(文明)的結(jié)構(gòu),商業(yè)文化(文明)的功能主要有三大功能:滿足需要功能、經(jīng)營管理功能和交流輻射功能。
首先,滿足需要功能。文化的功能,或者說商業(yè)文化(文明)功能,從根上說就是滿足人的需要。[44]而人的需要就是人性。[45]滿足人的需要,就是滿足人性的需要。這是商業(yè)文化(文明)的根本目的和價值。無論是財富說、利潤說,還是價值說,都并非是商業(yè)文化(文明)的根本目的和價值,它只是滿足人類生存和發(fā)展的基礎和手段,是我們獲得真實自由的手段[46]。
其次,經(jīng)營管理功能。在商業(yè)文化(文明)中,商業(yè)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商業(yè)經(jīng)營管理活動過程中起著導向、規(guī)范、凝聚、激勵等作用。其中,商業(yè)精神文化所體現(xiàn)的價值導向,能夠起到精神激勵的作用,特別是共同的價值觀,以及體現(xiàn)這種價值觀的企業(yè)公平、公正的管理、薪酬、升職等企業(yè)制度文化,能夠發(fā)揮目標激勵、行為激勵、競爭激勵等積極作用,能夠發(fā)揮比物質(zhì)激勵更強、更持久的動力[47],調(diào)動起職工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激發(fā)出人們的潛在智慧,充分發(fā)揮每個員工的知識和優(yōu)勢,提高各部門和員工的自主管理能力、自主經(jīng)營能力和企業(yè)忠誠度,降低員工流動和雇傭成本,提高企業(yè)核心競爭力,推動企業(yè)的快速發(fā)展。[48]
最后,交流輻射功能。商業(yè)文化(文明)對消費者、員工、企業(yè)、市場、社會以及國際環(huán)境起著交流、輻射作用,這是由商品交換的社會性和開放性決定的。商業(yè)文化(文明)的交流輻射功能主要是由商品和服務所體現(xiàn)出的文化內(nèi)涵及其傳播來發(fā)揮作用的。商品交換及其文化交流超越了地域、民族、國界的范圍,不同的商業(yè)文化(文明)相互借鑒,取長補短,相互促進,推動了商業(yè)和商業(yè)文化(文明)的發(fā)展。[49]
總之,從商業(yè)文化(文明)的結(jié)構(gòu)和功能來認識和分析中華商道與企業(yè)家精神,可以更加透徹地認識到,人本價值觀是中華商道的根本之道,是企業(yè)家精神的核心要義,具有普遍性的意義。在今天,是應當也必然具有共同價值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深刻認識到,中國是后發(fā)展國家,就物質(zhì)文化層面以及制度行為的法制層面,中華商道還有不足之處,應當也必須積極學習和借鑒西方發(fā)達國家的經(jīng)驗和教訓。而這些技術和制度,正如德魯克所說,是可以引進的,也是應當且必須學習和借鑒的。當然,要指出的是,這些技術和制度可以稱之為“術”。而道和“術”必須有機結(jié)合,相輔相成。這也正是商業(yè)文化(文明)的結(jié)構(gòu)所揭示的一般性規(guī)律,即商業(yè)文化(文明)是物質(zhì)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位一體的有機整體。
進一步來講,中華商道強調(diào)的是人性自覺,而西方商業(yè)文化更注重理性自覺。所以,華為公司的首席管理科學家黃衛(wèi)偉指出,東方道+西方術=華為的成功。無獨有偶,方太的二代掌門人茅忠群也深刻地指出:中學明道、西學優(yōu)術、中西合璧、以道馭術[50]。當然,歸根結(jié)底,道是根本,是目的,是動力;而術是技術,是方法,是手段。道要駕馭術,術要服務于道。對此,成中英分析指出:“人性和理性,都是人類所需要的。如果只有人性,而沒有理性,人類就只有質(zhì)而沒有文,只有情而沒有理。若只有理性,而沒有人性,人類將淪為冷血的機器,喪失道德價值的肯定,只講求方法而不講目的。……一定要堅持人性的自覺,同時也要擴大理性的自覺”。[51]要把道與術相結(jié)合,把人性與理性相結(jié)合。這是今天傳承和弘揚中華商道的必然要求。
另外,還要強調(diào)的是,今天新時代中國的企業(yè)家面對百年未有之變局,特別是面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無所不用其極的技術脫鉤、打壓和卡脖子行為,是在先進的芯片等技術既買不來也求不來的情況下,只能靠自己。我們的企業(yè)家除了以更加開放的精神學習和借鑒包括西方在內(nèi)的先進技術和制度的同時,更要深深扎根于以人為本的中華商道的基礎之上,以“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創(chuàng)新奮斗精神,大力推進科技的自主創(chuàng)新,努力提高原始創(chuàng)新能力和集成創(chuàng)新能力,把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里,徹底打破西方的技術霸凌,推動中華民族復興偉業(yè)的實現(xiàn)。
注釋
[1]蘋果公司年銷售收入表,見財富中文網(wǎng)(http://www.fortunechina.com/fortune500/c/2020-05/18/content_365275.htm.)。
[2]世界各國GDP統(tǒng)計,見https://www.kylc.com/stats/global/yearly/g_gdp/2019.html.
[3]蘋果公司年銷售收入表,見財富中文網(wǎng)(http://www.fortunechina.com/fortune500/c/2020-05/18/content_365275.htm.)。
[4]世界各國GDP統(tǒng)計,見https://www.kylc.com/stats/global/yearly/g_gdp/2019.html.
[5]華為公司2017年年報,見https://www.huawei.com/cn/annual-report.
[6]世界各國GDP統(tǒng)計,見https://www.kylc.com/stats/global/yearly/g_gdp/2019.html.
[7]華為公司2018年年報,見https://www.huawei.com/cn/annual-report.
[8]華為公司2017年年報,見https://www.huawei.com/cn/annual-report.
[9]同上。
[1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經(jīng)濟建設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62頁。
[11]郭樹清:《企業(yè)家的作用無可替代》,《人民日報》2016年10月11日第5版。
[12]戴維·蘭德斯等:《歷史上的企業(yè)家精神:從古代美索布達米亞到現(xiàn)代》,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07頁。
[13]戴維·蘭德斯等:《歷史上的企業(yè)家精神:從古代美索布達米亞到現(xiàn)代》,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29—30頁。
[14]威爾·杜蘭特、阿里爾·杜蘭特:《歷史的教訓》,倪玉平等譯,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8頁。
[15]吳慧:《中國古代商業(yè)》,中國經(jīng)濟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頁。
[16]林毅夫:《經(jīng)濟發(fā)展與中國文化的復興》,《北京大學學報》2009年第3期;盛洪:《儒學的經(jīng)濟學解釋》,中國經(jīng)濟出版社2016年版,第199頁。
[17]富蘭克·H·奈特:《風險、不確定性和利潤》,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8頁。
[18]讓·巴蒂斯特·薩伊:《政治經(jīng)濟學概論》,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78—83頁。
[19]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經(jīng)濟學原理》,華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205頁。
[20]約瑟夫·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125—137頁。
[21]同上。
[22]彼得·德魯克:《創(chuàng)新與企業(yè)家精神》,機械工業(yè)出版社2009年版,第36—39頁。
[23]威爾·杜蘭特、阿里爾·杜蘭特:《歷史的教訓》,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0頁。
[24]道格拉斯·C·諾斯:《制度變遷理論綱要》,《改革》1995年第3期。
[25]道格拉斯·C·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制度績效》,劉守英譯,上海三聯(lián)書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3頁。
[26]德魯克:《德魯克:中國的管理者不能依賴進口》,《政工研究動態(tài)》2006年第9期。
[27]阿馬蒂亞·森:《經(jīng)濟學與倫理學》,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52頁。
[28]稻盛和夫:《企業(yè)家精神》,機械工業(yè)出版社2018年版,第14—15頁。
[29]稻盛和夫:《企業(yè)家精神》,機械工業(yè)出版社2018年版,第21頁。
[30]稻盛和夫:《企業(yè)家精神》,機械工業(yè)出版社2018年版,第167—168頁。
[31]《孟子·盡心章句上》
[32]趙士林:《中華傳統(tǒng)文化開講》,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9頁。
[33]《論語·雍也》
[34]樓宇烈:《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中華書局2016年版,第46頁。
[35]《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5年版,第924頁。
[36]周文彰:《略論商業(yè)文明》,《北京聯(lián)合大學學報》,2015年第4期。
[3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頁。
[38]樓宇烈:《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中華書局2016年版,第46頁。
[39]林毅夫:《經(jīng)濟發(fā)展與中華文化的復興》,《北京大學學報》2009年第3期。
[40]稻盛和夫:《企業(yè)家精神》,機械工業(yè)出版社2018年版,第299頁。
[41]《管子·乘馬》
[42]烏麥爾·哈克:《新商業(yè)文明:從利潤到價值》,呂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2—13頁。
[43]烏麥爾·哈克:《新商業(yè)文明:從利潤到價值》,呂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推薦序言1,第1頁。
[44]馬林諾夫斯基:《文化論》,費孝通等譯,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譯序第2頁。
[4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4頁。
[46]Sen,A.K.(2000)Development as Freedom,New York:A.Alfred Knopp:14.
[47]賈春峰:《賈春峰說企業(yè)文化》,中國經(jīng)濟出版社2003年版,第63—65頁。
[48]王建均:《加強企業(yè)文化建設促進非公有制經(jīng)濟健康發(fā)展》,《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4年第4期。
[49]傅立民、賀名侖主編:《中國商業(yè)文化大辭典》上卷,中國發(fā)展出版社1994年版,第5頁。
[50]黃芳等:《茅忠群文化自信與方太戰(zhàn)略創(chuàng)新》,《企業(yè)管理》2021年第2期。
[51]成中英:《C理論:中國管理哲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5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