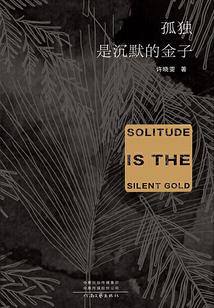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孤獨與沉默的合唱(自序)
人無法戰勝時間
也無法戰勝孤獨
孤獨是沉默的金子
只有讓沉默守在孤獨的身旁
才會聽見孤獨與沉默的合唱
那歌聲如時間般永恒
如火焰,如明月
疫情期間,當我寫下這首《孤獨是沉默的金子》時,我不以為它是一首多么好的詩,但它喚起了我內心洶涌的激蕩,如一道光,在黑暗中閃爍著刺劃而過。這是屬于一個人的精神感悟,也就成為了這本集子的書名。
那時候,每一個人和每一個家庭,都把自己關在房子里,焦慮,恐懼,又滿懷希望。忽然之間,人們意識到在小區最日常的散步,在菜市場最細碎的討價和還價,哪怕是在公共汽車和地鐵上,有人跑步去搶座位,之后又看到有年長的人站在自己面前,最后不得不沮喪地佯裝大度和文明,把座位讓給別的人……多么小而無趣的事,那一刻在沉寂中變得溫暖、誘人而又富有無限的意義。甚至于那些庸俗的細碎,都昭示了生活本身的豐富。
那兩個月,我把自己關在家里,獨自看了一百多部電影,讀了之前想看而沒看的數十位作家的書。從奧登、布羅茨基、艾略特、狄金森,到加繆、馬爾克斯、谷崎潤一郎、遠藤周作、夏目漱石……這些作家的書,有的是粗略地翻閱,有的恨不得把看到的每一句話都用筆畫出來吞進肚里去。而當家里青菜的菜根和方便面的紙袋堆得和書籍同樣高時,我忽然站在那堆書和方便面袋子的中間沉默著。
屋子里散亂不堪。
大街上是虛無的寬闊。
從陽臺下駛過去的公交車,除了司機,整個車廂空無一人,即便如此,司機也還戴著雪白的口罩。幾輛空空蕩蕩的汽車過去后,不僅沒有給我帶來動感和活力,它們叮叮當當孤寂的響聲,反而讓人更加感到罕見的空虛和悲涼。忽然間,我意識到了人的渺小,如一只蟻蟲在浩瀚中獨守著一片空曠和虛無。
就在這一瞬間,我懂得了那些經典電影如《十誡》《悲慘世界》《巴黎圣母院》《奧菲莉婭》……那些充滿激情的小說如《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危險關系》和那些荒誕到令人費解的《變形記》《荒蠻故事》《黑店狂想曲》;還有那些因為費解反而更讓人渴望理解的哲學與思想隨筆——原來一切的寫作、影像、藝術、繪畫,從根本上說,都是在表達創作者被孤獨地糾纏與對孤獨的愛。
為了擺脫這孤獨,我們渴望愛情和激情。為了重回這孤獨,我們在情感中掙扎和爭吵。為了把孤獨從生活中趕走,我們對世俗的熱情猶如寒冬對火的渴望。為了抓住這孤獨,我們創造了藝術的美;為了某種永恒的存在,我們讓孤獨永遠和時間在一起。
生活中,其實只有兩種人,不是男人和女人,而是愛孤獨和不愛孤獨的人。換句話說,是想擺脫孤獨和不想擺脫孤獨的人。而在這兩種人中,想要擺脫孤獨的是絕大多數。而愛著孤獨并愿意守著孤獨的人,是絕少絕少的。所以真正的詩人是罕見的;真正的作家也是罕見的。真正的畫家、藝術家、哲學家,及其偉大的科學家和理想主義者,他們都是絕少而罕見的。
因此,我們不得不贊譽那些為孤獨唱過歌的人。
加西亞·馬爾克斯在《百年孤獨》里說:“生命從來不曾離開過孤獨而獨立存在。無論是我們出生、我們成長、我們相愛還是我們成功失敗,直到最后的最后,孤獨猶如影子一樣存在于生命的一隅。”“孤獨是健康人格養成的基礎,君子慎獨而思無邪。”許多人欣喜這句話,如黑夜欣喜黎明。既然無法擺脫孤獨,那我們應該如何在孤獨中自處?如何與孤獨更好地相處?在孤獨中淬煉與成就自我?胡適也曾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中坦言:“世界上最強有力的人,正是那最孤立的人。”這也就是說,人若能在孤立、孤獨中保持著自律與自省,他的內心就會更有力量、更強大,能讓自己成為一個精神的卓越者。
現在,我們不能說疫情已經過去了,但確實可以說,喧囂、熱鬧的生活重又開始了。散步、購物、吃飯、海闊天空地談論和爭辯,往日生活中被我們不經意遺忘、無視的一切,都又莊重、隆重地回到了我們的生活里。而那站在一堆書籍和一堆方便面袋中間的我,也再一次記起——而且是永遠也不愿忘記的里爾克的詩:
誰此時沒有房子,就不必建造
誰此時孤獨,就永遠孤獨
不管世界如何變幻無常、艱難困苦,如里爾克詩句的啟示那樣,人始終是要守住一些更內心的東西吧。如此,倘若我們不能以孤獨為信仰,那就讓我們仍在生活中,讓孤獨成為沉默的金子。在后疫情時期的人生里,讓人類的個體孤獨,走向更加寬闊的極致。讓那經過孤獨淬煉的人,像一條深沉的河流,永遠朝向大海的方向。
至2020年,我已經離開大學整十年,工作、生活、創作是我人生的三個立足點。辦公室是我走出門的家,而擺放床鋪、衣柜那地方,是我抽離社會獨自存在的桃花園。而在這兩處之間或之外的那個被稱為“詩歌”的去處,是我最隱秘的去向和我靈魂隱私的存放處。我把所有我不愿告人和不敢告人的隱秘都擺放在那兒了。
我非常感謝東莞這一片沃土,是這片豐沃的土地讓我這顆被鳥銜著的種子落下來。這粒種子本不是一粒飽滿到不發芽就會脹破的種子,它多年的飄飛已經接近了枯。可是東莞的水、土和光,竟然讓這粒種子發了芽,竟也在一片綠中有了綠,在一片紅中也有了紅。每每想到我也是東莞的女兒,心里就涌出那粒種子用它的干唇碰到水時那心里怦怦的跳動和感恩。
“何必為部分生活而哭泣,君不見,全部人生都催人淚下。”這是哲學家塞內加留下的名言。可是我不能不為部分生活而哭泣,不能不為我過去走過的路上的一粒石子而感動,不能不為路上我口渴時給我遞水的老人而鞠躬。那路上有孩子莫名地過來拉著我的手,我心里的暗處就有了一束光;有人在我面前的十字路口朝我迷茫的方向指了指,我就在冬日的深處看到春日了。
不是我要寫詩,是那一粒石子就是詩
不是我自己要歌唱,是每一片新芽
在春日的溫暖中自己發出了聲
這本詩集對別人只是一本書,可它在我——是生命,是甘苦,是寒冷中的暖意和黑暗中的光,是一粒種子對一片土地的回報,是一段心靈的細語和一段人生私隱的喃喃之聲。它的出版既是我命運的一個生日,又是我未來的一個起點。所以,我在寫下這些話作為這本書的自序時,我已經看見遠處的門開了,那門前有著一條時隱時現的路。我知道我該出門了,我要從擺著我衣柜的地方離開去,途經許多機關的門扉,然后朝著擺放我靈魂隱私的地方重新去尋找,重新去塑造。
庚子年秋于東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