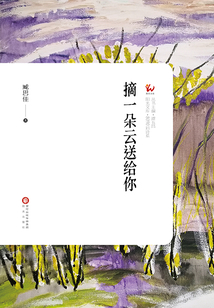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編選說明
譚五昌
在中國當代詩歌發展史上,后起詩人群體的流派與文學史命名一直是一個饒有趣味的詩歌現象。自“朦朧詩群體”的流派命名在詩壇獲得約定俗成的認可與流布以來,“第三代詩人”、“后朦朧詩群體”、“知識分子詩人”、“民間詩人”、“60后詩人”(也經常被稱為“中間代詩人”)、“70后詩人”、“80后詩人”、“90后詩人”等詩歌群體的流派與代際命名,便陸續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如果我們稍微探究一下,不難發現,在這些詩歌流派與代際命名的背后,體現出后起詩人試圖擺脫前輩詩人“影響的焦慮”心態,又在更大程度上,體現了他們進入文學史的愿望。這反映出一個極為明顯的事實:崛起于每一個歷史時期的詩人群體往往會進行代際意義上的自我命名。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朦朧詩群體”為假想敵的“第三代詩人”開創了當代詩人群體進行自我代際命名的先河,流風所及,則是21世紀初期70后詩人、80后詩人等青年詩人群體自我代際命名的仿效行為。90后詩人則是在進入21世紀詩歌的第二個十年后對于80后詩人這一代際命名的合乎邏輯的自然延續。
當下,這種以十年為一個獨立時間單位所進行的詩歌群體代際命名現象,在詩壇上引起了激烈的爭論與內在分歧。從詩學批評或學理層面來看,這種參照社會學概念,并以十年為一個斷代的詩歌代際命名方法的確經不起推敲,因為這種做法的一個明顯后果便是對當代詩歌史(文學史)研究與敘述的高度簡化、武斷與主觀化。因而,我們對于當代詩歌群體的代際命名問題,應該持嚴謹的態度。不過,文學史層面的群體、流派與代際命名問題非常復雜,沒有行之有效的科學命名方法,也很難達成共識。這足以說明文學史命名的艱難。更為常見的情況是,一個詩歌流派或詩人代際的命名(無論出自詩人之口還是批評家之口),往往是一種策略性的、權宜之計的命名,從中體現出命名的無奈性。如果遵循這種思路,我們便會發現,60后詩人、70后詩人、80后詩人、90后詩人這種詩歌代際命名,也存在其某種意義上的合理性。因為就整體而言,他們的詩歌創作傳達出了不同的審美文化代際經驗。簡單說來,60后詩人骨子里對于宏大敘事與歷史意識存在潛意識的集體認同,他們傳達的是一種整體主義的審美文化經驗。70后詩人則以叛逆、激進的寫作姿態試圖打破意識形態的束縛(最典型的是“下半身寫作”現象),他們在歷史認同與個體自由之間劇烈掙扎,極端混雜、矛盾的審美經驗使得這一代詩人的寫作處于某種過渡狀態(當然,其中的少數佼佼者很好地實現了自己的文學抱負)。而80后詩人興起于21世紀初的文化語境之中,他們這一代的寫作則是建立在70后詩人掃除歷史障礙的基礎上,80后詩人的寫作立場真正做到了個人化,他們在文本中可以自由展示自己的個性,沒有任何歷史包袱,能夠在語言、形式與經驗領域呈現自己的審美個性,給新世紀的中國新詩提供了充滿生機的鮮活經驗。繼之而起的90后詩人繼承了80后詩人歷史的個人化的核心審美原則,并在語言形式與情感內容層面,表現出理論上更為自由、開放的可能性。
目前,80后詩人、90后詩人是新世紀中國新詩最為新銳的創作力量,而且這兩撥詩人在詩學理念與審美風格上存在較多的交集(簡單說來,90后詩人與80后詩人相比最為鮮明的一個特點是:90后詩人的思想觀念更為開放與多元,他們的寫作受到新媒體的影響要更為深刻一些)。因而,從客觀角度而言,80后詩人、90后詩人的詩歌寫作頗具文學史價值與意義。
因此,陽光出版社推出《陽光文庫·8090后詩系》,體現了陽光出版社超前的文學史眼光與出版魄力,令人無比欽佩,其價值與意義不言而喻。
2020年6月25日(端午節)凌晨寫于北京京師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