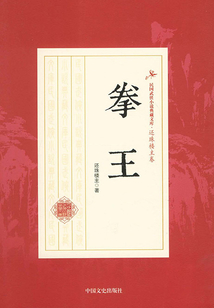最新章節(jié)
- 第14章 絕處喜逢生 甫得知音 又飛勞燕
- 第13章 燃燈取寶 再戮兇頑
- 第12章 古洞飛尸 初驚異事
- 第11章 山腹中的笑聲
- 第10章 逢四害 老武師喪命 報親仇 小雙俠探山
- 第9章 大鵬十八式擒拿手
第1章 還珠樓主小傳
還珠樓主,原名李善基,后更名李壽民;筆名還珠樓主,晚年又改筆名為李紅。四川長壽縣人。生于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同胞兄弟中排行老大,在叔伯兄弟中排行老七。李家世代為官。其父元甫,進(jìn)士出身,光緒年間官至蘇州知府,為人清廉正直,厭惡官場骯臟黑暗而棄官歸里,設(shè)館授徒。其母周家懿,四川成都人,也是大家閨秀,知書通文。由于父母教子嚴(yán)厲,李壽民又聰明過人,三歲開始讀書習(xí)字,五歲便能吟詩作文,七歲能寫丈許長對聯(lián)。九歲時更寫出了五千言的《“一”字論》長文,被譽為“神童”,并獲得了長壽縣衙頒發(fā)的“神童”大匾,此匾高高懸掛在李家祠堂。可知李壽民具有驚人的天賦且受到良好的家庭啟蒙教育,這也是他后來成為著名作家的基礎(chǔ)。不幸十二歲喪父,家道中落,家計難以維持。其母攜帶李壽民及兩弟、一妹,順江而下,至蘇州投奔親友,幸得其父之門生故舊慷慨周濟(jì),勉強(qiáng)度日。李壽民也得以就讀于著名的草橋中學(xué)(今蘇州第一中學(xué)),學(xué)習(xí)成績一直高出儕輩,名列前茅。
在此期間,李壽民墜入了初戀的情網(wǎng)。戀人名叫文珠,比李壽民大三歲,為鄰右之女。雖非絕代佳人,卻也相貌清秀,性格溫柔,尤善琵琶彈奏。李壽民愛聽文珠彈琵琶,文珠則愛聽李壽民擺四川“龍門陣”。一來二往,兩小無猜,愛苗在不知不覺中茁壯成長。然而這段戀情卻只見開花而未能結(jié)果。原因在于李壽民家境貧寒,又是長子,故從二十二歲起,便不得不停止學(xué)業(yè),為養(yǎng)家糊口而開始浪跡江湖。起初尚與文珠有鴻雁傳書,漸至魚沉雁杳,后才得知文珠竟然淪落到煙花柳巷。這是李壽民的終生之痛,致使他在很長時間內(nèi)不作燕婉之想。據(jù)說他的小說《女俠夜明珠》,就是為紀(jì)念文珠而寫的。
李壽民的首個落腳點是天津,而天津也沒有辜負(fù)他的期望,不僅使他找到了終身伴侶,而且成為他作家生涯的起點。李壽民初到天津,經(jīng)人介紹,充任天津警備司令傅作義的中文秘書,因其才氣橫溢,中文功底深厚,深得傅作義賞識。傅作義的英文秘書為段茂瀾,是留英學(xué)生,與李壽民一見如故,義結(jié)金蘭。由于李壽民生性散漫,不慣軍旅生活,且性格強(qiáng)傲,不肯唯命是從,有時甚至敢于頂撞上司,故不足一年,便拂袖而去,據(jù)說還留下一首打油詩,對傅作義冷嘲熱諷。傅作義也有過人度量,一笑了之。此后李壽民的職業(yè)很不固定,做過宋哲元冀察政務(wù)委員會的秘書,天津《天風(fēng)報》的編輯、記者,還為名伶尚小云寫過劇本并結(jié)為金蘭之契,又曾以“木雞”(取意于典故“呆若木雞”)和“壽七”(“壽”指長壽縣,“七”指排行老七)的筆名發(fā)表短文,接著又進(jìn)入天津郵政局,當(dāng)了一名小職員。由于小職員的薪金微薄,不足以養(yǎng)家糊口,又經(jīng)人介紹,兼做天津大中銀行老板孫仲山公館的家庭教師,為其子女教授國文和書法。不料這一來,卻給李壽民帶來了桃花運,成為他一生的一個轉(zhuǎn)折點。
孫仲山是一個暴發(fā)戶,他與李壽民為小同鄉(xiāng)。當(dāng)李壽民進(jìn)入孫公館時,正是孫仲山生意的鼎盛時期,其大中銀行在全國十三個城市開有十三個分行,其帶花園的洋房豪宅在天津英租界馬場道占地達(dá)二十余畝。孫家二小姐孫經(jīng)洵,比李壽民小六歲,雖貌不驚人,但溫文爾雅,氣度非凡,性格堅強(qiáng)。起初,李壽民因初戀的隱恨未消,心如止水,對孫經(jīng)洵并未在意;而孫經(jīng)洵乃大家閨秀,對于李壽民這個憨厚的老師,也沒有一見鐘情。然而不知為什么,兩人之間好像有一種無形的引力,既攪動了李壽民止水般的心境,也攪亂了孫經(jīng)洵小姐矜持的芳心。他們在不知不覺之中,同時陷入了情網(wǎng)。
那時正值民國初年,社會風(fēng)氣雖然有所開放,但封建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因此他們的戀愛仍如張君瑞與崔鶯鶯那樣,只能在暗中進(jìn)行。然而天下沒有不透風(fēng)的墻,戀情終于被孫仲山發(fā)現(xiàn)。孫仲山首先以“門不當(dāng),戶不對”以及“師生相戀,敗壞家風(fēng)”來訓(xùn)斥女兒,結(jié)果無效;然后又以“只要李先生與小女一刀兩斷,要多少錢不成問題”利誘李壽民,又遭到李壽民嚴(yán)詞駁斥。于是孫仲山便下了個殺手锏,將李壽民炒了魷魚,以為如此便可斬斷這對戀人的情絲。
然而愛情猶如燎原之火,是很難撲滅的。他們居然想出了一個傳遞情書的絕妙辦法:雙方將情書用橡皮膏貼在孫仲山上下班乘坐的汽車號牌后面,李壽民等孫仲山上班后到大中銀行門口取信,孫經(jīng)洵則在孫仲山下班回家后取信。孫仲山做夢也沒有想到,他的專車倒成了女兒與李壽民的郵車,自己也被迫當(dāng)了一回紅娘。終于有一天,事情敗露。孫仲山自然怒不可遏,一個耳光將女兒打倒在地。這一耳光不僅沒有打消孫經(jīng)洵婚姻自主的決心,反而打得她離家出走。
孫仲山在氣走女兒后仍不善罷甘休,必欲置李壽民于死地。他仗著財大氣粗,買通了英租界工部局,將李壽民投入監(jiān)獄。幸虧段茂瀾精通英文,李壽民又未犯法,經(jīng)段茂瀾從中斡旋,李壽民便獲釋放。孫仲山一計未成,又施一計:以“拐帶良家婦女”的罪名,將李壽民告到天津法院。1930年11月的一天,法院開庭審判。因為案件屬于桃色事件,控告人又是大中銀行老板,故記者云集,法庭座無虛席。但孫仲山不敢出庭,派其長子孫經(jīng)濤作為代表。當(dāng)審判到關(guān)鍵時刻,孫經(jīng)洵突然出庭做證,大聲說道:“我今年二十四歲,早已長大成人,完全可以自主;我與李壽民也是情投意合,自愿結(jié)合,怎么能說‘拐帶’?”此話一出,全場嘩然。本來就同情妹妹的孫經(jīng)濤,更是無言以對。于是法官當(dāng)即宣判李壽民無罪。此案在當(dāng)時的天津曾經(jīng)轟動一時,家喻戶曉。李壽民后來即以此事為素材,寫成了小說《輪蹄》(又名《征輪俠影》),這也是李壽民唯一的一部言情小說。此案雖了,但翁婿之間的怨恨卻終生未解,互不往來。據(jù)說《蜀山劍俠傳》中那個生相丑惡、專吸人血而神通廣大的綠袍老祖,就是影射孫仲山的,足見李壽民對岳丈的怨恨之深。
李壽民為了與孫仲山賭氣,也為了報答孫經(jīng)洵堅貞不渝的愛情,發(fā)誓要辦一場體面的婚禮,因此在官司打贏后并沒有馬上成婚,而是想方設(shè)法賺錢。直至1932年2月5日,李壽民與孫經(jīng)洵才正式結(jié)婚。婚前孫經(jīng)洵特至醫(yī)院做了婦科檢查,證明身為處女,并登報聲明。新居選在天津日租界秋山街,尚小云贈送了全套家具。婚禮采用西洋式,相當(dāng)隆重,主婚人為段茂瀾,為新娘執(zhí)婚紗者為袁世凱的孫女袁桂姐(后來認(rèn)為義女)。婚后不論生活多么坎坷艱難,夫妻始終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并養(yǎng)育了七個子女。李壽民為了感激至友段茂瀾,七個子女的名字皆用段茂瀾之字“觀海”中的“觀”字,即觀承、觀芳(女)、觀賢(女)、觀鼎、觀淑(女)、觀洪、觀政(女)。
1932年是李壽民時來運轉(zhuǎn)的一年,在這一年,紅鸞星和文昌星同時在他頭頂上高照。新婚不久,天津《天風(fēng)報》老板鑒于他曾在該報做過編輯和記者,又不時發(fā)表短文,文筆優(yōu)美動人,便請他寫一部連載小說。李壽民雖未寫過小說,卻自信可以勝任,于是一口答應(yīng)。寫什么呢?他立即想到了武俠小說。首先,武俠小說在當(dāng)時的北方大行其道,十分流行;李壽民也耳濡目染,十分熟悉。其次,李壽民從七歲起,三上峨眉,四登青城,總共在山上生活過一年半,對這兩座名山的一丘一壑、一澗一水、一草一木、一觀一寺,無不了如指掌,并做過詳細(xì)筆記,畫過游覽草圖;同時結(jié)識了不少和尚道士,聽了不少新奇故事,還學(xué)會了練功練氣。這一切都是武俠小說的極好素材。那么使用什么筆名呢?李壽民覺得“木雞”只是自我調(diào)侃,“壽七”又有點粗淺,一時委決不下。這時孫經(jīng)洵說話了:“壽民,我知道你心中有座樓,那里面藏著一顆珠子,就用‘還珠樓主’作筆名吧。”“還珠”既是一個典故,又暗指李壽民的初戀對象文珠,可謂妙不可言。李壽民既佩服愛人的才思,又感激她對自己的理解。因此從當(dāng)年的7月開始,便以還珠樓主的筆名,在《天風(fēng)報》上連載《蜀山劍俠傳》。不料作品一經(jīng)發(fā)表,《天風(fēng)報》的發(fā)行量便直線上升。不久,天津勵力印書局(后改名勵力出版社)又將該書結(jié)集出版,銷售依然火爆。于是還珠樓主一鳴驚人,文名鵲起。從此一發(fā)不可復(fù)收,此書斷斷續(xù)續(xù)寫了近二十年,總字?jǐn)?shù)將近五百萬,還沒有寫完。《蜀山劍俠傳》一炮打響后,又陸續(xù)推出了《青城十九俠》《蠻荒俠隱》《邊塞英雄譜》《云海爭奇記》等,皆大受歡迎。
李壽民為了更大的發(fā)展,便帶著天津給他的兩大禮物——終身伴侶和作家名望,移居古都北平,并置了房產(chǎn),成為職業(yè)作家,作品源源不斷地問世。除了續(xù)寫在天津的未完之作外,又陸續(xù)推出了《輪蹄》《皋蘭異人傳》《天山飛俠》[1]等。至日寇侵占北平時,李壽民已經(jīng)推出了八部小說,成為一位享譽平津的著名作家了。然而正是由于他的名聲,為他帶來了一場災(zāi)難。先是漢奸周大文請他出任日敵電臺偽職,被他一口拒絕。接著,時任偽華北教育總署督辦的周作人親自出面勸駕,仍遭拒絕。事有湊巧,有徐姓出版商看準(zhǔn)了出版李壽民的作品可獲厚利,欲將其出版權(quán)從天津勵力出版社挖過來,也遭到了李壽民的拒絕。姓徐的一怒之下,便托其為日寇當(dāng)翻譯的親戚,在日寇面前誣陷李壽民為“重慶分子”,加上李壽民兩次拒絕出任偽職,于是被日寇投進(jìn)了牢獄。在獄中的七十多天里,李壽民受盡了各種酷刑,如鞭笞、灌涼水、用辣椒面揉眼睛等。李壽民的獲釋也頗有戲劇性,除了孫經(jīng)洵四處求親托友斡旋外,還與他精通卜卦有關(guān)。一個日軍大佐請李壽民為其算卦,竟算得絲毫不差。加之日本人又找不出李壽民為“重慶分子”的任何證據(jù),才被釋放。李壽民本來頗通氣功,身強(qiáng)體壯,經(jīng)過七十多天的酷刑折磨,身體幾乎垮掉。其視力損傷尤為嚴(yán)重,以致后來只能寫大字,不能寫小字,創(chuàng)作全憑口述,由秘書記錄。
李壽民出獄后,略作休養(yǎng),為了躲避日寇和漢奸的再次迫害,便只身逃到上海。上海人本來熱衷于言情小說和社會小說,所以此前李壽民的小說只在北方流行,在上海少有讀者。因此李壽民初到上海時,僅靠賣字糊口,無力養(yǎng)家。后被頗有眼光的上海正氣書局老板陸宗植發(fā)現(xiàn),為他安排了住處,請他繼續(xù)寫作,并約定由正氣書局全權(quán)出版。于是李壽民迎來了第二次創(chuàng)作高潮,除了續(xù)寫平津未完之作外,又推出了二十幾部新作,如《武當(dāng)異人傳》《柳湖俠隱》《峨眉七矮》《蜀山劍俠新傳》《北海屠龍記》《虎爪山王》《黑孩兒》《青門十四俠》《關(guān)中九俠》《萬里孤俠》《蜀山劍俠后傳》等。一向熱衷于言情小說和社會小說的上海人,像突然發(fā)現(xiàn)了新大陸一般,一下子迷上了李壽民那充滿了奇思妙想的新神魔小說和新武俠小說,以至出現(xiàn)了“還珠熱”的盛況。李壽民在上海的知名度不僅超過了平津,而且蓋過了所有上海作家。由于他的小說都是邊寫邊分集出版,所以每當(dāng)新作一出版,書店門口便會排起長龍。他的巨著《蜀山劍俠傳》還被改編為京劇連臺戲,在大舞臺久演不衰。由于作品廣受歡迎,供不應(yīng)求,李壽民子女又多,家累甚重,不得不同時口授幾部小說,每天都在一萬字以上。而各部小說的眾多人物和故事(如《蜀山劍俠傳》有上千人物和上百故事)卻井井有條,紋絲不亂,這不能不令人佩服其才情出眾,思維敏捷,記憶力驚人。這種巨大的壓力使他染上了煙霞癖,成為他后來生活的一大禍害。
直到抗戰(zhàn)勝利后,社會初步安定,李壽民的稿酬也相當(dāng)豐厚,才把家眷由北平接到上海,全家得以團(tuán)聚。
然而正當(dāng)李壽民躊躇滿志的壯年時期,其創(chuàng)作事業(yè)也進(jìn)入如火如荼的鼎盛時期,卻因時局的巨變而使其創(chuàng)作之路走到了盡頭。一向風(fēng)行民間的武俠類小說,似乎突然變成了洪水猛獸,“談武俠而色變”的氣氛籠罩于九州大地,圖書館也通統(tǒng)將其束之高閣,禁止借閱,以至于武俠類小說完全銷聲匿跡。這就是李壽民的大部分小說皆被腰斬、成為斷尾蜻蜓的唯一原因。這是李壽民無可彌補的遺憾,也是中國文學(xué)和中國讀者無可彌補的遺憾!
李壽民的最后十來年,一度暫居蘇州,旋又移居北京,都是在惶恐中度過的。他雖然沒有被戴上什么政治“帽子”,并前后任上海天蟾京劇團(tuán)、總政京劇團(tuán)、北京京劇三團(tuán)的編劇及北京市戲曲編導(dǎo)委員會委員,為劇團(tuán)寫過不少劇本,但似乎總有一種無形的巨大壓力籠罩在他的頭上,壓得他喘不過氣來;他的數(shù)十部小說似乎都變成了深重的罪孽,他所塑造的那些人物形象更像是變成了憧憧魔影,使他揮之不去。于是他把自己的作品全部付之一炬,一本不剩。這種恐懼感和負(fù)罪感,使他猶如驚弓之鳥,不得不“夾著尾巴做人”。這倒幫了他一個大忙,使他在那場“放長線釣大魚”的政治陰謀中沒有上鉤,保持沉默,從而僥幸成為“漏網(wǎng)之魚”,逃過了一劫。然而最終還是沒有逃過那“批判的武器”的致命一擊。1958年6月,一篇《不許還珠樓主繼續(xù)放毒》的文章,便把他打成了腦溢血,雖經(jīng)搶救脫險,終造成左半身偏癱,生活無法自理,自此輾轉(zhuǎn)病榻兩年有余。當(dāng)他口述完歷史小說《杜甫》,秘書以工整的鋼筆小楷記錄下杜甫“窮愁潦倒,病死舟中”那一段的描寫時,李壽民對妻子說:“二小姐,我也要走了。你多保重!”第三天,即1961年2月21日,還珠樓主終于與世長辭,終年只有五十九歲,恰與一生坎坷的中國“詩圣”杜甫同壽。
“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杜甫《戲為六絕句》其二)李壽民雖然一生坎坷,結(jié)局凄慘,但他無愧于中華民族,無愧于古老的文明祖國。他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時間里,創(chuàng)作了總計達(dá)一千七百萬字的四十部小說,還有幾十個京劇劇本。他的《蜀山劍俠傳》更榮登于香港和內(nèi)地兩個專家組評出的兩個“二十世紀(jì)中文小說一百強(qiáng)排行榜”之上。他創(chuàng)造了一種無與倫比的新神魔小說,為中國小說增添了一枝璀璨的奇葩。他的小說曾為一代人所著迷,并將永世流傳。
裴效維
2011年12月15日于北京蝸居
注釋
[1]后經(jīng)增訂,更名為《冷魂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