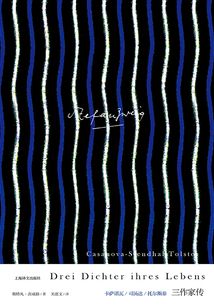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作者的話
真正研究人類的是人。
蒲伯[1]
我試圖利用《世界建筑大師》這套叢書說明重要人物類型所具有的創造性的精神意向,并反過來通過這些人物形象闡釋這些人的類型。在這套叢書里,這本第三卷是前兩卷的對立面,同時又是前兩卷的補充。《與魔搏斗》告訴人們,荷爾德林、克萊斯特和尼采是受魔力驅動的悲劇品格的三種變化的基本形態。這種品格既超越自身,也超越現實世界,是與無限的事物相抗衡的。《三大師傳》說明巴爾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敘事文學世界創造者的典型。他們在自己的長篇小說宇宙里安排了一個業已存在的現實之外的第二現實世界。《三作家傳》的生活道路不像第一卷里的三人那樣進入無限,也不像第二卷三人那樣通向現實世界,而是僅僅回歸自身。這三位作家都本能地認為,他們的藝術的重要任務不是描摹宏觀世界,反映五彩繽紛的豐富生活,而是把個人的“自我”的微觀世界擴展成大世界。因此,在他們看來,沒有任何現實比他們個人生活的現實更重要。世界上有創造性的作家,總是把他的“自我”融解在他所描述的客觀事物中,直到隱蔽不見(像在最杰出的莎士比亞那里一樣,他已經從普通的人變成神話里的人),而主觀的感覺者,內向的、面向自我的作家,則是讓人世的一切終止在他的“自我”當中,他首先是他個人生活的塑造者。無論他選擇哪種體裁,戲劇也好,敘事詩也好,抒情詩也罷,自傳也罷,他總要不自覺地把他的“自我”作為媒介和中心寫進任何一部作品里去,在任何一種敘述中,他首先描述的都是他自己。以卡薩諾瓦、司湯達和托爾斯泰這三個人物為例說明這種研究自我的主觀主義的藝術家類型及其重要的藝術體裁——自傳,是這套叢書第三卷的意圖和課題。
我知道,把卡薩諾瓦、司湯達和托爾斯泰這三個名字放在一起,初聽起來并不令人信服,而是令人驚異。首先,人們想像不出他們的價值怎么會相等,像卡薩諾瓦這樣一個放蕩的不道德的騙子怎么能跟托爾斯泰這樣一位英勇的倫理學家、完美的作家同日而語呢?事實上,把他們集中在一本書里并不等于把他們并列在同一精神水平上;相反,這三個名字象征著一級比一級高的三個不同階段,是同一類性格的不斷提高的主要形態。我要再重復一句,他們代表的不是三種同一價值的形態,而是同一種創造性功能,即描寫自我的三個不斷提高的階段。卡薩諾瓦只代表第一個最低級的原始階段,也就是簡單的描寫自我的階段。在這種描寫中,一個人還是把生活與外部感性的、實際的經歷等量齊觀,只報道他自己生活的自然過程和事件,對它們不作任何評價,對自己也不進行深入的研究。到了司湯達,描述自我就已經達到了一個更高的階段,即心理描寫的階段。這種描述不再滿足于單純的報道,簡單的履歷,這個“自我”變得急于想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他觀察他個人原動力的必然過程,他尋找自己做與不做的原因,尋找靈魂里動人心魄的戲劇性的東西。這樣便開始有了一個新的觀察方法,即用兩只眼睛進行觀察,這個“自我”是主體同時也是客體,寫的是內心與外部的雙重的傳記。這個觀察者自己,以及這個感覺者自己的感情——形象地進入他的觀察范圍的不僅有世上的生活,也有心理的生活。在托爾斯泰這個類型里,靈魂的自我觀察達到了觀察的最高階段,因為這種觀察同時變成了倫理和宗教上的自我描寫。這位精確的觀察者描述他的生活,這位精細的心理學家描述感受引起的反射。此外,一個自我觀察的新要素,即良知的嚴峻的眼睛,觀察著每一句話的真實性,每一個想法的純潔性,每一個感覺的持續作用的力量。于是,這種自我描述就超出充滿好奇心的自我檢驗,變成了一種自我審判。這位藝術家在描述自我的時候,不僅要問他的現世表現的類別和形式,而且要考慮他的現世表現的意義和價值。
這種類型的描述自我的藝術家善于把他的“自我”塞進任何一種藝術形式,但他只在一種形式中才能完全實現自我,那就是自傳,在特有的“我”的內容全面的敘事文學作品中。他們當中的每一個人都不自覺地致力于這種藝術形式,不過能達到目的的卻寥寥無幾。在一切藝術形式中,自傳是極少可能完滿成功的,因為它是一切藝術形式中最有責任心的一種。嘗試這種藝術形式的人是極少的(在浩如煙海的世界文學作品中幾乎只有十幾部具有重要精神價值的作品),嘗試用這類作品進行心理觀察的人也是極少的,因為這種形式多半會不可避免地從通行無阻的文學領域墜入心理學最深層的迷宮里去。在一篇簡短的前言里,自然只能大概地談一談自我描述的可能和限度,只能像演奏序曲一樣提綱挈領地說一說對這個問題的主要想法。
不帶偏見地看,自我描述總是每個藝術家最本能最輕松的任務。這位劇作者對誰的生活能比對自己的生活更了解呢?對他來說,個人生活的每一件事都是預料之中的,最隱秘的事情都是已知的,內心埋藏最深的東西也都再明顯不過。因此,為了講述他現在和過去生活的真情,他無需花費別的氣力,只需翻開記憶的篇章,記錄下生活的事實就行了——就像一幕戲,無需費很大氣力,只要在劇院里把遮住安排停當的場景的幕布拉開,讓自己和世界之間閉合的四壁遠離就行了。而且遠不止如此!攝影術對畫家才干的要求很少,因為這是一種沒有想像力的、單純機械地描繪一種秩序井然的現實,同樣,自我描述這種藝術似乎也根本不需要藝術家,只需要真正的記錄者。從原則上說,甚至每一個人都能成為他個人的自傳作者,都能以文學筆法描寫他的命運和他所遭遇的危險。
但歷史教導我們,一個普通的自我描述者從未有過成功的經驗,他所做的不過是證實那些他偶然碰到的事實而已。與此相反,從自己內心來創造內在靈魂的圖畫,則永遠要求有洞察力的熟練的藝術家,即使在他們中間也只有極少數能夠勝任這種不尋常的責任重大的嘗試。在值得懷疑的撲朔迷離的回憶中,沒有一條路是行不通的,正如一個人從他顯而易見的表面墜入他內心的黑暗王國,從他生機勃勃的現在墜入他荊棘叢生的過去。他必須進行多少冒險才能越過自己的深淵,在自我欺騙和任意忘卻的狹窄泥濘的通道上摸索著走進最后的孑然一身的孤獨——正如浮士德在奔向眾女神的道路上那樣,他個人生活的圖畫只作為他從前真正生活的象征,毫無生氣地靜止地“懸浮著”!在他有資格說出“我已認清我自己的心”這句莊嚴的話之前,他需要有多么大的忍耐和自信!這種內心的東西從內心深處復歸,然后又上升到進行著抗爭的形象世界,從自我觀察進入自我描述,是多么艱難啊!自我描述的成功率是很低的,這就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了這種大膽行為的不可估量的困難。用書面語言描繪出個人的活靈活現的畫像的作家是屈指可數的,即使在這種相對完成的作品里也存在多少漏洞和缺陷,多少人工的補充和掩飾啊!在藝術中,恰恰是這種最貼近自身的東西是最難的,這種貌似容易的事情是最艱巨的任務。
藝術家最難于真實塑造的不是他同時代和任何時代的人,而是他的“自我”。
然而,是什么一再迫使一代又一代的嘗試者去擔負這幾乎不能完成的任務?無疑是有一種基本動力強加在人的身上:這就是使自我不朽的天然要求。每一個人都是數十億分子中的一個分子,這個分子被置于流動之中,被罩上轉瞬即逝的陰影,被不停奔騰的時間長河沖走;這時,他(由于不朽的直覺)總是不知不覺地想方設法把往昔和一去不再復返的東西保存在某種長久的超越他生命的遺跡里。為他人作證和為自己作證,歸根到底意味著一種功能,一種同樣的原始的功能,一種同樣的努力:把轉瞬即逝的痕跡遺留在堅持不懈地繼續生長的人類大樹的主干里。因此,每一篇自我描述都只不過是這種自我作證愿望的最鮮明的形式,而自我描述的初次嘗試往往缺乏形象的藝術形式,不使用文字;或是墳墓上疊起層層的巨石,或是在墓碑上用笨拙的楔形物頌揚真相不明的業績,或是在樹皮上刻下累累刀痕——個別人的第一次自我描述就是用這種方石塊一類的語言通過數千年空曠的空間向我們述說。這些行為早已無法考察了,那已化作泥土的一代人的語言也變得無法理解了;但他們的一種沖動卻明白無誤地表現了出來,這就是塑造自我和保存自我的沖動,就是通過個人的呼吸把某一個人曾存在過的痕跡轉給世世代代活著的人。這種不自覺的、模糊的追求自我永存的意志,便是一切自我描述的動機和開端。
后來,在一千幾百年以后,有覺悟和有知識的人類才在那種還是赤裸裸的模糊的表現自我的傾向之外產生了第二意志,這就是個人的認識自我的要求,為了了解自我而說明自我的要求:自我觀察。正如奧古斯丁[2]巧妙地說出的那樣,如果一個人“把自己變成問題”,把自己變成他所尋找的屬于他的答案,那么,為了更清楚更全面地認識自己,他就會像展開一張地圖一樣把他一生的道路展示在自己眼前。他闡釋自己不再為了別人,而是首先為了他自己。這時便出現了一個分岔路口(這種岔路口就是今天也還可以在每一部自傳里看到):是描述生活,還是描述經歷;是闡明別人,還是闡明自我;是客觀的外部的自傳,還是主觀的內心的自傳——一句話,是客觀地報告他人,還是主觀地報告自我。一部分人永遠傾向于公開表明,他們采取懺悔這種基本形式,向教區教會懺悔或作書面懺悔;另一部分人則作思想的獨白,大都采取寫日記的方式。只有像歌德、司湯達和托爾斯泰那種真正的全才,才會在這里嘗試一種完美的結合,使自己在兩種形式中永生。
然而,觀察自我,還只是一個單純做準備的、無需考慮的步驟:每一件真實的事物只要是恰當的,它就很容易保留真實的面貌。藝術家真正的困難和痛苦是在想把這種真實事物轉達給別人的時候開始的,于是,便要求每個自我描述者都具有坦誠的勇氣。因為,很自然,一方面有一種相互交流的精神壓力,迫使我們像對待親兄弟一樣把我們的往事告訴所有的人;同時另一方面在我們心里又有一種要求保存自我、隱瞞自我的對抗性的基本意志在起作用。這種意志在我們身上是通過羞慚表現出來的。就像一個女人由于天生的要求愿意獻出身體,同時又由于清醒感情的相反意志而力爭保持自己的貞操一樣,在思想中,那種信賴世人的懺悔意志也在與勸導我們嚴守自己秘密的內心羞愧進行搏斗。因為這個最虛榮的人本人(而且恰恰是他)認為自己并不是完人,不是像他想在他人面前表現的那樣完美無缺。因此,他很想讓他的丑惡的秘密、他的不足之處和他的狹隘淺薄跟他一起滅亡,同時他又希望他的形象活在人間。可見,羞慚是每部真正自傳的永久的敵人,因為羞慚企圖以嫵媚的態度誘使我們不去真實地描述自我,而是按照我們希望被看到的樣子去描述自我。羞慚將施展各種各樣的陰謀詭計,引誘決心坦誠面對自己的藝術家隱瞞他心底的秘密,弱化他的于己有害的東西,遮掩他最機密的事情。羞慚不自覺地教我們用雕塑家的手刪去或以騙人的方式美化有損個人形象的瑣事(在心理學意義上卻是最本質的東西!),通過光與影的巧妙安排把性格特征重新修飾得更加理想。但誰要是意志薄弱,向羞慚的諂媚要求讓步,那他就只能神化自我或維護自我,而不能完成自我描述。因此,每一部誠實的自傳并不要求單純的漫不經心的敘述,它要求時刻留神虛榮心闖入,要求嚴防按照個人塵世本性不可遏止的意向,把自己的形象修飾成使世人滿意的樣子。正是在這里,為了達到藝術家的誠實,還需要一種特殊的、千百萬人中難得一見的勇氣,因為恰恰在這里,除了這個獨特的“自我”,沒有任何人考察和檢驗描述的真實性——這個“自我”是個人面貌出現的證人和法官,又是起訴人和辯護人。
這場不可避免的反對自我欺騙的斗爭,至今沒有完善的裝備和防護手段。正如在武器手工業那里永遠需要找到一種穿透力強的槍彈來對付堅固的胸甲,對付欺騙也必須學會各種心理學知識。如果一個人決心把欺騙關在門外,欺騙就必須變得兇險如蛇般圓滑,它會從縫隙里爬進去。如果一個人為了對付欺騙而從心理學上透徹研究欺騙的陰險狡詐,那么,欺騙就要學會更巧妙的佯攻和抵擋新戰術;欺騙將像一頭豹狡猾地藏在暗處,以便在對方不加防御的時刻陰險地猛撲過去。他們自我欺騙的技巧恰恰是憑借一個人的認識能力和心理變化才變得更精到更高超。只要一個人粗魯笨拙地操縱真相,他的欺騙也就永遠是笨拙的,容易被識破的。在精細的識別能力強的人那里,他的謊言才變得更巧妙,然后又在更有識別能力的人那里被識破,因為謊言往往躲在最使人迷亂最危險的騙人的形式里,而它們的最危險的假面具又總是貌似真誠的。正如蛇最喜歡藏在峭壁和巖石下面,最危險的謊言最喜歡在偉大的慷慨激昂的、貌似英雄主義的豪言壯語的陰影里筑巢。在讀每部自傳時,人們恰恰必須對講述者最勇敢最令人驚異地暴露自己和為難自己的地方特別留神,看這種懺悔的粗野方式是否恰恰企圖把一種比較隱秘的自我隱藏在人們捶胸頓足的大喊大叫后面。可以說,在自我懺悔中有一種幾乎永遠暗示內心隱秘弱點的大力士氣質。一個人寧肯輕輕松松地暴露自己最可怕、最令人厭惡的東西,也不去泄露可能使自己變得可笑的最微不足道的本質特征,這便是羞慚的基本秘密。害怕別人譏笑,隨時隨地都會把一部自傳引上最危險的歧途。甚至像讓—雅克·盧梭這樣真正愿意透露真情的人也是以一種令人懷疑的徹底坦白的態度痛斥他性愛方面一切離經叛道的行為,并且懊悔地承認,他這位著名教育小說《愛彌兒》的作者,讓自己的子女在育嬰堂里變壞了。不過事實上,這種貌似大膽的供認只不過是掩蓋那些更具人性卻使他感到為難的供認,他很可能從來就沒有孩子,因為他沒有能力生育孩子。托爾斯泰寧愿在他的懺悔里痛斥自己是嫖客、兇手、竊賊、奸夫,而不肯用一字一句承認這樣一件小事:他一生中對他的偉大對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判斷都是錯誤的,并向來對后者毫不寬容。把自己隱藏在一種自白的背后,而且恰恰在懺悔中隱瞞自己的劣跡,是在自我描述中進行自我欺騙的最巧妙、最有欺騙性的陰險手段。戈特夫里德·凱勒曾就這種聲東擊西的手段憤怒地譏諷過所有的自傳作品。他寫道:“這個人承認七種大罪,可是有意隱瞞他左手只有四個手指頭;那個人講述和描寫他的一切色斑和后背上的小胎痣,惟獨對他所作的一次使他良心不安的偽證諱莫如深。如果我把所有的自傳與他們視為水晶般透明的坦誠作一比較,我就會自問:有坦誠的人嗎?可能有坦誠的人嗎?”
事實上,要求一個人在他的自我描述里寫出絕對的真實情況,就像要求塵世間有絕對的正義、自由和盡善盡美一樣,可以說是無稽之談。要始終一絲不茍地堅持最激情滿懷的決心,最堅決的志向,自古以來就是不可能的,因為一個不爭的事實,我們根本不具備掌握真實情況的可靠器官,我們在開始講述自我之前,就已經在真實的經歷方面被我們的記憶欺騙了。因為我們的記憶絕不像官僚機構里整理得井然有序的卡片柜,生命中的一切事實都寫成了文字,歷史可靠而不可更改,一幕一幕地像文獻記錄那樣儲存在那里。我們所說的記憶,就裝在我們血液的通道里,并被血液通道的浪頭漫過,它是一個活的器官,聽命于一切變化,它不是冰箱,不是固定不變的保存器,可以在里邊保持每一種過去感受的天然特性,原始氣味和它存在過的形式。在這種流動和奔騰流逝的東西里(這種東西,我倉促地給它取了一個名字,叫做記憶),各種事件像小溪底部的卵石似的移動著,它們相互磨擦碰撞,直至變得不可辨認。它們相互適應,得到重新安排,以無比隱秘的保護形態采納符合我們意愿的形式和色彩。在這種變壓器式的要素即記憶里,不存在或者說根本不存在一成不變的東西。每一個后來的印象都給以前的印象罩上陰影,每一個新的記憶都蒙騙原來的記憶,直至原來的記憶面目全非,常常成為相反的東西。司湯達第一個承認記憶的不可靠和自己絕對忠于歷史真實的無能為力。他的記憶是這樣的,他無法分辨,他心中“越過大圣伯納山口”的印象,是他親身經歷的那個環境的回憶,還是他對后來看到的描述這個環境的銅版畫的回憶,他的這種記憶堪稱經典的例證。司湯達精神的繼承人馬塞爾·普魯斯特更令人信服地為這種記憶不斷改變的能力提供了一個例證:這里講的是一個男孩對扮演最著名的角色的女演員貝爾瑪的印象。在他見到貝爾瑪之前,他就在想像中構筑了一個預感,這預感完全徹底地溶化在他直接的感官印象里。他的這個印象又由于鄰座的看法而變得黯淡,第二天又由于報上的評論而受到歪曲,完全消失。幾年以后,他又看到這個女演員扮演同一個角色,這時,他和那個演員都有了很大的改變,于是他的記憶便無法確定原來的“真實”印象究竟是什么了。這可以作為任何回憶都不可靠的象征:記憶,這個一切真實情況貌似不可動搖的水位標,本身就是真實的敵人,因為在一個人開始描寫他的生活之前,他身上便已經有了一個機構從事創造而非復制活動,記憶力本身已經在發揮一切創作的功用了。于是這里便出現了:本質東西的篩選,加強和減弱,有機的組合。幸虧有了記憶這種創造性的想像力,每個敘事者才不知不覺地成為自己傳記的作家。我們的新世界里智慧最高的人歌德就深知這一點,他的自傳的英雄主義的標題《詩與真》對任何自我懺悔都是適用的。
如果沒有一個人能說出實情,說出他個人生活的絕對的真實情況,如果每一個自我供認者都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他個人生活的詩人,那么,努力做到真實便要求每個自白者心里具有道德上最高的坦誠。無疑,歌德所說的那種“假懺悔”是秘密的懺悔,都披著一眼即可看穿的小說和詩歌的外衣,比拉起瞄準器進行描述要容易得多,從藝術角度看往往更有說服力。不過,正因為這里不僅要求實情,而且要求不加修飾的實情,所以自傳描述的便是每個藝術家特別杰出的行為。因為沒有任何地方能像在他的自我暴露中這樣完全徹底地描寫出一個人道德上的概貌。只有成熟的、熟諳心理的藝術家才能成功地寫出這樣的自傳。因此,心理的自我描述很晚才出現在藝術的行列里;它只屬于我們的時代,屬于新的、即將到來的時代。人這種生物必須發現他內心的大陸,測量他內心的大洋,學會他內心的語言,然后才能把他的目光轉向他的內心世界。整個古代對這種深奧莫測的方法一無所知:那個時代的自我描述者,包括愷撒和普魯塔克,都只會羅列事實和客觀的事件,從來都不想稍許挖掘自己的內心。人在能夠研究自己的內心之前,必須意識到內心的存在,而這一發現是以基督徒精神的出現真正開始的。奧古斯丁的《懺悔錄》使內在的眼睛睜開了,但這位大主教的目光并不轉向自我,而是轉向他希望按照自己的變化而變化的并加以教化的教區;他希望他的宗教宣傳的小冊子能夠起到教區懺悔的作用,起到示范贖罪的作用,也就是具有神學上的目的,不是作為對自我的回答和理解。又過了數百年,才有盧梭這位奇異的開拓者,這位炸毀禁錮人心一切束縛的人,為自己創作出一幅自畫像,連他自己都對他的這種新奇大膽的行為感到驚異。“我打算做一件事,”他開始說,“這種事沒有先例可循……我想描繪一個天性百分之百真實的人,這個人就是我自己。”但他懷著每個初學者的輕信,誤以為“這個我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統一體,是一種可比較的東西”,以為“真實情況是可以摸得著抓得到的”,他還天真地相信,“只要法庭的長號一吹響”,他“就能夠手里拿著這本書走到法官面前說:我過去就是這個樣子”。我們這些后代人不再有盧梭那種老實的輕信心理,取而代之的是關于靈魂的多種意義和秘密深度的更完整更大膽的知識。我們的自我解剖的好奇心試圖通過越來越細的分解和越來越大膽的分析披露每一種感覺和思想的神經與脈絡。司湯達、黑貝爾[3]、克爾愷郭爾、托爾斯泰、阿米爾、勇敢的漢斯·耶格爾,都通過他們的自我描述發現出人意料的自我科學的領域。他們的后代,由于有了更精密的心理學儀器,將一層又一層,一個領域又一個領域,越來越廣闊地深入研究我們這個新的無限世界:人的內心。
對那些不斷聽到人們說起技術和理智世界里藝術正在衰落的人來說,這將是一個安慰。藝術不會終結,它只會轉換方向。無疑,人類神話般的創造力畢竟減弱了。幻想在人的童年時代永遠具有最強大的影響,每一個民族永遠在它生存的早期為自己創造神話和象征。但是知識的明確透徹、具有文獻性質的力量取代了這種日漸衰退的空想力。人們可以在我們同代人的長篇小說里看到這種創造力的具體化。這種長篇小說今天正十分清楚地發展成精確的心理學,而不是在大膽地任意編造。但在創作與科學的這種結合中,藝術根本不會被壓死。遠古親如手足的關系會得到更新,因為當科學出現時,在古希臘詩人赫西俄德和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那里,科學還只是創作,還是一個含糊不清的詞語和搖擺不定的假說。現在,在二者分開幾千年以后,研究的意識又與創造的意識結合在一起了。從今以后,創作不再局限于描寫虛構的世界,而是描寫我們人性的魅力。創作不能再從地球的未知事物中汲取力量了,因為所有的熱帶和酷寒之地都被發現了,所有的動物和植物直至一切碧水海底的奇跡都被研究到了。塵世間什么地方也不會再有神話了,即使在其他天體上,即使攀緣在我們已經測定的、已用名字和數碼標明的地球上,永遠渴求知識的意向也不得不漸漸轉向內心,轉向自身的神秘之處。這種內心的無限、靈魂的宇宙還為藝術開辟了許多取之不盡的領域,因為揭示內心的精神,也就是認識自我,將成為智慧人類在未來要愈發勇敢地解決卻又解決不了的任務。
一九二八年復活節于薩爾茨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