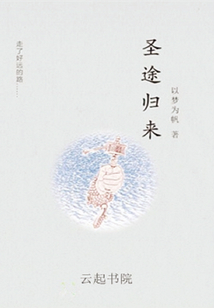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 1評論第1章 前言
他之才,文墨比書干。他朝駕鶴入云,旗云得開,揮手一摸,斑若星河。
這是我生平作的第一首短詩,雖然格式、韻律尚不成型,讀來倒也朗朗上口。那是發生在課堂上的趣事。老師喊我三遍,神游物外的我被喚醒。“不聽講,在干嘛?”同桌出賣了我,“他在寫詩呢!”哄堂一笑。然后我就被叫上講臺獻詩一首。從書桌到講臺不過七步開外,我沒有曹子建七步成詩的才華,想的倒是“不知從何時起我華夏的詩詞歌賦竟成了供人哄堂發笑的引子。”好在我做出了一首《凈空寺》,詩曰:姹紫嫣紅總是情,迷離佛陀錯念經。世間有所凈空寺,只念枯禪不念音。自此后他們便開始叫我“詩人”。
講這件往事倒不是要與曹子建斗文,只是感慨當年自己揮斥方遒、激揚文字的那股子書生意氣。其實,細品那首臨堂而作的《凈空寺》或多或少我是有嘲諷、抨擊的寓意在里面的。
席慕蓉說:一首詩二十歲看是一種心情,三十歲看是另一種心情。讓現在年齡的我去創作那樣的詩,我是著實寫不出來的。這跟文采無關,是心境不一樣了。
談到寫詩,我一直有著這樣的認為:人生來都有詩人的潛質,只是走著走著我們的靈魂被肉體丟在了身后。沒有靈魂的肉體,行尸走肉,又談何詩的情愫。至于為什么寫?一樣是將情緒和態度表達出來,情緒來了就寫,情緒走了倒頭便睡。
那年,我想出人頭地,光耀門楣,想寫幾首流傳千古的名詩給下一代品玩,于是我埋頭苦讀,坐爛幾張凳子也沒憋出一首像樣的詩。就這樣我初生做個詩人的理想破滅了。
安天下,興社稷,堆祖墳不是我的態度,不是從心底里自然萌生的理想。理想一詞,本就太過虛妄。似一沉重烙印深深刻在心里。揭開烙印方才發現在這之下貯藏的是一道隱隱不去觸碰的傷痕。莫不然,如此血淋淋的烙印竟讓人毫無痛感。
詩者,集天地靈氣于身。觀萬物之表,言其性也。故而,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言之為詩,情動于中發于言,言之不租嗟嘆栽。因此,好的詩人也定是一位懂得生活懂得人間疾苦的人。
人往往只有把自己變成一個真實的弱勢者方能真切感受人間疾苦和真愛。這與你到貧窮中體驗苦難不同。就好比把兩個人丟進沙漠,一個有后援,一個無后援。貧苦會讓人無助與孤獨。孤獨無處訴說時,便想寫下來。而那樣的孤獨創作是對自己心境的一次洗禮。善惡之事,你懵懂不清時,在換位思考中,往往會從你詩歌中涇渭分明地體現出來。這一點“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杜甫做到了。所以他成了善鳴詩者的“詩圣”。
一次次切入人生、人性、仁愛的創作,會令人更深刻的去思索生命的真實意義:人,何以為人?這種思索會提升思想的高度,或說是安定你對俗世的浮躁情結。我相信這個過程,更享受于這一過程。
2018年的深秋,我實現了縈繞心頭多年的XZ夢。在唐古拉山口,我看見了那只飛越雪山的雄鷹;在大昭寺門前,我目睹了夜以繼日的朝拜者;在羅布林卡,我跟隨著那位老喇嘛觸摸遍所有轉經筒;最后,布達拉宮前,和一位來自理塘的七旬阿瑪拉做了合影。快門按下的那一刻,我的內心莫名傷感。許久以前,那位少年的活佛也來自理塘。于是有了那首《上師倉央嘉措》的詩,詩中摻插了些許對生命的思考。“人和佛的區別在于人面對現實會屈服,佛也會,但不是屈服而是坦然接受。佛在面對殘酷現實摧殘時精神永遠高架于身軀之上,所以,人是未來佛,佛是過來人。這過來與未來之間橫亙的不過是修行。”修行為何?是對生命、生活的體會罷了。因此,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人成不了佛,更成不了詩人。
生活是什么?生活是平常人家的煙火,它裊裊升起,凝結著世間縷縷動人的溫馨。凝一眸碧水,拈一縷清風,于一懷靜謐中傾聽凡塵的落音。這世間的萬物如此寧靜,躁動的是難耐寂寞的人心。
關于光陰的故事,終有一天都會在歲月的素箋上泛黃,我們所能做的是在它泛黃之前將其埋葬。
《圣途歸來》是我從多年來創作的詩詞里篩選并整理成冊的一本詩集。是關于親情、友情、愛情和人生的一些思考。老人們常講:“三十而立!”立德、立業、立家,而我所想要的除此之外還應是立著。這跟傲氣無關,事關文人的傲骨而已。
聽到它們將要載入華夏詩壇的消息,我的內心是由衷感慨的。自從它們在我的筆下誕生以來,這么多年,居無定所,像無根的浮萍四海為家。如今,我給它們正名,縱是投了這筆,負了這三千繁華又有何妨。
就像八廓街那位多吉林活佛給過我的偈語:“命有華蓋,生而不凡。”
“你這張帆只是少了一片海洋。”
“生于西北荒漠,何來大海?”
“沙漠亦叫沙海!”
想我本是那莫尼山下采石郎,從天德城到LS,從烏梁素海到納木錯,采石鋪路,恪守不渝。圣途,走了好遠的路,我從夢中醒來,沒有恐懼沒有荒蕪,一切都是自然自在的。
沉浮的時光終是在不經意間滌蕩,時間的無涯已經留不住經年的癡狂。云淡風輕,黃葉更迭,輕輕吹起的思緒,已是久遠的辰光。
我曾在春天的萬物復蘇里離開,夏天的雪山連綿中停留,秋天的期待碩果中回歸。我不曾去描寫冬天的感悟,因為冬天來了春天不會太晚。
我不喜歡拍照,因為快門按下的瞬間,我們已老。
一個人的行走,不需要被標榜成瀟灑的旅行。思考,尋找,才是初衷。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圣途很遠,一步一蓮花,終會到達。出發了,就不再是難事。義無反顧還是飛蛾撲火,是給放縱青春一個借口,還是只是自己恣意妄為的任性后所承擔的后果?面對著綿延雪山,眼前的一切皆是雪白。站住了,思想也就停住了,皆因你我身在無印的云端。所以,對著雪山,就不該有過多的雜念。一切都會釋懷,久了,你的靈魂會得到乾安。生命何等可貴,像亙古時光里的洪荒之力,未曾,未有,亦未重生。
生命的行走,安靜的行走,或許還未曾走出這虛數空間,思想已升華了千年。
在LS的每個夜晚,總會去布宮一遍遍的轉著經筒,一圈又一圈。酥油燈的火苗幽幽,仿佛能參透前世與往生,搖經筒的佛光燦燦,轉去流年,轉去悲傷,轉去雜念。
朝圣,天堂,信仰,絕美,詩意,從容,重生,釋懷。沒有人能找到一句話來形容她。可是,我找到了,在一個念誦了整晚上梵經的喇嘛那里,我找到了它,是他寫予世間最舒真的情話!
三十歲,正當時,晚幾年心力不足;早幾年經驗不足。三十多歲是詩人創作的黃金時代。每一位詩人都曾與寂寥的夜有過隔空長談。創作是對長談的紀錄。天地靜謐,夜深人靜,一支筆,一盞燈,陪伴他的仍舊是那一灣星宿。
曾經的他墜入紅塵深處,輕倚于時光的路口,靜看花開花謝。
現在的他破繭而出,佇立于風口浪尖處,關心的還會是那一場花事。
于一懷靜謐中傾聽凡塵落素,經年回眸,其實,每一次花開花謝,何嘗不是一次心靈的泅渡?
生命是一場懂得,剪了一段流年的時光,握著一路相隨的暖,把最平淡的日子梳理成詩意的風景。
一輩子攜過一支筆,是心路歷程孤寂的緬懷史;一輩子走過一條路,是圣途歸來對信念的執守。你問我,手中的這支筆經歷過多少風和雨?
我翻開這《圣途歸來》的心路歷程,默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