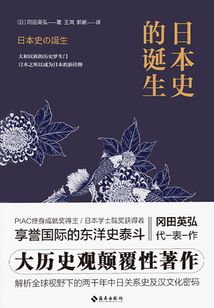
日本史的誕生
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推薦序
胡令遠
《日本史的誕生》是日本著名歷史學家岡田英弘多年研究成果的擷英集萃之作,其與結構嚴整、內容厚重的煌煌歷史著述雖判然有別,但“形散而神不散”,集中討論的是日本史“自身”與日本史“誕生”二者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這就如同一個嬰兒的孕育過程與其怎樣來到世間一樣,兩者之間既有聯系,又是判然有別的兩類事情。探尋作為“客觀存在”的歷史自身,與難免存在“主觀意志”的史書的“誕生”兩者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是一件饒有意味但又十分具有挑戰性的工作。因而,探賾索隱、洞幽燭微,去偽存真、去蕪取菁,從而達到“撥云見日”的睿智與思辨性,也就自然而然成為這本文集的伴生物和鮮明特色。
本書以三本史書——被稱為地中海文明“歷史之父”的希羅多德編寫的《歷史》(Historiai)、被魯迅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和作為日本第一本“正史”的《日本書紀》——為例證,闡述并強調了作者對“歷史誕生”的三個基本觀點。
首先,岡田認為應該把“國史”(即國別史)放在區域文明中去考察。基于此,日本史與中國文明密不可分,歐洲諸國之間更是如此。這一點在今天也許已經是人們的常識,特別是湯因比的《歷史研究》問世之后。但從現實層面看,包括“皇國史觀”在內的各種日本文明獨特論在今天依然謬種流傳,可知岡田先生強調這一點并非過時。
第二,岡田認為“只要是人撰寫出來的歷史,都帶有各自的態度和立場。無論哪一種文明,第一部撰寫出來的史書,早已決定了該文明的個性,并能夠將這種印象固化,告訴人們他們到底是什么樣的一種人”。譬如“希臘人諸城市團結對抗席卷世界的波斯帝國的威脅,于公元前480年的薩拉米斯海戰中獲勝的事件是希羅多德編寫《歷史》一書的契機。在希羅多德的構想當中,是把世界描繪成亞洲對歐洲、東對西的對立抗爭”。“位于地中海文明分水嶺的西歐人根深蒂固地認為,歷史就是從對立走向統一的過程。好像有一個最后的終點,全世界都朝著這個終點前進。”而司馬遷的《史記》,則敘述以漢武帝為中心運轉的世界,空間涉及天文、地理、世事;時間則從神話時代的黃帝開始,貫穿五帝、夏、殷商、周、秦,一直到公元前2世紀末的當時為止。其敘述的要害和核心問題是“天命”與不變的“正統”。與地中海文明或西歐文明以對立與抗爭為歷史的本質不同,中國文明的歷史借由敘述穩定不變的世界來證明皇權的正統性,其中沒有世界從何而來、要往何去的觀念。而《日本書紀》是作為公元660年天武天皇建國大業的一環開始發起,宣揚天智、天武兄弟的祖先是從天神手中繼承正統,一直統治著整個日本列島。其無視中國的影響,與從中國歷史文獻中看到的事實完全相反——這是因為撰寫《日本書紀》的目的,就是為了證明日本作為一個統一的國家,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早在公元前7世紀,日本便已經統治了整個日本列島。
岡田認為,正如《史記》的歷史書寫,決定了之后中國的歷史文化。《日本書紀》中表現出的“日本與中國對立”“奉天繼承獨自正統的國家”等封閉思想,永久地決定了日本的性格。他的結論是:“無論哪一個文明,最初寫下的歷史框架,限制了人們的意識,第一部史書決定了國家的個性。”雖然這一結論還有待商榷之處,但它對我們認識和理解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性格,還是提供了一個可以發人深思的空間與新的視角。
第三,《日本書紀》即“日本史的誕生”,是當時倭國內外情勢的產物,并非孤立的現象。即公元前108年漢武帝征服了朝鮮半島之后,日本列島上的倭人住民就不斷受到中國文明的沖擊,在其后800多年的歲月里,他們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屬于亞洲大陸,尚未擁有屬于自己的歷史。公元660年唐朝與新羅聯手滅了百濟,倭國為了復興半島上的這一長期盟友,與唐朝發生了軍事沖突,結果在663年的白村江之戰中慘敗并被徹底趕出半島。對于列島上的倭人而言,百濟是通往世界的窗口,它的存亡對倭人可以說是生死攸關。而且,高句麗王國也于公元668年被唐軍所滅。至今為止,他們所知的全世界,都被唐朝及其同盟的新羅王國所征服。這種情勢對倭國不言而喻是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機,面對這樣的非常事態,他們采取的對策是將日本列島各地的諸氏族,以倭國王家為中心團結起來,組成統一的國家。于是,繼承倭國王家的天智天皇于公元668年在近江即位,成了日本第一位天皇。這個“日本”的國號與“天皇”的王號,就是在此時頒布的日本列島最初的成文法典《近江律令》中制定的。同時,為了主張獨自的自我認同,必須要有自己的歷史。因此,著手編纂所謂國史——《日本書紀》,也就成為題中應有之義。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區域文明與地緣政治孕育和催生了“日本史”,而“《日本書紀》反映的是日本國誕生之時的政治需求”。
以上三個基本觀點所體現的岡田先生的“史識”,從書中看,有兩個基本支撐點:其一為方法論的“史料批評”,其二是端正“國益”與民族感情。我們看到,岡田在闡述與論證自己的史學觀點時,對無論什么資料、包括所謂第一手的資料,都要盡最大可能在兩個層面詳加考證,一是史實本身,二是這些史實的政治意蘊。譬如,他指出:“我們在使用《日本書紀》中的史料時,唯一的辦法就是,在了解到日本7世紀這種建國當時政治形勢的基礎之上,一條一條地對其學術價值加以甄別與判斷。這便是史料批評,是一種歷史學的正統研究方法。那些只懂得日本史的史學家們,則往往會被《日本書紀》牽著鼻子走。倘若想要從《日本書紀》的框架之中逃離出來,就必須具備中國史和韓半島史的基本常識。”同時,他認為:“一個歷史學家,如果想撰寫一部真正的世界史,那就必須要摒棄所有眼前的利害關系、理想和情感,思辨地對歷史脈絡加以梳理,對史料加以解釋,保持一種融合性的立場。只有在這種立場下書寫的歷史,才能夠超越歷史學家個人的意見,成為人人都能夠接受的‘真實’。日本的歷史,也應該如此。”
因此,可以說這部書是一部嚴肅的史學論著,幾乎涉及所有有關歷史研究的方法、理論、治學態度,并將其衍化進作者自己的研究過程與結果中,可謂身體力行。要了解真實的日本史,特別是日本史的誕生,這是一本必讀書。其實,它給予讀者的啟迪,遠遠超過本書的具體內容。
同時,這本書還充滿黑色的“歷史幽默”,作者的睿智,體現在風趣的行文之中。有不少大膽的比喻,在讀史書時可以說聞所未聞。這些也許會被人諷為“野狐禪”,亦屬仁智之見。
本書譯者郭穎、王嵐兩位老師,分別于日本廣島大學和廈門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現均執教于廈門大學外文學院。兩位老師學養既深湛,又兼才華橫溢、譯筆如椽,允為此書中譯本增色良多。
胡令遠:
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上海高校智庫“亞太區域合作與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部“兩岸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首席教授,曾任日本東京大學外國人研究員、京都大學客座教授、香港大學客座教授,兼任中華日本學會副會長、中國日本史學會副會長、中華日本學研究學會(香港)副會長、上海市國際關系學會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為當代中日關系、文化·文明與國際政治。學術專著包括《東亞文明的共振與環流》等3部,主編有《戰后日本的主要社會思潮與中日關系》《國際化——島國日本的歷史抉擇》等6部,發表中、日、英文學術論文60余篇。

